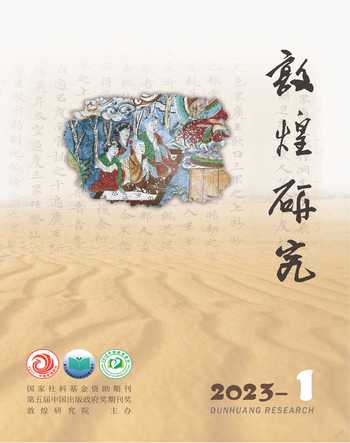夏鼐與西北科學考察團
閆麗
內容摘要:1943—1945年,夏鼐受“中央研究院”委派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他在考古發掘、田野記載和文物保存方面利用科學的方法,是中國學者在西北地區的首次科學考古發掘活動。考察期間,面對嚴酷的自然環境和復雜的地方民情,夏鼐屢次有效解決,極大地推動考察團順利進行。考察所獲漢簡、碑刻、隨葬品等文物為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至今仍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夏鼐;西北科學考察團;科學發掘
中圖分類號:K87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23)01-0149-10
Xia Nai and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Plus a Discussion on the Beginning of Scientific Archaeology
in Northwest China
YAN li
(Institute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63, Zhejiang)
Abstract:In 1943-1945, Xia Nai was appointed to the historical archaeology group of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by the Academia Sinica. Professor Xias use of scientific methods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field documentation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mark the first scientific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undertaken by Chinese scholars in northwest China. During the expedition, Xia Nai effectively reacted to problems caused by the harsh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omplex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greatly facilitating the progress of the expedition. The artifacts obtained during the expedition, which included Han dynasty slips, stele inscriptions and funerary objects, provided important material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are of great value even today.
Keywords:Xia Nai;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scientific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夏鼐(1910—1985),字作銘,1930年進入燕京大學,次年轉入清華大學學習,1934年在清華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35年—1939年在英國倫敦大學留學,獲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1941年回國后先后供職于“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0年—1982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先后主持多起重大考古發掘活動,發表《齊家期墓葬的新發現及其年代的改訂》《臨洮寺洼山發掘記》《敦煌藏經洞封啟的年代》《漫談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學》等文章,并出版《考古學論文集》《考古學和科技史》《中國文明的起源》等著作,在史前考古、中國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作為著名的考古學家、中西交通史學家,夏鼐的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20世紀40年代,他參加了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聯合組建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歷時一年半,主要對甘肅境內的遺址進行調查發掘。該團考察地域范圍廣,從蘭州至敦煌;所考察的遺址時間跨度大,自史前至隋唐。關于發掘過程和細節,除《夏鼐日記》的相關記述外,考察團成員也有相關著文{1},此不贅述。關于考察團的研究,目前學界已有較多成果,但很少涉及夏鼐與西北科學考察團。因此本文重點從學術史角度出發,探析夏鼐與考察團的關系。這對于了解他的個人經歷,以及推進史前考古、中西交通史、敦煌學、近代考古學的發展,皆有重要價值。
一 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的成立
20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抗戰形勢的日益嚴峻,西北作為大后方,各界掀起一股“到西北去”“開發西北”的熱潮。在這樣的背景下,大量考察團體前往西北進行歷史文化、地質地理、森林植被、礦產資源的考察。
傅斯年基于民族自尊心,一直希望以科學方法考察西北,并找到新資料加以研究,以期奪回東方學的主導權。1928年,他在籌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未來工作藍圖時就表示對西北研究的熱忱{2}。但此地區早年經過國內外探險家和團隊的盜挖,傅斯年對還能獲得文物的數量及質量并沒有太大把握。他認為只有在時間、經費、人力充裕時,考察才能有所成就。因此,1942年西北史地考察團{3}派出時,他在給西北史地考察團團長辛樹幟和“中央研究院”總干事葉企孫的信中說道:“敦煌初步考查西人走之已熟,煌煌巨制,學人共喻。今茲之行,弟等感覺必須稍有所得,若漢簡及漢唐遺物能有特殊發現,始免貽笑他人。若仍系試探性質,則西籍具在,展卷可當臥游,何必舍吾人更重要之工作空走此一躺哉。”[1]。又表示若經濟未得到改善,此組或許應該取消。抗戰時期,史語所經費拮據,他認為當下最重要的事是撰寫安陽殷墟發掘報告{4}。所以在給葉企孫的另一封信中說:“石、勞之行,必一無成績(所云報告由敝所出版,亦一句話耳,蓋根本在科學上不能有所得也)”[1]948-949。
但在西北史地考察團結束后,向達、石璋如、勞榦在石窟寺和簡牘方面大有收獲{1}。向達認為西北考古工作大有可為,1942年11月26日,當他還在敦煌考察時就致信朱家驊說:“今日組織考察團在西北工作一二年之一般考察,借明各地大勢固屬切要之舉,唯如對于各種問題欲為精深之研究以冀獲一可信之結論,則非在河西籌設一永久性質之工作站不可。”{2}之后他又告訴好友曾昭燏:“西北工作,絕非旅行式之考察所可盡,非設一工作站作長期工作不可。”[2]。同年向達發表《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3],主張在河西選擇一個適中的地點設立工作站,對西北的古城廢址、長城遺跡、古墓葬群進行詳細發掘勘測。這個建議使傅斯年對設立西北工作站的想法信心大增。1943年1月15日,在組織第二次西北考察(西北科學考察團)期間,他致信朱家驊表示:“就目下情形言,若能將西北科學考察團改為‘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將其并入,似更方便”{3}。同年2月2日,李濟就傅斯年對此事的態度復信向達:“(一)于敦煌現在情形得一詳盡之紀錄;(二)于西北工作站之組織設備及工作節目得一具體之建議,此兩事已在大函中得到極圓滿之答復矣。”{4}并就考察經費作了說明:“孟真先生與弟同具下列意見:‘本年度西北考察團之十萬元全作歷史考古用,由兄負責支配,建設西北工作站詳細計劃請兄擬定……博物院籌備處本年度預算成立后,除撥史前考古費外,若尚有余款,可優先撥用作補充西北工作站經費。”{5}西北工作站原為“中研院”“中博院”合作辦理,1943年2月28日,向達致曾昭燏信表明:“近得湯錫予先生函,謂北大有與‘中研院‘中博院合作,在西北設立歷史考古工作站之意云云。”[2]392但最終因抗戰期間交通不便、經費不足等原因,不能支持長期工作,以三家聯合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進行短期考察替代西北工作站。
二 夏鼐西北科學考察之始末
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的人選幾經變更,但對夏鼐的推薦卻始終如一。向達在1942年11月26日給朱家驊的信中表示:“唯工作站之設立有相當之人才而無充分之經費,無米之炊亦難有成”{6}。可見此時他僅擔憂經費問題,對于考察人選已經胸有成竹{7}。同年12月在給曾昭燏的信中他說“若得作民兄與足下來此,則誠妙選矣”{8},直接表達他想讓夏鼐和曾昭燏主持西北工作的想法。之后,曾昭燏回信或許因其在“中博院”的工作無暇顧及而推辭。1943年1月向達復信時提出“私意作民(夏鼐)如能同石君璋如來此,正式作有系統之發掘,絕不至于毫無所得。”[2]388向達與夏鼐相識于英國留學時期,每談及夏鼐,向達都贊不絕口,他在給曾昭燏的信中說道:“作民不唯于考古學出色當行,即于史學、人類學及其他相關各部門,亦有相當修養。若再能在西北馳驅一二十年,自可開一代風氣”[2]394-395。夏鼐在留學期間系統學習了經緯儀測量法、考古遺存的田野發掘與室內整理、礦物與巖石示范、田野考古的目的與方法、考古繪圖、體質人類學等課程,并先后參與梅登堡城址{1}、阿爾曼特遺址{2}、杜韋兒遺墟{3}的發掘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可見向達所言非虛。
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組長及“中央博物館”籌備外籌備主任的李濟是夏鼐的老師,對他也非常賞識,早在夏鼐還在英國時就有意聘請他{4}。因此在人選方面,他與向達有相同的意見。1943年2月2日,他給向達的信中說:“夏作民兄返李莊時,弟勸往西北助兄一臂”{5}。向達對西北考察考慮得更為細致,3月1日他寫信給傅斯年、李濟表示:“工作站達既不能負主持之責,故于人選一事,自無所用其置啄,至于作民兄如不來此瓜代,則達唯有結束一切,作逐漸撤退,東歸返川之計耳”,又表示:“達在此俟作民兄來后,即行東歸。作民在此,人生地疏,璋如先生人既精干,留此時間亦長,各方面俱熟悉,如能為作民臂助,豈不甚佳”[2]420-421。
其中,石璋如以史前遺址見長,第一次考察之前他就以“安特生的‘史前六期(齊家、仰韶、馬廠、辛店、寺洼、沙井)為預定計劃”[4]。所以在考察結束后,他認為“勞先生的工作已經完成,可以回到李莊,我的調查工作還未開始。”而且“原本預定先做完沙井遺址后,安特生剩下來的遺址就分布于隴南、青海一帶,離沙井很遠……現在無法成行。”[4]270但由于他們已經作了千佛洞調查,所以他希望前往鞏縣石窟和龍門石窟,也因此未能參加第二次西北考察。向達對夏鼐前往西北的希望自始至終沒有改變。對于石璋如不能幫助夏鼐,向達在給曾昭燏的信中說:“達愿在旁協助,將工作站成立,然后東歸;過此,則非達之力量所能勝矣”[2]395。傅斯年早有派夏鼐前往西北考察之意。向達對此也強烈建議,3月9日他給王重民的信中確切地說:“孟真、濟之先生來函謂即擬以此款在敦煌設立一工作站,命弟在此主持籌備,且擬派夏作民(鼐)兄來,北大亦有命弟留此勿歸之意。弟俱覆函力薦作民主持此事”[5]。說明此時夏鼐作為西北科學考察團的人選已經確定。
1943年5月31日,夏鼐抵達重慶,開始了西北考察的準備事宜。當日他拜謁葉企孫和“中央研究院”會計處主任王敬禮時被告知:“‘中央研究院已決定派余及向覺明先生二人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希望余不久即可赴西北工作。”[6]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古組原定9月底出發,但夏鼐自9月17日起連日生病{1},身體條件不允許遠赴西北。因此,9月21日向達寫信向傅斯年詢問西北科學考察團的進展時說:“達與作民商量,以為關于今后歷史考古組西北工作,不外三途:(一)根本取消;(二)由左右及濟之先生另簡賢者,重組歷史考古組赴西北工作;(三)待作民愈后,于明年一、二月再行出發。區區之見,不識先生以為如何?”[2]42311月4日,向達再次致信傅斯年表示:“(夏)作銘病愈,唯身體尚未復員,勞作稍久,即感疲乏,是以今冬出發赴河西一事,亦不敢向之強聒”[2]424。可見在三種方案中,傅斯年依舊堅持由向達和夏鼐前往西北,并趨向等夏鼐病愈后再出發。由此,原定9月底出發的西北考察不得不延遲。
但在客觀上使考察團有更多的準備時間。除考察前的公務外,夏鼐大量閱讀與西北相關的中外研究論著。國內論著包括正史、地方志、考察日記及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華陽國志》《甘肅通志》《肅州志》《流沙墜簡》《敦煌隨筆》《居延漢簡考釋序文》《敦煌佛教藝術的系統》等。外國論著涉及《遠東地形學與考古學研究》《塞林提亞:中亞與中國西域考古記》《奧萊爾·斯坦因爵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5年進行探險期間測繪的中國新疆和甘肅地圖研究報告》《沙埋契丹廢墟記》《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發現的漢文文書》《敦煌石窟》《敦煌畫の研究》《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等。其實夏鼐并不是首次閱讀這些外國學者書籍,早在30年代英國留學期間,他就已經大量閱讀了海外漢學家與中國歷史考古相關的著作{2}。他閱讀的西北地區研究論著時間范圍上自馬家窯、齊家史前遺址,中至隋唐繪畫、石窟,晚到明清史料碑刻,這使他對西北的研究情況有了更全面的把握。除文字材料外,夏鼐也非常注重圖像資料。考察前,他預先描摹了古籍及西方學者書中與西北相關的地圖,以供考察之用{1}。夏鼐在閱讀漢至唐各史地理志時,又將有關河西走廊的內容抄錄成冊,為繪制漢唐時期河西地圖做準備。這都為考察團的發掘和研究工作順利進行奠定了基礎。1944年3月21日,因購機票排序問題,向達先行前往蘭州。夏鼐乘坐下一班機于4月4日抵達蘭州,西北考察正式開始。
考察的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考察自1944年4月4日夏鼐抵達蘭州到1945年1月15日他返回蘭州。主要工作地點在蘭州和敦煌附近,在蘭州調查西果園、十里店、土門后山、曹家嘴、青崗岔等史前遺址。在敦煌地區主要是發掘敦煌墓葬群、調查石窟寺遺址,以及考察漢長城烽燧遺存。其中發掘墓葬共30座,包括敦煌佛爺廟東近2千米處的六朝墓葬10座(FYM1001—1010)、佛爺廟東破墩子下的六朝墓葬8座(FYM501—508)、老爺廟唐墓2座(LYM一—二)、敦煌城南沙山墓葬10座(M101—110)。考察遺址包括小方盤城、壽昌古城、雙塔堡、鎖陽城等,并對千佛洞和西千佛洞做了詳細的調查和記錄。第二階段的考察從1945年1月15日到12月18日夏鼐離開蘭州。主要工作地點在臨洮、張掖、武威。考察的遺址包括臨洮辛店、寺洼山、陽洼灣、瓦罐嘴等史前遺址,張掖黑水國遺址,以及武威三角城、沙井子、黃蒿井子等。另外,夏鼐等人還在武威發掘了兩座慕容氏墓葬,分別為唐金城縣主和慕容曦光墓。
1945年12月18日,夏鼐結束考察從蘭州返回重慶。返程途中,由廣元前往李莊時,因所攜五箱行李過重且經費不充裕{2},夏鼐只能從水路返回。1946年1月4日他經過廣元時,所乘船只遭到搶劫,除器械現金及私人物品外,還丟失了西北考察團在武威所掘得的木質黑漆馬鞍殘片7片(其中4片鑲嵌有金片花草禽獸裝飾)、西北史地考察團石璋如經手所購玉帶鉤10件,以及考察團拍攝但還沒來得及沖洗的膠卷10卷{3}。“中研院”對此事格外重視,事后多次致函廣元、閬中縣政府及四川省政府尋求幫助{4}。政府部門收到公函后予以高度重視,由廣元市警察局長劉彥章親自率隊破獲此案,并以防范不周清查當地保長{1}。然而丟失的文物及膠卷卻并未找回。1946年2月24日,夏鼐安全抵達重慶,西北考察正式結束。
三 夏鼐對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貢獻
考察期間,向達雖任考察組長,但因他不熟悉田野考古技術,所以較多地承擔行政事務[7]。他在1944年9月13日給袁同禮的信中表示:“五月抵敦,復亦曾告孟真先生,工作站既已成立,三個月后達即準備東歸”[2]431。這與向達預計幫助夏鼐熟悉西北地理環境和人文風貌后就返回重慶的計劃一致,10月19日向達離開敦煌。之后的考察工作交給夏鼐和閻文儒,但閻文儒在考察期間分別就職于敦煌藝術研究所和西北師范學院。因此,全面主持考察團的夏鼐“實以一人之力代表史語所在甘肅從事先驅性的工作”[8]。歷時近兩年的考察,收獲頗豐。在考察期間,夏鼐貢獻頗多,主要歸納為以下兩方面。
1. 科學方法在西北考古中的首次使用
此次考察是夏鼐第一次獨立主持的考古工作。他在考察期間嚴格應用考古學方法,每到一處要么拜訪當地活躍的文化人,要么參觀遺址點或民眾教育館,盡可能地了解當地的文物狀況,做到了調查的廣泛性。在發掘方面,嚴格按照探方分格的方法,并以熔蠟法提取木質。在田野記載時,隨時繪圖攝影,以便更好地記錄文物情況。在文物保存方面,考慮到文物不能脫離歷史環境,夏鼐對大型文物采取就地保存的方式。這些都是當時科學考古方法首次應用到西北地區考古發掘的表現。
夏鼐曾說:“考古工作者成績如何,主要不是看他發掘出什么東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發掘出這些東西而定”[9]。他認為科學的發掘方法,“目標在搜取古代一切遺物或遺跡,以重造古代歷史”[10]。而此前西北地區的考察,采用盜挖的方式,目的在于“尋寶”。我國早期由董作賓主持的殷墟發掘也采用了非科學的方式,直到李濟、梁思永的參與才改善了這種局面。1935年5月,夏鼐留學前在殷墟實習發掘時就表示:“中國考古學上的材料頗不少,可惜都是未經科學式發掘方法,故常失了重要的樞紐”[11]。1936年他在給梅貽琦的信中說:“生以為中國將來之考古學,必須以埃及考古學之規模為先范,故中國之考古學界,必須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學,以其發掘技術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鏡”[12]。1941年,夏鼐回國后,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演講考古學方法論。他主張應用層位學、標型學等方式進行科學考古[10]41-48。夏鼐關于考古學的先進理論及國際方法都成為了此次考察的理論基礎。
在遺址發掘方面,夏鼐應用探方法發掘。這個方法是夏鼐1936年在梅登堡遺址(Maiden Castle)學習的成果。此遺址的主持者惠勒將整個遺址以10英尺的探方分格發掘,首創開探方發掘的方法。夏鼐在此地進行了六個星期的專業發掘訓練。他將此方法應用到敦煌墓葬發掘中。而且在發掘時,他非常關注文化層的延展和地下堆積情況。這些在西北地區墓葬考古上是史無前例的。面對文物提取時的困難,夏鼐也應用了科學的方法,以便盡可能地保存文物的出土原狀況。1944年10月9日,在敦煌沙山M107提取木俑時,夏鼐應用了彼特里的融蠟法{2},這是當時木質器物提取的先進方法。雖然無法保存原色,但可使木質不縮皺,已經是很大的突破。在老爺廟M1提取陶俑時,夏鼐主張“剔去泥土,包以麻布,圍以石膏,然后提取,結果必佳”[13]。但因時間和設備有限,使文物出現斷裂。雖然夏鼐做了標記以便今后粘合。但足以說明當時的客觀條件僅在一定程度上能支撐科學的發掘。
田野記錄方面,夏鼐參照國外科學發掘報告撰寫發掘筆記{1}。在發掘日記中詳細記錄了發掘情形、地層狀況和出土文物的情況。除文字記錄外,夏鼐非常注重圖像資料的保存。在考察期間,他繪制了各地的遺址分布圖。如在臨洮縣發掘時,以二千分之一比例尺繪測寺洼山遺址附近圖。在千佛洞考察時,又以盛勝保{2}測繪的萬佛峽圖為藍本進行描摹。在敦煌發掘墓葬時,他繪制了《敦煌城區平面圖》以及各墓葬的平面、立面墓室圖和遺物圖。他還嚴格按照地層學的方法分析墓葬的各個文化層層位,在地層剖面圖中,側重橫縱剖面,這在此前西北考察的探險家繪圖中從未有過。考察時夏鼐隨身攜帶照相機,他所攝照片不再以考察團人物為主,而是側重于遺址圖、文物圖及地層圖。因敦煌照片沖洗價格昂貴,夏鼐特將空倉庫改成暗室自行沖印。他還經常利用休工的時間或沖洗照片,或補繪測地圖。其中夏鼐考察時的“石俄博”,即P. 2691《沙州歸義軍圖經略抄》中的漢代烽燧“破羌亭”,在21世紀初因修建水電站已經毀壞{3},但夏鼐的照片保存了當時的狀況。可見這些圖文資料在學術研究的重要性。
在文物保存方面,夏鼐對大型文物采用就地保存的方法,對小型文物分類整理后用棉花和麻布仔細包裹。對于佛爺廟M1001出土的559塊花磚,因體型較大不便運輸,且夏鼐出于不脫離原歷史環境的考慮,在考察團離開敦煌前“全部運到千佛洞。依原來的樣式復原,分做二段,堆砌在張氏編號第9洞中,做永久的保存。”[12]50這種復原保存工作前所未有,“在中國田野考古方面,尚恐為第一次”[6]253。這種保存方式也使這批花磚在戰亂中沒有流散,至今仍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對于武威唐墓出土的38片帶金飾馬鞍殘片,夏鼐“皆裹以棉花,外加麻紙標識號碼”{4}帶往重慶,可見對文物保護的重視。
2. 夏鼐對考察所遇困難的有效解決
當時西北地區自然環境惡劣、社會條件艱苦、地方民情復雜,在這種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夏鼐在考古發掘中仍然堅持不懈,并就墓葬地形與土質進行詳細分析。在遇到困難時,夏鼐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屢屢解決困難,化解危機。這也極大地保證了此次考察得以順利進行。
考察團派出后,傅斯年因經費不足并不抱太大希望,在1944年8月26日給夏鼐的信中說:“或者省下之錢,兄多走數處,亦一理也。大規模之發掘,決非今日之可能,零星小掘,則本不能存奢望也。”[1]115410月5日他寫信給夏鼐再次表明:“其實此日大局,影響及于國計民生者,亦不容許兄等久在西北也……兄亦當于工作費用完后即返。”[1]116211月25日夏鼐回信傅斯年報告了在敦煌所獲漢簡和文書[14],傅斯年大為欣喜。在次年2月5日給夏鼐的信中說“將來之工作,可以此為藍圖……本所考古事業之前途所望于兄者多矣。”關于考察團之后的走向,他表明“兄似可再在甘肅作一夏天……武威、張掖之北,長城之外,直到草地,似尚有多處可走,如此則研究之對象,仍是漢唐舊跡。若欲改變作風,往黃河上游一走,包括洮水區,直到西寧,或更西,亦佳,此則當是史前問題耳。”[1]1190對夏鼐的繼續考察表示了極大支持,同函甚至說可以再爭取經費支持。2月6日,他給朱家驊的信中對夏鼐大為贊賞,他說:“夏君乃本所少年有為之一人,在濟之兄領導之下,將來于考古界之貢獻必大”[1]1193。可見夏鼐在第一階段的考古收獲,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考察團繼續工作的條件。在《“中央研究院”概況(民國17年至37年)》中,詳述了史語所的組織機構及二十年以來的成果,其中著重提及了考古組在甘肅地區的考察活動,即“三十三年發掘敦煌漢唐遺跡。三十四年發掘洮河流域及民勤史前遺址多處,得有完整陶器及石器,又在武威發掘唐墓得墓志及珍貴之殉葬品”{1}。可見,此次考察在史語所的重要地位。這自然離不開與夏鼐的功勞。
在敦煌墓葬發掘前,夏鼐通過大量閱讀河西地質、地理情況的文獻,弄清楚了墓葬中的“礫巖”是地下鹽堿和石灰的可溶物。因為水分蒸發上升凝結,使墓道中的松軟填土變成了堅固的礫巖。在發掘時,他通過分離墓葬中因水分蒸發而產生的“礫巖”和原始礫巖,成功將墓道的原狀清理出來。此外,發掘之初,考察團因沒有正確找到探溝的位置而無法繼續進行。在此之前,斯坦因和石璋如也出于這個原因放棄發掘敦煌墓葬。但夏鼐通過將敦煌唐墓與吐魯番一帶的六朝至唐墓葬進行比較,發現古人在戈壁上筑墳的方式是在礫巖處挖傾斜的長溝做墓道,較深的一端掘橫穴做墓室,保留墓室頂部的礫巖,僅用沙礫堆積的墳堆表示墓室的位置。這種思考使他迅速找到墓地的探溝,為后期發掘奠定基礎。[12]48發掘之初,考察團以竹籃吊取的方式起土,此法極費人力和時間,嚴重影響了發掘進度。直到夏鼐以當地汲水的桔槔{2}為靈感制作取土工具代替竹籃,提高了發掘效率,才徹底改變了掘進慢的局面。
敦煌自然條件嚴酷,氣候環境惡劣。但學術研究的熱忱促使夏鼐克服了這些困難。佛爺廟發掘結束后,考察團決定前往千佛洞避暑。待其他成員到莫高窟后,夏鼐又獨自留在了工地將近十天,專門補測墓地的墓坑分布圖,當時溫度達到了華氏120度(48攝氏度左右)。對此,夏鼐當時就賦詩形容發掘的環境:
前生合成披袈裟,野廟棲身便是家。
靜參禪悅眠門板,閑觀題壁啜苦茶。[6]194
1945年11月4日,夏鼐在小方盤城考察時住在帳篷中,因天氣寒冷“晚間生火取暖,以帳篷無火窗,煙霧迷目,記日記時,真有向君所謂‘淚隨筆下之感”[6]243。11月11日, 在考察漢代烽燧時,夏鼐發現“西堿墩似即斯氏之T.XXIIIV”,想前往調查,但隨行士兵們因路程較遠、天氣寒冷,“頗欲趕到圓井住宿店,不欲復居帳篷,雖屈從余等之言,而頗有怨意”[6]250。在這種情況下,夏鼐仍堅持前往西堿墩且在第二天一大早再次到西堿墩記錄。在考察期間,也正是夏鼐的這種執著使考察團盡可能全面地調查了漢代烽燧。
夏鼐在西北考察過程中不僅僅是與天“斗”、與地“斗”,還要與人“斗”。1946年在臨洮發掘寺洼山A區時,田主趙永年向夏鼐索要5000元才允許發掘。夏鼐多方尋求幫助,最終由寺洼山保國民小學校長陳克家率領警察來工地幫助協調,“允以千元補償其損失,否則以強力執行”[6]319才解決此事。此外,5月24日,因未收到考察團匯款,夏鼐“早餐后囊中只余25元,連購一碗面條的錢也不夠”[6]334,不得已多次向臨洮師范學校校長王宇之尋求經濟支援。《夏鼐日記》1945年5月17日載:“匯款仍未至,明日取木箱的錢也不夠了,頗為著急……晤及王校長,擬暫支數千元,王校長謂校中因購平價布剛匯了8萬元,無余款可借。余往省銀行晤及張經理,以有客人在座,且與之僅晤面一次,不好意思開口借錢。赴袁荊山先生處,以昨日洮惠渠剛放水,今日正在渠上忙著,未曾遇到。”[6]332次日在日記中記載:“晨間晤及王校長,將昨日所擬之電稿與之一觀,蘭州7000元款未匯來時,擬請其暫借3000元,以便下午往提取木箱,承其允許。”[6]332又見5月24日“只得再向王校長處借1000元,花了200元購稻草。”[6]334 5月25日載:“又至王校長處聲明有車擬即先返省城,所借之錢如未匯出,到省后當即匯寄。后縣政府通知明日有車赴省,乃前往接洽,連行李一共要8000元,須先付2000元定洋。返校覓王校長未得,至縣府,晤及閻縣長,即向之借2000元。”[6]335以及5月26日“向王校長再借1000元。旋張觀芹先生來談。”[6]333在武威發掘時,武威士紳想扣留出土的慕容氏墓志。在他們的糾纏下,夏鼐最終不得已僅將墓志拓片帶回,才得以脫身。當時,夏鼐多次與當地士紳協調,并向武威縣長馬國昌和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尋求幫助{1}。同時他也向朱家驊、傅斯年報告此事并申明文物的歸屬權。朱家驊、傅斯年予以重視,他們多次與谷正倫、甘肅科學教育館館長袁翰青等交涉,1946年5月7日朱家驊致電谷正倫說:“武威縣發掘之墓志一件。已電讬蘭州科學館袁館長翰青代領暫存”{2},最終以文物歸屬“中央研究院”,暫存于甘肅科學教育館而終。由此可見夏鼐在文物保護中認真求實的精神。
總之,西北科學考察團是20世紀40年代建設西北、開發西北的產物。受抗戰影響,經費不充足,“中研院”史語所對西北的開發由長期的西北工作站改為短期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夏鼐的參與除個人學識外,也離不開傅斯年、李濟的認同和向達的推薦。考察前夏鼐的充分準備與考察期間對所遇困難的有效解決皆促使考察團順利進行。此次考察是夏鼐首次主持考古發掘工作,在發掘方法、田野記載和古物保存方面皆使用了科學考古的方法。這也是中國學者在西北地區首次科學考古發掘的應用。
參考文獻:
[1]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 傅斯年遺札:第3卷[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942.
[2]榮新江. 向達先生敦煌遺墨[M]. 北京:中華書局,2010:386.
[3]方回. 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N]. 大公報,1942-12-30.
[4]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 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M].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270.
[5]王重民. 敦煌遺書論文集[G]. 北京:中華書局,1984:329.
[6]夏鼐. 夏鼐日記:卷3[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110.
[7]王世民.夏鼐傳稿[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103.
[8]李東華. 從往來書信看傅斯年與夏鼐的關系[G]//徐蘋芳先生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徐蘋芳先生紀念文集:下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85.
[9]王仲殊. 夏鼐先生傳略[J]. 考古,1985(8):678-685.
[10]夏鼐. 夏鼐文集:第1冊[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43.
[11]夏鼐. 夏鼐日記:卷1[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328.
[12]夏鼐. 敦煌考古漫記[M].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341.
[13]夏鼐. 夏鼐西北考察日記:上[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258.
[14]邢義田. 地不愛寶: 漢代的簡牘[M]. 北京:中華書局,2011:427-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