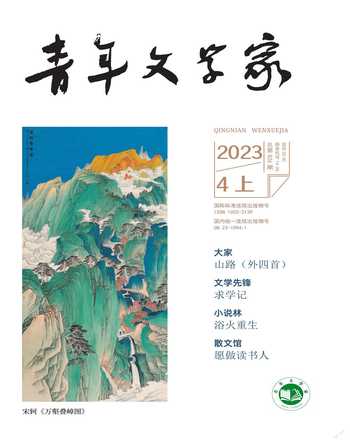祖母
李保林
祖母出生于中條山下冷口村一個姓郭的大戶人家,十五歲那年嫁入我們留孟李堡村李家。
祖母善于持家,是一位非常賢惠的女人,干凈利落。曾祖父母去世后,家務便由祖母一手操持料理。芒種時節,田地一片金黃,正是“龍口奪食”的緊要關頭,家里雇了人干活兒,全由祖母一人做飯。祖母“咣當咣當”帶有節奏感的搟面動作非常優美,一把四五十厘米長的切面刀落案有聲,看似沉重的刀身在祖母的手里變得輕盈靈巧,切面一氣呵成,粗細均勻的面條就出現在了祖母的手下。在祖母的指導下,我十來歲便學會了搟面。那個年代,鞋子、衣服全靠手工紡棉、織布制作。祖母的炕頭上,常年放著一架紡棉車。每天晚上,我就在祖母紡棉的“嗡嗡”聲中入睡,清晨又在“嗡嗡”的紡棉聲里醒來。
祖母心靈手巧,能蒸出好多花樣的喜饃,還會用紅紙剪出各樣的喜字。祖母還樂于助人,誰家辦喜事都請她去幫忙,她總是有求必應,欣然前往,即使累得胳膊疼、腿疼,也樂在其中。
祖母視孫如命,當老師的父親偶爾給祖母買點兒好吃的,祖母總要留給孫子。我們兄弟和堂兄弟十幾個,滿院里跑著、鬧著,她看著哪個都可愛。我小時候調皮,母親脾氣又暴躁,教訓起我來往往是往死里打。但由于我時常陪著祖母住,祖母對我便格外疼愛。我殺豬般的號叫揪著祖母的心,這時,祖母就會出來把我護在胸前,呵斥母親教育孩子太簡單粗暴。晚上臨睡前,祖母要上廁所,我便點上馬燈在前面照路。在當時,我們家的廁所是極超前的,跟平常蓋房一樣,設有頂棚,下雨、下雪都不受影響,而且祖母每天都把里面打掃得很干凈,別人都很羨慕。
祖母每年都要回娘家幾次,由我陪著。大人說,我們村到冷口有五里地,但我感覺非常遠。祖母拄著拐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冷口河里有水的時候多,河里墊腳石過寬的話,祖母是跳不過去的。我便搬一塊石頭放在中間,再在前面拉著祖母的手小心翼翼地過河。有一回,路過工農兵食堂,火燒的香味撩撥得我不想走。一個火燒六分錢,祖母摸遍了口袋也沒掏出來六分錢,我便哭著滿地打滾兒,祖母心疼得哄著我,又無奈得像做錯了事的孩子。上小學四年級那年,我學會了騎自行車,一條腿從車梁下掏過去跨著蹬半圈。這樣,祖母再回娘家的時候,我便能用自行車馱著她去了。平路上我騎著,上坡時就推著。到河邊時,我先把自行車扛過去,再回來牽著祖母的手過河,來往的人都夸我。
祖母一生養育了四個孩子,有我的伯父、我的父親,還有兩個姑姑。祖母除了回娘家外,也到姑姑家小住。祖母一生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姑。小姑從小體弱多病,那時醫療條件落后,落下了殘疾。出嫁后,家境又不怎么好,孩子又多,日子非常難過。小姑家住著一孔破窯洞,窯頂很高,上面有一棵蒼老的柏樹,老遠就可以看見。到了小姑家里,祖母一刻也閑不下來,把所有的被褥漿洗一遍,還要給外孫們做幾件衣裳。小姑家的土炕上跳蚤猖狂,我怕咬,便急切地盼望著去大姑家。
大姑無論是樣貌還是性情都像極了祖母,漂亮、聰慧、善良、賢淑,尤其是那雙深邃、美麗的眼睛,永遠透露出智慧與慈祥。大姑父在外有工作,光景相對要好些。大姑總是把家里打理得干凈利落、井井有條,祖母去了竟找不出什么事可做。但她的心永遠在小姑那里,到老都沒有放下……
祖母最后的那段日子,為了不給兒女添麻煩,她從未把痛苦表現出來。有一天晚上,祖母沒有讓我吹燈,用微弱的聲音對我說:“林兒,奶奶要走了,陪奶奶說會兒話吧。”我嘴上答應著,卻不知不覺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窯里一片寂靜,看著祖母安詳的睡顏,我連叫了幾聲“奶奶”,都沒有回聲。那一年,我十六歲。
如今,祖母離我而去已四十余年。隨著年齡的增長,好多事情已經逐漸淡忘,而祖母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腦海里越來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