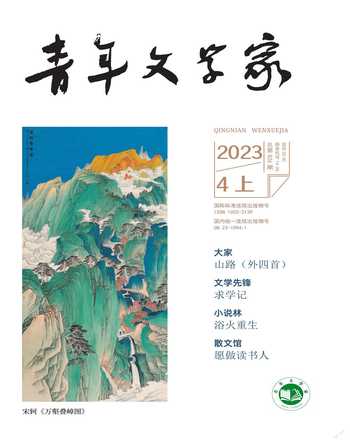綠格上衣
高丹鳳
媽媽有一件綠格上衣,總是疊得板板正正地放在一個包袱里,我從未見她穿過。不過,媽媽時常會拿出來用手一邊撫摸著一邊跟奶奶說:“這件衣服料子手感真好,有棉有毛,顏色也好。”每次看過之后,還要重新疊起來,再放回包袱里,還會順手放上兩顆衛生球。
有一次,我看見媽媽又在柜里放上衛生球,便說:“媽,你咋總不穿呢?這衣服多好看呀!”媽媽回過頭對我笑笑:“你還小,等你長大了穿。”有一天,媽媽不在家,我把那個包袱解開了,拿出了綠格上衣,對著鏡子在身上試了一下,確實又長又肥,可衣服的味道真香啊!
媽媽跟我說過,這件衣服是叔叔從內蒙古回東北看望奶奶時,送給媽媽的禮物。可當年媽媽舍不得穿,這件衣服一直受到特別的禮遇,專門放在一個淺白色的包袱里。
有一年,我說:“媽,你要不穿,給我穿吧?”媽媽頭也沒抬,板著臉說:“你還是小學生,不能穿這么好的衣服。”于是,我心里暗自盼著自己快點兒長大。
又過了一年,我又想穿那件綠格上衣時,媽媽一臉嚴肅地對我說:“誰家小姑娘穿這么好的衣服呀,你穿出去會讓人說你腐化。”
“腐化”?當年的我不知啥叫腐化,只覺得這兩個字聽起來真別扭。
媽媽又接著說:“學生要樸素。”“樸素”是啥意思,我好像也不是很懂,只覺得都是拒絕我穿漂亮衣服的借口。
記得我在中學讀書時,是校課外美術組的成員。暑假時,接到學校通知:隨同文化館的老師去長春看美術展。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我又想穿綠格上衣。媽媽說:“學生還是要樸素點兒好。”
雖這樣講,可能也覺得女兒第一次去省城,總也不至于穿得太過樸素。于是,媽媽在百貨商店花五元錢給我買了一件新襯衫。是白底小綠格還夾雜著隱形黃格的那種,我穿在身上照著鏡子里的自己,也覺得挺好看的,心里便也沒了怨言。
媽媽站在我的身后,看著鏡子里的我,說:“這襯衫穿上像個大學生了。學生就是要樸素大方,那種有香味兒的衣服你現在還不能穿。”
1973年,我下鄉了,天廣地闊,在四季的勞作中,我長胖了,臉也黝黑了,經常風塵仆仆地帶著鄉野之氣回家。
那一次,媽媽看我穿著爸爸那褪色不勻的舊工作服,可能是覺得過于老氣了吧,便從柜子的包袱里拿出了像寶貝一樣珍藏的綠格上衣,喜滋滋地讓我換上。可當我忙不迭地對著鏡子試穿時,連門襟都合不攏了,肩線也不夠寬了。我長大了,橫豎都不是我的衣服了。我的心里如同上了一把鐵鎖。
奶奶看到這個情景,嘆氣地說:“多好看的衣服,總想給鳳兒留著,可留著留著,穿不得了。唉……”說完,奶奶進了廚房。
其實,媽媽當時的心里一定也是酸楚的,一定更難受。至于后來,媽媽是以怎樣的心情把那件衣服疊起來,又是以怎樣的心情保管或在哪年哪月送給了誰,我是一概沒有過問的。那一刻,綠格上衣不再屬于我,綠格上衣也從我的記憶中淡出了。
工作后,我喜歡服裝設計。為了彌補我對綠格上衣的遺憾。我常會買些偏綠色的格子面料,還常常自己畫些效果圖,然后操起剪刀,大膽地裁了一件格子面料的休閑裝,是那種超長的北歐款。拿回家讓媽媽用縫紉機做,那時期我經常逛布城買面料,媽媽和奶奶也一次次地做我的打版師。
我的衣柜里掛滿了不同款式的系列服裝,可再多的服裝都替代不了我對那件綠格上衣的喜愛。
閑時總想,那種綠色有點兒偏藍調,主格旁還有暖色的細條作對比,諧調而雅致,且質地細密。市場上所見的格子料質感和色度上都有些許不足。有些染色一旦是綠色就容易有死感,質感也不夠檔次。
我幾次去大城市出差,都有意搜尋理想中的綠格面料。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內外服裝博覽及展示會信息常見報端,我設計的女時裝系列夏裝效果圖,入選了法國巴黎女裝博覽會和慕尼黑國際時裝節。同年,分別在吉林市搞了兩場青年裝和中老年裝的效果圖及樣衣展示會,受到盟市委和行業好評!
在設計中,我總是偏愛綠色。
如今,我已定居昆明二十三年了,但我的日常穿著,總少不了綠色調。
媽媽離開我這么多年了,每當想起媽媽,我就會想起那件綠格上衣,特別是在春意盎然的時節。年輕時的媽媽是多么喜歡那件上衣,又是那么舍不得穿,卻希望女兒長大穿上綠格上衣,在那樣一個不太大的小城,鮮亮亮地走在街上……
十幾年來,被媽媽包裹著的那件綠格上衣,分明是包裹著一份母親對女兒的拳拳之愛啊!在這始春的綠中,我又想起了媽媽,想起了綠格上衣。
今天,我想說:“媽,那件綠格上衣,我一直記得它的剪裁分割線和紐扣的顏色,我早已在少年時就偷偷試穿無數次了,它覆蓋過我的每一寸皮膚。”
媽媽,每當我想起您,總像是嗅到了一種幽幽的暗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