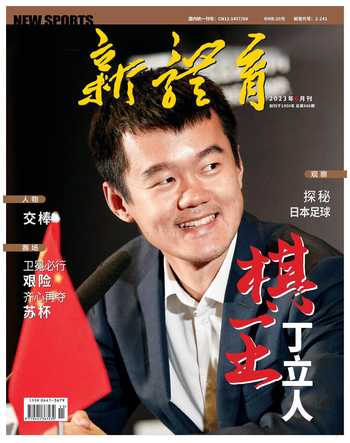探秘日本足球
金正陽 李伊凡
今年U20亞洲杯上,中國隊1比2憾負日本隊,賽后的一條評論引起了人們的注意:9年前,中國青年隊曾2比1戰勝日本隊,當時日本隊中的南野拓實、淺野拓磨、板倉滉等人如今已是歐洲五大聯賽的主力球員,而中國隊員后來的發展卻沒能達到球迷的預期。
為什么中國球員的發展高開低走?為什么當年能力克強敵的球員成年后大多泯然眾人?為什么中日足球幾乎同時開始職業化,30年后的差距竟如天塹?
本文作者面對面與一眾日本一線足球人對話,切身感受中日足球異同,對這些問題有了更深的體會。
日本足球成功,背后是數十年如一日的艱苦探索。

2023年日本超級杯決賽,橫濱水手2比1戰勝甲府風林。


日本足球曾經走過不少彎路。日本男足以參加1964年本土奧運會的陣容為班底,經歷4年沉淀后,終于在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上勇奪銅牌,迎來了歷史性突破,讓日本國民對男足的未來充滿信心。然而,這樣的成績建立在精英模式、外籍教練、海外拉練之上,不符合“金字塔模型”。對這種模式的盲目崇拜,導致日本男足后來持續低迷長達三十年。
2002年韓日世界杯后,時任日本足協主席的川淵三郎意識到,職業足球時代沿用以往的“集訓模式”已然行不通。日本足球崛起,不僅需要塔尖出類拔萃,更需要塔基堅實穩定。只有把塔基做得更大,才能通過不斷競爭與淘汰,培養更出色的職業運動員。此后,日本足協通過“船長使命”等一系列規劃指導,努力在全社會普及推廣足球運動,積極擴大足球人口。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銅牌模式的得失,對后來日本足球的發展方向有很大的啟示。
日本足球聯賽于1965年創辦,標志著進入了企業足球時代。經過20多年發展,對日本足球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但企業足球在后期暴露出的問題,阻礙了日本足球進一步成長,表明業余性質對球員們是一種枷鎖。企業足球對聯賽與足球環境帶來了很大的不穩定性。對俱樂部的持有者而言,足球只是企業對外宣傳的工具,需要圍繞企業利益開展相應活動。球隊成績好壞容易受母企業業績與經濟狀況的影響,聯賽中因母企業經營問題導致球隊受到懲罰的案例并不少見。
此外,企業足球隊最早的擁躉是企業員工,運動員和所有員工一樣從事本職工作。員工之間良好的人際關系,以及身處同一組織帶來的集體榮譽感,促使企業足球隊擁有了第一批球迷。隨著球員逐漸脫離日常工作,從以往的交際圈中分化出來,他們的身份已與職業球員無異。同事們以往對球隊的支持與熱情逐漸淡化,企業內部忠實的支持者越來越少。身為企業附屬品的球隊很難吸引到其他球迷群體的支持,人氣逐年走低。
1988年,川淵三郎上任聯賽總務主事,組織團隊開展了為期6年的調研、考察與改革,促成了“J聯賽”的誕生。這個聯賽的準入門檻包括:球隊法人化,職業球員需達18人以上,確保與地域居民、自治體和企業的三位一體化,確保分擔聯賽經費等。這些條件的限定給日本足球帶來了巨大的變革與影響。
其中,“球隊法人化”意味著球隊要擺脫對母企業的依賴與附屬,成為法律意義上的獨立法人;在財務上同樣與母企業分離,獨立核算,成為在社會上獨立運作的公司。
“確保與地域居民、自治體和企業的三位一體化”即地域密著型理念,要求俱樂部必須落戶于日本某一特定地區并融入當地社會,吸納當地企業投資入股,做到社企合一,扎根當地。這帶來的一大改變就是球隊名稱的變化。企業足球時代,球隊名稱基本由企業冠名,而J聯賽要求加盟球隊名稱必須改為“地名+昵稱”的形式。
J聯賽的全新理念吸引了許多觀眾重新走入球場,各俱樂部奉行的“巨星政策”也為聯賽帶來了非常可觀的收視率。20世紀90年代正值日本泡沫經濟的巔峰,J聯賽俱樂部相繼引進國際賽場上的超級球星濟科、斯托伊科維奇、勞德魯普、鄧加等。這些球星的到來,將J聯賽的熱度進一步推向高潮。
然而好景不長,不期而遇的泡沫經濟崩潰給J聯賽帶來了巨大的動蕩,眾多此前粗放經營的球隊紛紛出現赤字,面臨嚴重生存危機。標志性事件當屬橫濱飛翼俱樂部消亡。

經營危機使J聯盟開始反思之前的聯賽發展路線,理性務實、量入為出的指導思想逐漸使各俱樂部健康有序發展。J聯盟陸續提出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構想,力求通過開展足球運動為日本社會作貢獻。正如J聯賽三大理念所表達的精神一樣,1996年J聯盟提出“J百年構想”,高喊“體育,讓這個國度更幸福”;日本足協發布的《2005年宣言》中,暢想通過足球“為人們創造幸福的環境,為人們帶來勇氣、希望與感動”。
J聯賽時代,足球深深地融入民眾的日常生活,成為社會美好的精神寄托。日本足球在這種積極理念的指導下,通過腳踏實地的耕耘,走上了成功的道路。2017年,J聯賽已經有來自38個都道府縣的57支球隊加盟,日本國家隊也因而受益良多。
日本完整的校園足球體系與數量驚人的賽事令人印象深刻。
日本小學年齡段共有兩項賽事,分別是全日本八人制U12足球錦標賽與地區女子八人制U12足球大賽。值得注意的是,全日本八人制U12足球錦標賽允許男女同場競技。
日本初中年齡段共有五項賽事,分別是高元宮杯全日本U15足球錦標賽、全國初中體育大賽足球賽、日本U15俱樂部青年足球錦標賽、日本U15俱樂部青年足球東西對抗賽和U13地方足球聯賽。其中全國初中體育大賽足球賽僅允許初中校隊參與,日本U15俱樂部青年足球錦標賽、東西對抗賽、U13地方足球聯賽主要參賽隊伍是俱樂部梯隊,而高元宮杯的參賽隊伍中既有學校代表隊,也有俱樂部球隊。由于初中階段不同年齡球員身體發育差距較大,高年級生在其中往往會有更多出場機會。因此,為了讓低年級球員也能獲得足夠的鍛煉,U13地方足球聯賽應運而生。
日本高中年齡段目前有八項賽事,分別是高元宮杯U18足球超級聯賽、高元宮杯U18足球王子聯賽、全國高中足球錦標賽、全國高中綜合體育大賽足球賽、全國高中定時制通信制體育大賽足球賽、日本U18俱樂部青年足球錦標賽、全國少年體育大賽足球賽以及U16國際夢想杯。其中高元宮杯王子聯賽是超級聯賽的二級聯賽,其下還有兩級地方聯賽,這四級聯賽間均有升降級關系,學校代表隊與俱樂部梯隊均可報名參加。隨著聯賽制的普及,日本校園足球賽事量持續增長。
日本校園足球體系中規模最大、地位最高的比賽是全日本大學足球錦標賽。這項錦標賽包括各地區聯盟賽事以及決賽階段賽事,前者是主客場聯賽賽制,每支球隊將參加22場比賽,后者則采用集中賽地的單場淘汰賽制。為了保證比賽的激烈性與公平性,全日本大學足球錦標賽還設有專門的升降級制度。除了大學聯賽,杯賽、對抗賽、職業球隊交流賽等比賽也進一步豐富了日本大學足球的賽事體系。
由此不難看出,日本校園足球的興盛一是源自龐大且扎實的賽事體系,二是在校園足球與職業足球之間搭建了可靠的互通橋梁。自初中年齡段開始,日本青少年足球賽事中就有學校代表隊與俱樂部梯隊同臺競技的舞臺,到了高中乃至大學,二者間的交流更加頻繁。日本校園足球正是在這種賽事體系基礎上,在日本足協與職業聯賽的扶持下,得以保持與俱樂部梯隊實力接近的水平。如此來看,日本校園足球的土壤中能培育出如此多的優秀國腳便不足為奇了。
截至2022年5月1日,日本在全世界135個職業聯賽中的留洋球員已達165人。過去10年里,香川真司、南野拓實、遠藤航、三笘薫、久保健英等優秀球員在五大聯賽賽場上有過精彩的表現。在歐洲其他國家與地區的聯賽里,古橋亨梧、前田大然等日本球員也如魚得水。
日本足球運動員的留洋史始于奧寺康彥。1977年,奧寺康彥跟隨日本古河電工足球隊赴德國集訓,被科隆隊主教練看中并邀請加盟。當奧寺康彥仍在猶豫時,時任古河電工主教練川淵三郎表示堅定支持,并積極推動他成為日本足球留洋第一人。
1994年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上,日本隊在2比1領先的情況下,被伊拉克扳平,失去出線機會。“悲劇”引發日本足球界思考,也喚醒了球員們追逐世界一流足球的渴望。以三浦知良為代表的日本球員們再度掀起留洋潮,紛紛前往足球發達國家闖蕩,通過接觸高水平比賽提升自己的能力。日本足球的留洋文化就這樣慢慢走向成熟。
如今,日本足球運動員留洋人數眾多,關鍵是國內青訓的高質量,把握住了青少年的身體發育規律。青少年在不同的成長發育階段需要發展對應的運動能力,需要來自不同運動項目的刺激。只有這樣,身體素質與運動能力才能全方位發展。
科學研究表明,3-8歲是發展運動神經的黃金年齡,9歲就可開發到90%。如果在這一階段沒有給予科學的指導和充分的訓練,未來的運動能力就會受很大影響。足球技能開發的黃金年齡是9-12歲,如果此前運動神經開發得好,掌握技術動作的能力就會變強。
日本足球界有一個共識,那就是避免過早的專項化訓練。在日本,9歲以前的孩子在訓練中的足球元素占比是50%-60%,9歲以后比例逐漸增大。日本足球界認為,孩子們小時候應該體驗各種各樣的體育運動,對身體和大腦進行多樣化刺激,然后再通過提升興趣的方式給予足球練習。
除此以外,薪水也是推動日本球員留洋的一大因素。日本球員在國內的收入并不高,而前往歐洲踢球則會顯著增加他們的收入。基于此,日本優秀的球員自然會選擇前往歐洲聯賽,賺取更高收入。相應的,年輕球員在本土聯賽中獲得了更多的出場機會,也因此獲得了更大的成長空間。
責編 王敬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