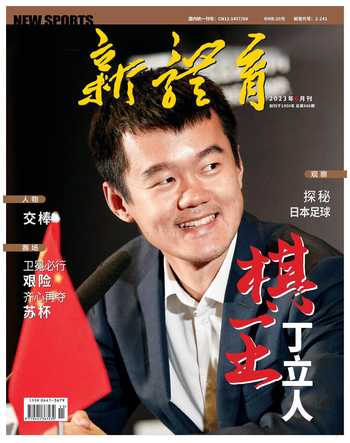特殊的群體
顏強
一個月前,我開始寫一個系列人物速寫,對象多為一面之緣卻有著一定印象的個體,系列名稱就隨便定為《一面之緣》。這本是完全隨意的寫作,與其說寫給人看,不如說是滿足自己寫作欲望,于是隨手寫的第一個個體,就是我多年前認識的一個足球經紀人。這個經紀人相當特別,因為他后來居然成了足協的秘書長。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特殊的角色轉換,從丙方變成甲方,讓這個經紀人的形象和傳聞在我腦海中留下了一定印象。既然是蜻蜓點水的“一面之緣”,那么就輕描淡寫一點浮光掠影好了。
我隨意為之的記述流傳出去后,竟然在某些網絡社區上,激發了好些憤怒的留言:“什么黑幕都不揭,寫的什么狗屁?”“現在媒體就這種水平嗎?這種人出事之前,就沒人敢發聲嗎?”“經紀人個個都該抓!”
這種憤怒讓我驚詫。本以為是自己隨筆寫得太爛,遭致這么多抗議聲,稍加留意識別,才意識到這種憤懣宣泄更是沖著“足球經紀人”,以及這個職業在目前體育風暴中有過的各種表現。
江湖傳言實在太多,而各種調查乃至結案陳詞里,留給普通球迷乃至和足球體育不相干的普通人的想象空間實在太大。從李鐵到劉奕再到更高層,從山東到遼寧再到一些國際轉會,不論已經發生還是正在調查中的種種,似乎都繞不開“經紀人”的身影。難道經紀人就是這體育黑幕里繞不過去的角色?或者像一些社交媒體發聲那樣,將經紀人都調查一番,就能還足球乃至職業體育以清白了?
不光中國體育,國際足聯似乎也拿經紀人這個行業頭疼。就在2023年4月,國際足聯又一次更改全球足球經紀人管理規定,要求新入行的經紀人必須在屬地足球管理機構參加一次從業資格準入考試。結果全球3800人參考,一半不及格……
最早,國際足聯在上世紀90年代規范經紀人管理時,不僅要求持牌經紀人需在屬地參加資格考試,并且需要各自在國際足聯注冊,其中一條要求是必須有瑞士銀行5萬瑞士法郎的存款,作為國際足聯的資格約束。國際足聯前主席布拉特在其執政后期,一度完全放開對經紀人的管理,幾乎任何想當經紀人者都可以進入這個行業,曾經的門檻一夜之間宣告作廢。
管理規定左變右改,當然有管理機構政出隨心的不負責任,也有這個行業相當復雜、難以管理的事實。這種國際管理都不規范的行業到了中國,更加南橘北枳。經紀人是什么?這應該是最古老的行業,有人類社會活動存在,就應運而生的行業。三國時代給孫權當過宰相的步騭,就是最底層的牙人出身,牙人就是經紀人——為了滿足交換需求的服務中間商。
中國足球出現經紀人,就是和足球上世紀90年代初所謂職業化改革同步的。如今看來,那一次改革既不徹底也不嚴謹,考慮和籌備完全不周全的背景下,匆忙將一項社會影響力最大、社會資源消耗也最多的運動推向了自身都未成熟的市場。其時,各種足球俱樂部從過往的體工大隊足球隊搖身一變、一夜成立,于是,球員流動的轉會需求來了;投資加大后,為了謀取競技差異優勢的外援需求也來了。這些需求對功能遠未齊備的俱樂部,根本不可能滿足,于是有了對經紀人服務的需求。
足球經紀人就是提供這樣中間服務的,更多是信息服務。然而,行業主管機構對經紀人服務的管理滯后;俱樂部急于提高成績,對經紀人需求火熱;球員提升自身價值,也需要經紀人提供中間商服務。經紀人在中國職業體育的出現,首先伴隨著各種利益交換,甚至他們本身必須成為利益交換的鏈條,將一切信任扎根于和各種決策人的私交關系中。
即便在行業管理相對嚴謹、交易相對透明的歐洲,經紀人仍被稱之為“5%先生”,完全是交換利益的代表。所有管理機構和俱樂部離不開經紀人,也絕對不會過度信任經紀人,因為各自的訴求有著本質不同。可是,在中國職業體育環境里,如果大家只是追逐利益的話,經紀人就會更加“純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