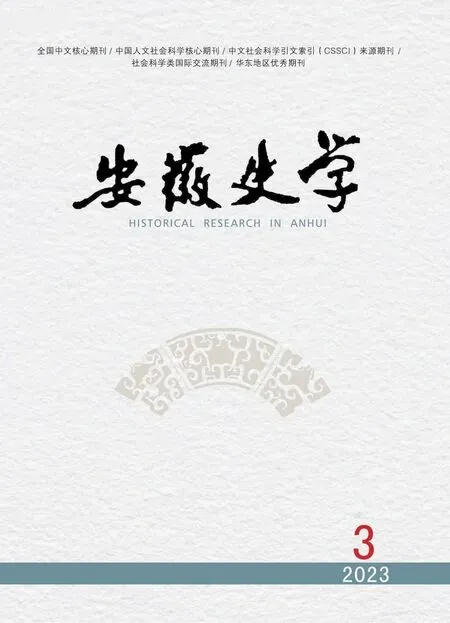清代中葉山陜、江寧商人在亳州的經營活動
——以碑刻資料為中心的考察
許 檀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350)
亳州是清代四大藥市之一,故亳州商業的研究多側重于藥材貿易;(1)參見李強:《明至民國時期亳州交通與商業發展》,《阜陽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韓本高、丁琳、劉露錦:《禹州藥市和亳州藥市比較研究》,《北方藥學》2015年第9期;王軍等:《亳州藥市及藥材種植業發展沿革考》,《中藥材》2017年第5期;徐俊嵩:《清前中期亳州的商業》,《城市史研究》第37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對在亳商幫的經營活動,僅見陳瑞對徽商的研究。(2)陳瑞:《清代淮河流域商業重鎮亳州境內的徽商——以乾隆、光緒〈婺源縣志〉為中心的考察》,《中國地方志》2008年第12期。筆者曾于2007年和2019年兩次前往亳州考察,在山陜會館和江寧會館收集了20余通碑銘,這些碑刻資料未見有人系統使用過。(3)筆者僅見陳從周《亳州大關帝廟》(《同濟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一文引用部分碑文對該會館進行介紹。本文擬以這些碑刻資料為核心,參酌其他資料,對清代中葉山陜、江寧等商幫在亳州的經營活動進行考察。
一、清代前期亳州商業的發展
亳州位于安徽西北部,與河南接壤,明代屬鳳陽府,清代雍正年間改屬潁州府。渦河自河南通許縣經柘城、鹿邑入州境,由亳州北門外東流,經蒙城、懷遠入淮河(4)光緒《亳州志》卷2《輿地志》,清光緒二十年活字本,第3a頁。,借渦河流通之便,亳州成為河南東部與江淮交流的重要碼頭和轉運中心。明代亳州已是“商賈輻輳鱗集……自城西北關及義門沿河一帶,樓舍攢拱聯絡,動計百家”。(5)嘉靖《亳州志》卷1《田賦考》,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第52b頁。清康熙年間的記載稱“亳之地為揚、豫之沖,豪富巨商比屋而居”(6)鈕琇:《觚賸》卷5《豫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頁。,“秦、晉、燕、齊、楚、豫、吳、越商賈輻輳,舟車云集”。(7)康熙十五年《關帝祠前創建戲樓題名記》,碑存亳州山陜會館,筆者于2019年11月拍攝。
清代亳州是鳳陽關的分稅口,在渦河北岸分設上下兩關,“上關在仁和街,下關在張家橋,皆近渦河北岸;上關征落地稅,下關征貨船稅,其稽查、征榷由廬鳳道委員監視,州不得與焉。”(8)道光《亳州志》卷19《食貨志·關榷》,(臺灣)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85頁。據《大清會典》記載:康熙二十五年鳳陽關關稅定額為79839兩,其中包括“并征亳州、盱眙稅課四萬一千一百一十五兩八錢三分”,(9)康熙《大清會典》卷34《戶部·關稅》,《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2輯第715冊,(臺灣)文海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7頁。以亳州稅銀占1/2計,已有2萬兩之多。鳳陽關共設稅口11處,其中“正陽一處為大關,臨淮、懷遠、盱眙、亳州四處為大口,新城、澗溪、長淮、蚌埠、符離、濉河六處為小口”。(10)兩江總督高晉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奏折,轉引自廖聲豐:《清代常關與區域經濟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頁。在鳳陽關的10個分稅口中,只有亳州、臨淮、盱眙三處有專門的《商稅則例》,也可見亳州地位之重要。
亳州的商業區在北關之外的渦河南北兩岸,各地客商、南北貨物均云集于此。乾隆《亳州志》記言:“商販土著者什之三四,其余皆客戶。北關以外列肆而居,每一街為一物,真有貨別隊分氣象。關東西,山左右,江南北,百貨匯于斯,分亦于斯。”(11)乾隆《亳州志》卷10《風俗》,《故宮珍本叢刊》第103冊,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頁。亳州的許多街巷名稱與商業經營相關,如白布街、帽鋪街、書鋪街、紙坊街、磁器街、門神街、故衣街、花子街、干魚街、打銅巷、爬子巷,姜麻市、老花市、老豆市、新市、席市、牛市、羊市、豬市、驢市等。(12)乾隆《亳州志》卷1《城池》,第31—32頁。嘉慶年間其商業街區繼續擴大,道光初年的記載稱:“亳州街市繁盛以北關及河北為最,乾隆五年舊志所列北關、河北之街巷僅三十有三,迨三十九年所列者五十有一,今自北關、河北及溝西計街巷一百一十有二,其多于前者共六十有一”(13)道光《亳州志》卷9《輿地志·街巷》,第317頁。,比乾隆中葉增長一倍還多。
清代前期來自山陜、江寧、福建、江西、浙江、湖北以及安徽本省的徽州、寧國、池州等地的商幫陸續在亳州修建了會館。表1可見,各地會館的選址多集中在北關之外。下面,筆者就利用會館碑刻等資料,對山陜、江寧等商幫在亳州的經營活動進行具體考察。

表1 清代前期亳州所建商人會館簡表
二、山陜會館碑文所見該商幫在亳州的發展脈絡
山陜會館,又稱大關帝廟,俗稱“花戲樓”,位于亳州北關外渦河南岸,坐北朝南,乾隆三十八年《重修大關帝廟》碑記載了該會館的創建和多次重修情況:
亳州北城之大關帝廟建于國朝順治十三年,首事為王璧、朱孔領兩人,皆系籍西陲而行賈于亳,連袂偕來,指不勝屈,亟謀設會館以為盍簪之地,仰承高義,俎豆蔫馨,爰創斯舉。嗣后一修于康熙二年,則郭九皋、張玉起、王桂也;再修于康熙三十三年,則梁臣、張玉鼎、陸德鳳也;又修于康熙五十二年,則李天福、梁爾祿、余文禎也。荏苒以來四十余載,木朽磚頹,漸就剝落。乾隆十九年曾有梁季賢、劉漢裔等勸募興修,規模粗就,因資糧不及半途中止。迨至乾隆三十一年,善士郭秉綸明經倡首勸募,得全興號董君繼先獨力捐資重建大殿,并塑金容,僧寮、客座,次第增設,左側以財神殿附焉,約糜金千有余兩,壯麗恢宏,美哉輪奐矣。(14)該碑文字已有部分漫漶,故轉引自陳從周:《亳州大關帝廟》,《同濟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
筆者在會館所存各碑中沒找到創建碑,所見年代最早的是康熙十五年所立的三通碑(15)這三通碑為:康熙十五年《創建府君、大王、財神廟碑記》《關帝祠前創建戲樓題名記》及一通捐款碑,均存亳州山陜會館,筆者于2019年11月拍攝。:其中《創建府君、大王、財神廟碑記》記其修建工程“起于康熙癸丑之二月,落成在乙卯之三月”,癸丑為康熙十二年,乙卯為十四年。《關帝祠前創建戲樓題名記》記言:“庀工畢力,遂于祠前,囗日而成”,創建戲樓工程似很快完成。另一通捐款碑記有:“山西平陽府、絳州信商捐貲創建關圣帝君祠前戲樓一座,并置買奉神香火地五十畝,各商姓名銀數依次附鐫于后”;該碑共鐫有捐款信商91人,捐銀超過202兩。(16)該碑最后一排12人的捐款金額不清,故實際捐款總數會更多。筆者估計府君、大王、財神三廟是由另外一批商人捐建,其人數和金額當不遜于修建戲樓,故此時匯聚亳州的山陜商人已有200家左右。
康熙三十三年的重修,也未見碑銘記載。現存一通康熙五十七年碑,正文文字部分字跡不清,捐款部分則大體可以識讀(見表2),或許反映的是康熙五十二年的重修捐款情況。該碑登錄的捐款共有96宗,約計捐銀170—180兩;其中包括京貨店、米行、弦行、鐵貨店、酒行、四月會、六月會、九月會、廿三會、潞安府囗會等十多個團體捐款,故參與本次集資的商人商號至少有一百數十家。

表2 亳州山陜會館康熙五十七年碑所鐫捐款情況分類統計表
乾隆三十一年的重修應是規模較大的一次,乾隆三十二年的碑文記載如下:
(大關帝廟)創始之由本為山陜諸商賈會館……自國初以后屢壞屢修,歷有年所,至乾隆三十一年重新大殿庭宇……公舉十三[人為]糾首,凡系出山陜而寄跡亳州者,典商以下一切囗貨懋遷,士農方技之囗志從捐例。……于歌囗囗飾后又為娛神酹愿之觀,旁置坐樓,為同人習劇之所,辟以前廡,囗為兩廊……十三人之中始終監督者郎囗綸、囗育齡、申宏、李即也,囗囗囗囗材者武金相、石先成也,其挾冊走募者郜祀先、梁統盛、段御藩、紀而璽、張炳忠、崔琦、蘇錫祿也。……同心協志,自備供餐,不辭勞勚,量力勸輸,約共計二千余金,以乾隆丙戌年六月經始,訖丁亥七月囗成。(17)碑存亳州山陜會館,碑名不詳,筆者于2019年11月拍攝。
乾隆丙戌年為三十一年,丁亥為次年。此次重修,公舉十三人為糾首,分工合作,共募集捐款二千余兩;所謂“挾冊走募者”,除在亳商人參與集資外,可能還曾赴外地募捐,惜未見捐款刊錄。
以上可見,山陜會館自清順治年間創建之后,于康熙、乾隆年間陸續添建戲樓、大王廟、財神廟、坐樓、兩廊等,乾隆三十一年“重新大殿庭宇”,“僧寮、客座,次第增設”,會館規制大體完備,規模宏敞,金碧輝煌。
不過僅相隔十數年,乾隆四十五年開始,該會館又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重修。其緣由主要是因黃河泛濫,殃及渦河,大量災民涌入會館避難,以致殿宇損毀,故于災后集資重修。乾隆四十九年《重修大關帝廟碑記》對此次重修情況的記載較為詳細,抄錄如下:

乾隆庚子為四十五年,癸卯為四十八年,甲辰為次年。此次重修從乾隆四十五年九月開始集資,四十八年二月動工,至四十九年八月告竣。此次集資立有《眾善樂輸題名記》(19)該碑未見年款,不過其中刊有董揆元在“眾綢布店”捐款之外又捐銀百兩,與碑文所記相符,可確認為此次重修的捐款碑。,該碑鐫有捐款的商行商號230余家,共捐銀696.3兩,捐錢400.335千文;其中綢布、皮毛、印局、曲糟等業均為團體捐款,故實際參與集資的商號至少有三四百家。還要說明的是,因最后一排字跡不清,所列31家商號中有24家捐款不詳,故捐款總額應超出以上統計數字。表3所列是該碑所鐫各行業的捐款情況統計。

表3 乾隆四十九年重修山陜會館各行業捐款情況分類統計表
表3可見,參與集資的各行以綢布業捐款最多,共捐銀440.6兩、錢8.2千文,已占到全部捐款的40%;其次為過載行,捐銀35.2兩、錢106千零,占比將近13%;藥材業捐款有18家缺失,故捐款所占比例肯定高于8%;皮毛業和印局捐款分別占比8.7%和7.1%;典當業雖只有3家商號捐款,但占比也達7.3%。還需注意的是,該碑所列捐款即便將最后一行的缺失部分計入也不過折合1100余兩,與碑文所載“捐輸銀一千五百余金”,還有三四百兩的缺額,應當是有一部分捐款未刊入。在大殿旁的小院中另有一通捐款碑,鐫有捐款名號14—15排,每排30余位,可能是此次集資的個人捐款部分;(20)該碑未見年款,不能確定是否為乾隆四十九年的捐款碑。如果這一估計不錯的話,參與此次集資的商人商號當有七八百家之多。
由上可見,亳州山陜會館始建于清初,康熙、乾隆年間多次擴建重修,會館的修建過程也大體反映出山陜商人在亳州的發展脈絡。康熙年間匯聚亳州的山陜商人約計200人,經濟實力尚屬有限,每次集資不過一二百兩;捐款最多者不過10兩,多為中小商號。到乾隆年間,匯聚亳州的山陜商人已增至三四百乃至七八百家,集資已超過千兩;捐款多者達到百兩,全興號董繼先甚至能夠“獨力捐資重建大殿”,足見其財力之雄厚。
三、江寧會館碑文所見嘉道年間會館的收支狀況
江寧會館位于亳州北關外之渦河北岸,據碑文記載:該會館為“江寧合郡眾商酹神之所,正殿供奉關帝神像,每屆春秋二季以及圣誕之辰演囗致祭”;又于廟旁公置隙地2畝,為寧郡商賈在亳物故者之義冢。(21)道光十年三月廿八日《告示》,碑存亳州江寧會館,筆者于2007年10月抄錄。
江寧會館的創建始于清初,因“廟宇歲久傾頹,義地墳多土窄”,乾隆五十七年董事吳恒源、楊安吉等公議重修,“各號緣金,每年利權子母……迨至嘉慶十二年間大工告竣”。(22)道光十年八月李音垿撰“重修江寧會館碑”,該碑原無碑名,現名為筆者根據內容所擬,碑存亳州江寧會館,筆者于2007年10月抄錄。此次重修之后的會館,“自大殿、戲臺以及后樓、廊舍縈迴周至”,金磚布地,白玉為堂,“座上八寶莊嚴,階下雕欄砌錦”(23)⑤道光十年九月李佳言撰“重修江寧會館碑”,該碑原無碑名,現名為筆者根據內容所擬,碑存亳州江寧會館,筆者于2007年10月抄錄。,其華麗精巧雖不及山陜會館,但也稱得上規模宏敞,氣象巍峨。會館重修雖于嘉慶十二年 “告竣”,但還有不少后續工程,故直到道光十年才刊碑以紀。
江寧會館的重修未見捐款記載,其經費當主要來自會館所收房租、厘金等公項以及“利權子母”的生息所得(詳下)。不過“殿閣之所需,神前之供品”則為同人踴躍捐輸,并開列有“眾號樂助各殿囗囗器物等件芳名”,所捐物品共計48宗,包括神幔、供器、角燈、桌椅、桌圍椅褡,以及銅盆、鐵罄、銅鈴、茶洗等各種用具。這次捐輸中有行業公捐,如江漢藥幫“公捐大殿中明角燈二對”,銅錫行“捐囗囗殿神幔一副,桌圍一條”;有多家商號合捐,如同興坊、西祥順等11家商號“公捐大殿囗門一副”;也有一家商號獨捐,如三進齋“捐大殿中明角燈二對,真人神幔一副,真人供桌一張,小錫供器全副”;還有多次捐輸者,如楊乾順號“捐地藏殿嗶嘰神幔一副、觀音殿繡白綾神幔一副、銅盆兩個”,并與樂壽堂、張起鳳、李大有等合捐桌圍、角燈、繡緞神幔、紅布照圍等。此次捐助者中可確認為商號者39家,人名20個⑤,再加上江漢藥幫、銅鎖行、銅金行、銅錫行等團體捐助,實際參與捐物的商人商號可能將近百家。
會館“大工告竣”之后,江寧商人于嘉慶十二年至道光十年曾兩次集資,并分別刊碑開列了“出入細賬”和“入出總目”,據此我們可對嘉道年間會館的收支狀況有一些較具體的了解。
其一,為籌措會館重修的后續工程和日常開支,江寧商人于“嘉慶十二年至道光十年四月初四日”抽收厘金和征收門面錢等項,共收入4180.388千文,支出3669.815千文(24)道光十年八月李音垿撰“重修江寧會館碑”之“嘉慶十二年起至道光十年四月初四日止出入細賬”。,并于道光十年八月刊碑詳細開列其“出入細賬”,詳見表4、表5。

表4 嘉道年間江寧會館的各項收入統計表

表5 嘉道年間江寧會館的各項支出統計表
表4所列各項收入中,“抽厘”當是按照某一議定比例向各行業提取的積累,合計為2135千文零,占收入總額的51.1%;門面錢應是會館出租門面房的房租收入,占收入額的35.8%;以上兩項是會館收入的主要來源。其中的“八行”,應是指租賃會館門面房的八個行業,至少應包括抽厘較多的藥材、京貨、紙、染等行,花子、門神、嫁妝、銅行、油漆等行是否均包括在內則未可知。
表5所列各項支出中,工程開支1360余千文,占支出額的37.2%;日常開支2207千文零,占比60.1%;此外,買地10畝,支出98.7千文;三項合計共支出3669千文有奇, 占收入總額的87.8%,尚有12.2%的余款。在工程開支中,油漆大殿、后樓、戲臺等處和建造觀音殿,應屬會館重修工程的未完之項。至于“還墊款”一項,是因嘉慶十二年會館“大工告竣”之際虧空“用土錢一千串”,系由19家商號墊付,當時議定每月從“大賬抽還錢一千文”,“自十三年起至十八年止”分三次共支付了450千文;至于下欠之550千文,19家商號“皆情愿將此項以作樂輸”。(25)道光十年八月李音垿撰“重修江寧會館碑”。
其二,樂善堂的“入出總目”。樂善堂的緣起為嘉慶十二年會館工程告竣后,首事吳恒源等考慮到會館義冢“積年停厝既多,搬還鄉者甚少”,故“邀集同人”集資,“將所捐之項妥議經營,以作搬柩囗鄉之費”,并立堂名為“樂善”。(26)道光十年《江寧會館樂善會碑記》,碑存亳州江寧會館,筆者于2007年10月抄錄。《江寧會館樂善會碑記》中有“樂善堂入出總目”,開列了此次集資的捐款名號,計63宗,共捐錢1297.645千文。此外,該善堂還有房租和歷年生息收入,其中房租收入3191.074千文,占收入總額的60.1%;歷年生息錢816.246千文,占比15.4%。以上三項收入合計為5304.965千文。(27)此處的5304.965千文系累計數,與原碑所載5260.22千文略有出入。
樂善堂的各項收入除用作搬柩返鄉的開支外,還大量添置會館資產,購買市房或買地自建,表6是“樂善堂入出總目”所列的各項支出統計表。

表6 嘉道年間樂善堂的各項支出統計表
表6可見,搬柩費用581千零,僅占支出額的15.2%,占搬柩捐款1297千文的45%。在樂善堂的各項開支中購買和修建市房是最大一項,占支出額的62.8%;而房租收入乃是樂善堂收入的最大宗。可見,不斷添置市房出租獲利是江寧商人維持會館各項開支的主要經費來源。
以上對會館“出入細賬”和“樂善堂入出總目”兩筆收支的分析可見,二者雖各有側重,但都是江寧會館嘉慶十二年至道光十年的賬目,筆者將其合并為嘉道年間江寧會館的收支總賬(見表7),其中“搬柩”集資應屬專款專用,故在收、支項下均予剔除。

表7 嘉慶十二年至道光十年江寧會館的收支統計表
先看收入部分,房租、抽厘和生息款是江寧會館的主要收入來源。其中房租收入占總收入的57.2%,是會館收入的最大宗;抽厘占比26.1%,也是一項重要收入;歷年生息款占比11.4%。
再看支出情況。各項支出共計6905千零,占總收入的84.3%;存留余款1280余千文。其中,工程尾款即重修會館的后續工程,支出1360余千文,占支出總額的近20%;添置資產是支出的最大宗,從嘉慶十二年至道光十年的20余年間,江寧會館陸續添置了市房4處(包括買地自建),購地10畝,支出2490余千文,占支出額的36.1%,占總收入的30.5%。但這兩項都不是會館的日常性開支,會館的日常開支主要是歷年對市房、義地的維修,祀神演戲、和尚養廉以及其他雜項支出,合計3040余千文,占支出總額的44.1%,占收入總額的37.2%。換言之,江寧會館每年的收入除支付日常開銷之外有很大剩余,故而才能不斷添置資產,并且在會館重修之際并不需要山陜會館那樣的大規模集資。
以上考察可見,清代中期亳州江寧商幫的規模遠不如山陜商幫,總計不到百人;其經營的商貨包括藥材、京貨、紙張、嫁妝、銅器、油漆等,尤以藥材為最。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江寧會館的收入中有30%用于添置資產,反映了其規模和實力正在不斷發展壯大之中。
四、山陜、江寧等商幫在亳州經營的主要商品和行業
前已述及,清代亳州是鳳陽關的分稅口,并有單獨的稅則。不過“亳州無論商船、陸販,均依旱稅例征收”(28)光緒《鳳陽府志》卷12《食貨考·關榷》,清光緒三十四年活字本,第67b頁。,故亳州的稅則均為旱販稅則,包括衣物、用物、食物、雜貨四個部分,共開列有皮衣、氈衣、布帛、鞋帽、綢緞、紗羅、綾絹、絨褐、皮張、磁器、鐵器、竹木器,茶、酒、煙、糖、果品、藥材、顏料、紙札,以及金銅鉛錫鐵雜貨、諸色零星雜貨等60多類七八百種商品。其中藥材、綢緞、布匹、紙張、糧食、雜貨等是經由亳州流通的較大宗的商品。
(一)藥材業
亳州是清代四大藥市之一,藥材是各地商人經營的重要行業,《亳州口旱販雜貨稅則》中列有藥材130余種(29)乾隆《戶部則例》卷76《稅則·鳳陽關》,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05—706、703頁。,而亳州本地輸出的藥材主要為亳白芍、亳菊花等。(30)王軍等:《亳州藥市及藥材種植業發展沿革考》,《中藥材》2017年第5期。
亳州的山陜商人有不少經營藥材,前引乾隆年間《眾善樂輸題名記》中,藥材業有71家商人商號參與集資,僅藥材行就有13家,計有弘裕行、月盛行、宏源行、永隆行、義興號、張庭囗、萬順堂、張天成、大慶號、呂協盛等,捐錢35.16千文;尤以弘裕、月盛兩行捐款最多,并募集了大量客商捐款。山陜商人中經營藥材者可能以陜商為多,亳州山陜會館現存道光初年陜西藥材幫捐鑄的鐵旗桿和香爐可證,旗桿底座的銘文為:“陜西眾藥材幫弟子敬獻鐵桿一對,永保十方平安,吉慶有余”;香爐的銘文為:“大清國江南潁州府亳州北關山陜廟薰爐一座,重三千斤”,“陜西眾藥材幫弟子敬叩”。
藥材也是江寧商人經營的主要行業,江寧會館嘉道年間的厘金收入中,“藥材厘件”1150余千文,占各行抽厘總額的一半還多;“花子、門神”二行厘金68.978千文,“花子”行,即“從事季節性的白芍刮皮”(31)亳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亳州市志》,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140頁。的藥材加工業。江寧商人中有“江漢藥幫”,漢口是長江中游重要的藥材集散中心,該藥幫可能專門在漢口與亳州之間往來販運。
亳州本地商人也有不少經營藥材,三皇廟即為藥商會館。地方志記載:三皇廟在鐵果巷,“康熙二十四年建,雍正十年藥商修為會館”(32)光緒《亳州志》卷4《營建志·寺觀》,第32b頁。,這些藥商估計以亳州本地商人為主。亳州藥商在河南各地藥市中都很活躍,密縣洪山廟藥市的振興活動中有26家亳州藥商參與;禹州創建十三幫會館也有亳州藥商的捐款。(33)參見許檀:《清代晉商在禹州的經營活動——兼論禹州藥市的發展脈絡》,《史學集刊》2020年第1期。
(二)綢布業
乾隆年間重修山陜會館題名碑中,綢布業捐款440余兩,占該碑所鐫各行業捐款總額的40%。可見,綢緞布匹是山陜商人經營的重要商貨,也是經由亳州轉運的大宗商品。鳳陽關檔案記載:“絲綿、綢緞、布匹等項,全賴浙江、蘇松”;(34)安徽巡撫趙龍乾隆二年十月十二日奏折,轉引自廖聲豐:《清代常關與區域經濟研究》,第185頁。地方志則稱,“蘇杭綢緞、雜貨由浦口起旱,至長淮雇船,運赴潁、亳、河南等處”。(35)乾隆《鳳陽縣志》卷3《輿地志·市集》,清光緒二年重刊本,第13b頁。亳州的綢緞布匹主要來自江南,銷往河南開封等處。山陜商人中有來自潞安者,《亳州口旱販用物稅則》中列有:上潞綢每匹稅一分五厘,次潞綢每匹稅七厘八毫⑨,潞綢到關當有一定數量。
亳州也是棉布的集散轉運碼頭,該城北關外的白布街當是布店匯聚之處。《亳州口旱販用物稅則》布匹項下列有:紫花布、白標布、斜紋布、江陰布、順昌布、葛布、夏布、麻布、紅花布、飛花布等20余種,地方志也有“中梭布,十匹征稅銀一分八厘”的記載。(36)道光《亳州志》卷19《食貨志·雜課》,第787頁。其中紫花布、標布、梭布、江陰布等產自江南,葛布、夏布來自江西。檔案記載:“江西一路所產磁器、紙張、葛夏布匹及本地煙葉等物向系在正陽關報稅”。江西商貨經廬州北上赴河南,多于正陽關東北五十里之河口分道,“水路則從瓦埠由此河口橫穿淮水入淝河,經鳳臺、蒙城、太和等境至豫省,旱路則由鳳臺境之古壽唐關,過下蔡家溝等集,經蒙、亳諸境至豫省”。(37)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藏清代鈔檔:戶部尚書海望等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九日題本。
(三)紙張、門神業
亳州經營紙貨和門神業的商人為數不少,北關外有專門的紙坊街和門神街。《亳州口旱販雜貨稅則》“紙札”項下列有:扛連、川連、連四、連七、毛邊、切邊、黃表、表心,以及烏金紙、砑花紙、木本紙、桑皮紙、油紙、色箋、柬帖等20余種,在“雜色紙貨”項下還有“門神紙囗,每箱各稅八分”。(38)⑨乾隆《戶部則例》卷76《稅則·鳳陽關》,第706、689頁。
亳州火神廟保留有兩通雍正十三年的重修碑銘(39)這兩通碑均存亳州山陜會館,筆者于2019年11月拍攝。,其一記言:“維神赫赫,正位離方;……敬建祠宇,奠茲一邦。歷年既久,風雨為殃;檐廡剝落,神像囗光。爰有眾善,合力贊勷;山門煥然,殿陛軒昂。尚囗神像,永新金妝;感召善信,門神紙商。合浮圖興,金碧輝煌;配享眾圣,粲然一堂。莊嚴既興,神報自囗;春秋囗囗,錫福無疆。”顯然,此次火神廟的神像“金妝”是由紙商和門神業所主持。該碑所鐫捐款商人張同春、傅子祥等10人估計是紙商,共捐銀12.5兩;“眾門神店共助銀二兩九錢”,合計15.4兩。另一碑記載:“妝修火神老爺神廚、隔扇、脊檐、山門、甬道,捐貲眾善姓名開列于后,祈保闔郡平安,廟貌永固”。該碑所鐫捐款商人商號60余家,共捐銀28兩有余,應當屬前碑所言之眾善“合力贊勷”。
江寧商人中也有專門經營紙張和門神業者,嘉道年間江寧會館的抽厘中,紙、染二行抽收厘金236.58千文,花子、門神二行抽收68千文有奇。亳州本地商人也有以造紙為業者,如“州中向有收買切邊零塊碎紙,泡爛造紙之家”;又“安家溜有十余家紙坊”。此外,州志物產項下“貨之屬”列有楮紙(40)乾隆《亳州志》卷10《物產》,第207頁。,說明亳州本地所產紙張當有一定的輸出量。
(四)糧食及其加工業
《大清會典》記有“鳳陽關之亳州口不征船料,止征米稅”(41)嘉慶《大清會典》卷16《戶部·貴州清吏司》,《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4輯第633冊,第827頁。,可見糧食也是經由亳州流通的重要商品。檔案記載:“鳳陽關稅雜貨不過十之二三,豫省米豆有十之七八。緣開封、歸德、光州、固始等處素產米豆,水路相通,各商采買,由鳳陽關運赴下江糶賣。蓋下江糧價較豫省為昂,是以豫省豐收則商販云集,檣帆絡繹,關稅豐盈。”(42)《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32輯,李質穎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奏折,臺北故宮博物院,1982年,第736頁。開封、歸德等府的糧豆大多會由渦河經亳州運往江南。山陜商人有經營糧食業者,如康熙五十七年的集資中,有米囗行和米行眾客的捐款;亳州的其他商幫估計大多也會經營糧食。
酒、曲等糧食加工業也是山陜商人經營的重要行業,分別設有酒行、曲坊、糟坊。如在乾隆年間山陜會館的集資中“大曲糟坊”捐錢45千文,占各行捐款的4%;山陜會館現存的一通道光年間碑銘中開列有曲坊、糟坊字號80余家。(43)碑存亳州山陜會館,碑名不詳,筆者于2019年11月拍攝。與亳州相鄰的河南周口、朱仙鎮等處都是晉商開坊踏曲的重要碼頭,“每商自數十萬以至百余萬塊不等,車載船裝販運他省”。(44)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5《河南疏四》,《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46頁。亳州的曲坊、糟坊數量眾多,可能也有曲、酒等商品的輸出。
(五)雜貨業
鳳陽關稅“雜貨不過十之二三,豫省米豆有十之七八”,由河南南下的商貨以米豆為主,從江南北上的船只則主要裝載雜貨。經由長淮口之“滿料雜貨船,查系前往亳州報細(稅)者,每船俱征船料銀五錢三分;不足船料者照臨淮口旱販例科稅”。(45)乾隆《戶部則例》卷76《稅則·鳳陽關》,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05—706、703頁。所謂“雜貨”涵蓋甚廣,綢緞布匹、紙張、京貨、銅錫鐵貨、木材等均可包括在內。綢布、紙張等前已述及,下面來看其他各項。
山陜商人開設有京貨店、鐵貨店,《亳州口旱販雜貨稅則》記載了“京雜貨每箱稅一錢二分,每扁稅六分,每匣稅三分”的征稅標準,惟具體商品不詳。山西澤潞地區是清代北方最重要的鐵器制造中心,所產“鐵絲、釘子、鐵鍋、鐵爐子、鐵犁、車輪子和各種工具的配件”等鐵貨(46)[德]李希霍芬著,李巖、王彥會譯:《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372頁。,多經由河南清化鎮南下銷往華北、江淮各地。《亳州口旱販用物稅則》中列有:鐵鍋每百口稅二錢,鐵釘每百斤稅三分二厘,又有大中小鐵鎖以及雜販生、熟鐵貨等的稅額。(47)乾隆《戶部則例》卷76《稅則·鳳陽關》,第704、706頁。《山西通志》記言“潞鐵作釘,為南省造船所必須,取其易銹也”(48)光緒《山西通志》卷100《風土紀》,《續修四庫全書》第64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頁。,故運至亳州的鐵貨中當有一部分轉銷江南。此外,亳州志物產項下“貨之屬”列有弓弦,山陜商人的“弦行”或即經營此類商品。
江寧商人也有不少經營京貨、銅錫器者,嘉道年間江寧會館的厘金收入中“京貨厘件”620余千文,約占各行抽厘總額的15%;銅鎖、銅金、銅錫等行都參與了會館重修的物資捐獻,不過在會館抽厘中,嫁妝、銅行、油漆三行共抽收厘金54.34千文,經營規模似屬有限。此外,《亳州口旱販雜貨稅則》中開列有不同規格的桱木和桱木板的稅額(49)乾隆《戶部則例》卷76《稅則·鳳陽關》,第704、706頁。,江寧商人中有專門經營“桱木行”者,至少有詹華囗、任德盛、詹中寬、合興號、汪全泰、查永亨、吳長升、詹囗一、詹囗輔、查際泰、囗恒利、詹務本、協振號、詹隆興、公盛號、囗敘興、太生號、詹樹于等20余家商人商號,并設有“房屋廠基與客堆貨”。(50)乾隆三十五年《告示》,碑存亳州江寧會館,筆者于2007年10月抄錄。
(六)皮毛加工業
皮毛加工是亳州較重要的手工業,州志記載:“工無奇巧……惟斂皮斂革,集毳成旃,故毞毲羊羧之屬頗以緊薄均調著名”。(51)乾隆《亳州志》卷10《風俗》,第202頁。經由鳳陽關輸出的商品中,“潁多粟,亳富藥材、氈剡、皮革”(52)光緒《鳳陽府志》卷12《食貨考·關榷》,第68a頁。,可見皮毛制品也是亳州輸出的重要商品。乾隆年間山陜商人的集資中有“眾帶毛作坊”和“眾帶毛作坊公會”,共捐錢95千文有余,占行業捐款總額的8.7%。皮毛及其制品是陜西的重要特產,當地商人“挾貲遠賈,率多鬻皮為業”;(53)乾隆《大荔縣志》卷6《風俗》,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第4b—5a頁。河南賒旗、朱仙鎮的皮毛業多為陜商經營(54)參見許檀:《清代河南賒旗鎮的商業》,《歷史研究》2004年第2期;《清代河南朱仙鎮的商業》,《史學月刊》2005年第6期。,亳州的皮毛業可能也以陜商經營為主。
(七)過載行
亳州作為水陸轉運的重要碼頭,過載行是其重要行業之一。在乾隆年間山陜會館《眾善樂輸題名記》中,參與集資的過載行有正超凡、任澤遠、趙廷川、張三剛、柴開先、王恒惠等6家,其中在王恒惠、柴開先等4家過載行名下捐款的客商多達140余家。表8是重修山陜會館過載行及其眾客的捐款統計。

表8 乾隆年間重修山陜會館過載行及其眾客的捐款統計表
表8可見,在王恒惠、柴開先、張三剛、其盛等過載行名下捐款的商號多者四五十家,少者亦有20余家,這些商號應是在亳州轉運商貨,由過載行代為辦理,故而才會在該行名下捐款。除山陜商人之外,亳州本地商人當也會經營此業。
亳州從事中介貿易的牙行也為數眾多。據州志記載:“亳州牙行系雍正年間定額,共一千四十余家,分上中下三則完稅,每年上則完稅八錢,中則完稅七錢,下則完稅六錢”,額征牙稅銀961.3兩。(55)道光《亳州志》卷19《食貨志·雜課》,第786—787頁。此項稅額為地方商稅,由州征收,從事牙行業者當以本地商人為主。乾嘉年間因連遭水災,亳州牙戶逃亡390余名,至道光元年豁免稅銀263兩,實征牙稅銀698.3兩。即便如此,亳州的牙行、牙稅數量仍遠超過鳳陽、潁州兩座府城。(56)清代中葉,鳳陽府城征收牙稅銀121.8兩,潁州府城牙稅銀128.7兩,參見乾隆《鳳陽縣志》卷6《賦役》、道光《阜陽縣志》卷4《食貨志》。
結 語
綜上可見,亳州是清代中葉皖北、豫東地區的商業中心,河南糧豆,江浙綢緞、雜貨等于此轉輸,藥材也是其中一項重要商品。北關之外的渦河南北兩岸是亳州的主要商業區,山陜、江寧、福建、江西、浙江、湖北以及安徽本省的徽州、寧國、池州等地商幫均在此建有會館,其中以山陜商幫規模最大。碑刻資料顯示,康熙年間匯聚亳州的山陜商人約有200人,經濟實力尚屬有限;到乾隆年間山陜商人已增至三四百乃至七八百人,經濟實力也大大增長。從乾隆四十九年重修山陜會館的集資可見,藥業捐款約占各行業捐款的8%—10%,而綢布業占比高達40%,過載行、皮毛加工等在山陜商人經營中也占有較重要地位。江寧商幫的規模遠不如山陜商幫,總計不到百人;不過嘉道年間該會館的收入大量用于添置資產,顯示出較強的發展態勢。江寧商人中經營藥材者相對較多,其次是雜貨和紙張業,在會館抽厘中藥材厘金占比超過50%,雜貨、紙張等約占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