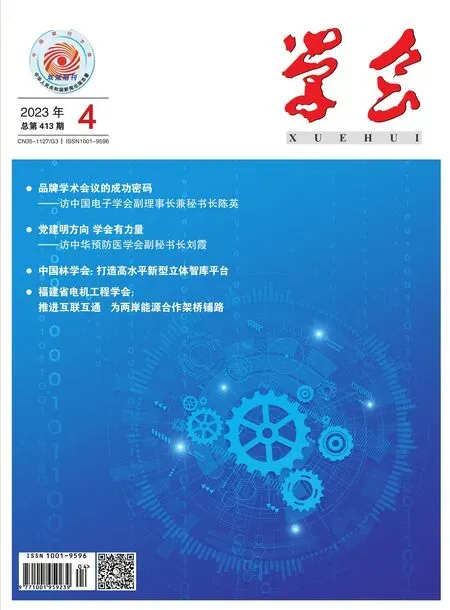共同富裕視域下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路徑研究*
——以浙江省為例
高燕 孫凱麗
共同富裕的本質是實現全體人民物質富足與精神富有的統一。新時代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激發經濟發展活力,優化收入分配制度,創新社會治理機制,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推進生態文明、精神文明建設。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不可或缺的主體之一,社會組織在實現共同富裕發展目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何規范引導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解放和激發社會活力與創造力,加快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一直是黨和國家以及地方黨委、政府研究推進的工作重點。2021 年,浙江省委辦公廳、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意見》,從強化黨建引領、準入管理、扶持培育、部門協同、作用發揮、保障機制六個方面提出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為社會組織助力共同富裕事業指明了方向。從浙江省社會組織發展情況來看,社會組織依然存在區域分布不均、類型結構欠佳、高素質人才缺乏、監督機制有待健全、發展環境有待優化等問題,與助力共同富裕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尚有一定距離。為此,本文基于調研資料進行總結分析,探索浙江省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的路徑,推動社會組織在共同富裕新征程中作出更大貢獻。
一、社會組織發展現狀
(一)數量規模
根據《浙江省社會組織發展藍皮書2016—2020》,2016—2020 年,浙江省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總數呈穩定增長態勢。截至2020 年底,在浙江各級民政部門依法登記的社會組織達71256 家,其中社會團體25856 家、民辦非企業單位44573 家、基金會827 家。浙江省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總數之和占浙江省社會組織總數的比例超過98%,發展勢頭迅猛,基金會則存在很大發展空間。
(二)地域分布
浙江省各設區市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數量與經濟發展程度呈正相關,經濟發達的區域,社會組織分布多,經濟相對欠發達的區域,社會組織分布少。杭州、寧波、金華、臺州、溫州、紹興諸市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數量在2016—2020年間呈顯著增長態勢。其中,2020 年杭州市社會組織數量最多,為12099 家,占全省社會組織總數的16.98%;嘉興、湖州、衢州、舟山、麗水諸市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數量呈緩慢增長態勢,其中,2020 年舟山市社會組織數量最少,僅有1439 家,占全省社會組織總數的2.20%。
(三)行業類型
浙江省社會組織行業類型日益豐富,包括教育類、衛生類、科學研究類、生態環境類、社會工作類、體育類、文化類、法律類、工商業服務類、宗教類、農業和農村發展類、職業及從業者類、國際及涉外和其他類型的社會組織。其中,2020年社會工作類社會組織數量最多,為25930 家,占36.39%。社會組織涉及較多的行業還有文化、體育、衛生、農業及農村發展和科學研究類,而生態環境、法律、宗教、職業及從業者、國際及涉外類社會組織較少。
(四)黨建工作
黨的十八大以來,浙江省社會組織持續推進黨組織建設,堅持黨建帶群團,凝心聚力共謀發展。浙江省建立黨組織的社會團體數量逐年增加,黨組織建立工作成效凸顯。截至2020 年,建立黨組織的社會團體數量增至4042 家,民辦非企業單位黨員人數達7.07 萬,共青團員人數為19.89 萬,民辦非企業單位黨群建設總體穩中求進。此外,浙江省社會組織積極打造黨建品牌。例如,杭州市西湖區社會組織綜合黨委通過“黨建+公益”打造具有西湖特色的社會組織黨建新品牌,為浙江省社會組織黨建工作推進提供了“他山之石”[1]。
(五)發展成效
經過多年的培育發展,浙江省社會組織的成效日益顯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浙江省社會組織涉及領域十分廣泛,為勞動者提供了多元的就業崗位,吸納就業人員50 多萬,緩解了浙江省就業壓力。二是行業協會商會在規范市場經濟行為、引導企業轉型升級、激發經濟整體活力、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2]。三是社區社會組織作為社區治理主體之一,在提升基層治理能力、滿足居民多樣化服務需求、維護社區穩定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浙江省約有9 萬個社區社會組織,動員300 多萬名志愿者參加疫情防控工作,充分體現了浙江省社區社會組織在基層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社會組織發展存在的問題
“十三五”期間,浙江省社會組織的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面對“十四五”時期的新發展要求,社會組織還存在一些短板,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內部層面
第一,區域分布不均衡。截至2020 年底,浙江省社會組織主要分布在杭州、寧波、溫州、金華和臺州,5 市的社會組織數量之和占全省總數的65.45%。嘉興、紹興、衢州、麗水、湖州、舟山較少,6 市的社會組織數量之和僅占全省總數的31.28%。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縮小區域差距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之一。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過程中,社會組織在優化區域產業結構,促進區域項目合作、經濟協調發展、環境協同治理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由于區域分布差異較大,浙江省社會組織在推進共同富裕進程中難以發揮應有的力量。
第二,類型結構欠佳。浙江省社會組織行業類型占比如圖1 所示,主要分布在社會工作類、教育類和其他類型領域,三者占比之和高達78.71%,而生態環境類、法律類、宗教類、職業及從業者、國際及涉外社會組織占比均低于1%,科學研究、衛生、文化、體育、工商業服務、農業及農村發展類型的社會組織規模也遠小于教育類和社會工作類社會組織。浙江省社會組織類型雖然覆蓋廣泛,但一些領域的社會組織扎堆,另一些領域卻起步維艱,結構缺乏科學性、合理性的狀況十分突出。

圖1 2020 年浙江省社會組織行業類型占比
第三,缺乏高素質人才。高素質專業人員可以為社會組織提供專業知識和技能,拓展服務范圍、創新服務項目、改善服務質量。因此,建立一支規模宏大、素質優良的人才隊伍,是實現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截至2020 年,浙江省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共計657879人,其中,具有大學專科及以下學歷的人員占總數的81.38%,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員占18.62%。可見,在社會組織從“高速發展”到“高質量發展”轉型中,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學歷水平較低,發展缺乏相應的人才保障。
(二)外部層面
第一,監督機制有待健全。對社會組織的監督除了法律規制和行政監管以外,還需要其他機構、組織、社會大眾的協同作用,形成一個多層次的社會組織監督系統,共同規范社會組織的運作。浙江省現行法律法規未對何種機構、組織和公眾可以采用何種方式對社會組織進行監督作出明確規定,致使社會公眾參與監督的積極性、主動性較低。在實際生活中,即使社會公眾行使自己對社會組織的監督權,比如采取上訪、舉報或向媒體曝光的方式,也難以有效遏制非法運營,對社會組織的監督效果微乎其微。
第二,發展環境有待優化。社會組織的發展內嵌于特定的社會環境,社會環境對社會組織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99 公益日詐捐”事件引起社會大眾廣泛熱議,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談及公益總是擔心自己的善心成為他人炫耀的資本[3]。此后,雖然國家對社會組織領域進行了洗削更革,但效果有限。受社會環境的潛在影響,社會公眾始終會對社會組織抱有懷疑態度,這無疑加大了社會組織發展的難度。
三、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的優化路徑
(一)完善黨建工作機制,實現黨的組織和工作全覆蓋
在新征程中,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和政治優勢,也是浙江省社會組織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加強黨對社會組織的全面領導需完善社會組織黨建工作機制,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黨組織應對社會組織的黨建工作進行分級管理;行業黨組織、屬地基層黨委和社會組織綜合黨委應承擔脫鉤后行業協會商會的黨建工作;城鄉社區社會組織的黨建工作應由社區(村)黨組織負責。此外,應積極倡導具備組建黨組織條件的社會組織建立黨組織。對于不符合組建條件的社會組織,可通過行業、區域統籌的方式聯合建立黨組織。同時,要加快建立社會組織黨建工作經費保障機制,確保黨組織應建盡建。對社會組織進行評估時,應將黨建工作作為評估指標之一,助推黨建工作的開展,進而實現黨組織和工作的全覆蓋,提高社會組織發展質量。
(二)優化社會組織區域布局,促進省域均衡發展
浙江省社會組織多集中在杭甬溫地區,經濟相對欠發達的設區市社會組織分布較少。基于此,在未來社會組織發展中,應從區域的協調發展出發,制定交流合作政策,促進不同區域間社會組織的相互學習和提高。積極探索建立“結對子”幫扶的激勵機制,鼓勵經濟發達地區的社會組織“走出去”,傳播發展經驗,激勵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社會組織將先進發展經驗“引進來”,形成發展合力[4]。鼓勵基金會等慈善組織增強動員能力、創新籌款方式,以資金扶持、產業開發、項目幫扶等形式賦能欠發達地區,對地區內創新性強、潛力大的社會組織,政府應予以政策和資金支持,增強其輻射力,帶動區域內“散”“弱”“小”社會組織的發展,促使社會組織的服務范圍更大、覆蓋面更廣、質量更高、發展更均衡。各級政府要重視社會組織參與共同富裕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加大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和轉移職能的力度,讓社會組織在提供和優化公共服務上有足夠的發展空間,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做出新貢獻。
(三)優化社會組織類型結構,促使其趨向科學合理
堅持以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為導向,依據協調發展、門類齊全、統籌城鄉、功能完備的原則和要求,對社會組織進行科學孵化培育,促使浙江省社會組織類型結構更趨科學合理。首先,加快培育和發展慈善類社會組織,強調其精細化定位,避免同質化發展。政府應鼓勵慈善類社會組織專注于扶貧、濟困、扶老、救孤、助殘、助學等慈善目的,基于慈善目的進一步培養專業人員開展服務、籌集善款的能力。其次,行業協會商會堅持“一業一會”“一地一會”的組建原則,重點培育和扶持“互聯網+”、生命健康、新材料領域的行業協會商會,并加大對科學研究類社會組織發展的資金支持力度,推動創新強省工作在最短時間內實現質的躍升。再次,應大力培育發展養老照護、法律援助、環境保護、文體娛樂和農村生產技術服務的社區社會組織,引導各地將政策、資金、人力等資源更多用于社區社會組織建設上,積極探索“六社聯動”新模式,為參與社區治理、提供社區服務、促進社區和諧發展提供新起點。最后,要大力發展樞紐型社會組織,發揮它們在“政社”“社社”“社企”聯系與合作中的橋梁紐帶作用,強化社會組織間的聚合力,促進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
(四)完善人才培養機制,加強高素質人才隊伍建設
高學歷、高素質、專業化人才的匱乏在較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組織的發展。社會組織要發展,人才是關鍵。首先,政府應加大對社會組織先進事跡的宣傳,提高社會組織的公信力、知名度,吸引更多高素質、專業化人才加入社會組織的建設和發展中。其次,政府應把社會組織人才培育納入浙江省人才隊伍建設和人才隊伍知識更新工程中,積極與高校、科研機構、企業聯手,形成“四方聯動”的人才培養模式,共建社會組織人才培養培訓基地,加快培養社會工作、慈善管理等領域的人才。再次,政府應監督社會組織落實人才引進、人才激勵、社會保障制度,提高社會組織專業人才社會地位和工資福利待遇,暢通其申請人才補助、住房補貼、人才落戶渠道,保障專業人才各項權益[5]。最后,創新數字化賦能,形成“數字+人才”培養模式,研發學習培訓模塊,將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納入繼續教育范疇,定期開展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培訓,加強對專職負責人的任職培訓,全面提高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綜合素質和專業技能。
(五)推進對社會組織常態化、社會化、數字化監管
一是民政、財政、公安等部門依法使用行政、法律和經濟手段,加強對社會組織常態化監管,建立社會組織年檢、評估聯動機制,將全省各級民政部門開展的登記、年度檢查、執法和考核情況等公開于社會組織信息平臺,提高社會組織信息公開程度,以利于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實現監管常態化[6]。二是完善社會監督法律法規,聘請社會監督員或引進第三方機構對社會組織進行監管,拓寬社會各界監督舉報渠道,支持新聞媒體、互聯網平臺對社會組織及其活動進行監督,對社會組織違法違規行為進行曝光并及時處理、回應公眾的舉報和投訴。三是推動數字化賦能監管,推進“互聯網+監管”深度融合,研發浙江省統一的社會組織線上監管平臺,實現監管信息一站式發布,提升社會組織監管的透明度。
(六)提高社會組織公信力,營造風清氣正的發展環境
公信力是社會組織信譽的重要指標。要提高社會組織公信力,首先,要構建社會組織信用管理法律體系,加強道德規范軟約束與法律體系硬約束的融合機制,將社會組織信用活動納入法治軌道。其次,要建立第三方公信力評估平臺,按照公信力指數,對社會組織進行年度評級,并定期公布失信社會組織和失信從業人員。再次,要加大社會組織信息公開力度,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拓寬信息發布渠道,及時發布真實、準確、完整的組織信息,尤其是敏感的財務信息,便于社會公眾對社會組織的全過程監督[7]。最后,要對違法違規社會組織重拳出擊,采取專項檢查、隨機抽查等方式查處違規違法、失德失信行為,及時取締非法社會組織;采用依法撤銷、指導注銷等方式,清理整治“僵尸”社會組織,使社會組織的公信力和發展環境實現系統性重塑。
——張脆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