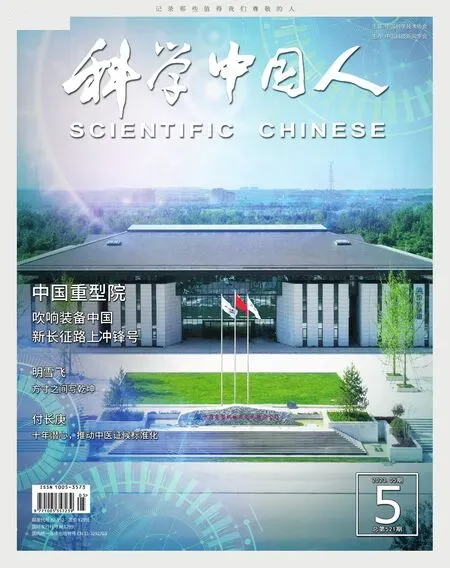面向未來 科學(xué)發(fā)展
——記北京師范大學(xué)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院長陳曉松
于德萍

陳曉松
2023年,是陳曉松教授擔(dān)任北京師范大學(xué)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院長的第四個年頭。
早在上任之初,陳曉松曾提出4個關(guān)鍵詞——氛圍、體系、土壤和機制,希望能圍繞于此,形成“以生命系統(tǒng)、神經(jīng)系統(tǒng)、教育系統(tǒng)、地球系統(tǒng)為主要方向,進一步夯實非平衡統(tǒng)計物理基礎(chǔ)”的相關(guān)舉措,扎扎實實地推進學(xué)科建設(shè)。“我們是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所以潛意識中希望包括學(xué)科建設(shè)在內(nèi)的所有工作也是系統(tǒng)的、科學(xué)的。”陳曉松說。
轉(zhuǎn)眼間3年多過去,陳曉松最欣慰的是,他的工作得到了同事們的支持和認可,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推進。而在2023年,他還將帶領(lǐng)同事們和同學(xué)們迎來北京師范大學(xué)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成立10周年的大日子。站在這個歷史性節(jié)點上,他由衷地希望能夠和學(xué)院一起,共同肩負承上啟下的重任,力爭把系統(tǒng)科學(xué)的學(xué)術(shù)進步轉(zhuǎn)化為推動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力量。
居安思危,集中力量辦大事
在北京師范大學(xué)(以下簡稱“北師大”)這樣一所建校120余載的學(xué)府中,成立于2013年的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著實年輕。然而,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科在北師大這方沃土上生根卻遠不止這10年。
早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理論物理學(xué)家方福康、數(shù)學(xué)家嚴士健、物理化學(xué)家劉若莊等前輩創(chuàng)建的量子力學(xué)研究小組為開端,“系統(tǒng)科學(xué)”已在北師大初見端倪。1979年,非平衡系統(tǒng)研究所創(chuàng)立;1985年,系統(tǒng)理論專業(yè)正式組建。“這是當(dāng)時中國僅有的兩個系統(tǒng)理論專業(yè)之一,北師大也從此開始有目的地投入力量開展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陳曉松介紹說。
誠如其言,在系統(tǒng)科學(xué)領(lǐng)域,北師大一邊探索一邊邁出了穩(wěn)健的步伐。到20世紀90年代末,他們已經(jīng)在全國率先形成從本科到博士后流動站的完整人才培養(yǎng)體系。2000年,北師大系統(tǒng)科學(xué)取得了一級學(xué)科博士學(xué)位授予權(quán);第二年,其系統(tǒng)理論專業(yè)被評為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科中全國唯一的國家重點學(xué)科。可以說,在一代代學(xué)科帶頭人的努力下,歷經(jīng)歲月的打磨,北師大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科已逐漸成長為一顆“明珠”,散發(fā)著獨特的光彩。2013年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成立之前,這一學(xué)科已經(jīng)在教育部組織的3次學(xué)科評估中展示出實力,“一次全國第一,兩次全國第二”。2017年,北師大入選國家“世界一流大學(xué)”建設(shè)A類名單,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科也入選了“世界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名單。
“然而,2016年的學(xué)科評估結(jié)果公示后,還是給了我們一個不小的警示,我們的學(xué)科排名是第四,等級為B-,這讓我們清醒地意識到:我們在進步,別人也在進步,而我們進步的速度沒有別人快。”2020年1月,陳曉松在學(xué)生黨建工作會議上如此說道。此時,他接任北師大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院長還不到3個月。
作為中國較早開展系統(tǒng)科學(xué)研究的單位,北師大的優(yōu)勢十分明顯。他們具有深厚的統(tǒng)計物理學(xué)基礎(chǔ),足以支撐復(fù)雜系統(tǒng)理論創(chuàng)新,并以探究復(fù)雜系統(tǒng)一般、普適性規(guī)律為目標,發(fā)展復(fù)雜系統(tǒng)基礎(chǔ)理論;此外,他們在認知與教育、地球系統(tǒng)、社會治理等方面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礎(chǔ),也建立了完整的系統(tǒng)科學(xué)人才培養(yǎng)體系。正因如此,陳曉松認為居安思危、敲響警鐘是必要的,但不能盲目追求所謂的“熱點”。在對國內(nèi)外復(fù)雜性研究機構(gòu)進行了充分調(diào)研后,陳曉松發(fā)現(xiàn)他們的確各具特色,但也存在不足,比如:系統(tǒng)工程研究多、系統(tǒng)科學(xué)研究少;缺乏完備、普適的理論體系,理論研究概念化、淺表化、碎片化等。
“以美國圣塔菲研究所為例,他們吸引了很多國際一流的學(xué)者,不斷地在引領(lǐng)研究潮流,但尚缺乏深入凝練的研究主題。”陳曉松覺得這其實是一種遺憾。如果北師大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想要可持續(xù)發(fā)展,他更傾向于在把握學(xué)院特色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凝練學(xué)科方向。具體來說,就是夯實復(fù)雜系統(tǒng)基本理論;研究地球系統(tǒng)復(fù)雜性,研究地球系統(tǒng)內(nèi)的自然生命與人類社會的運行規(guī)律;探索認知與教育系統(tǒng)復(fù)雜性,建設(shè)“認知與教育復(fù)雜性”研究集群。
在陳曉松看來,這是一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措。他希望能夠打破學(xué)科壁壘,創(chuàng)造適應(yīng)復(fù)雜系統(tǒng)多學(xué)科交叉研究的平臺和環(huán)境,創(chuàng)新資源配置、考核方式、資源保障方式,集中優(yōu)勢研究力量給予穩(wěn)定支持。
“2021年諾貝爾物理學(xué)獎授予了3位科學(xué)家,以表彰他們‘對我們理解復(fù)雜物理系統(tǒng)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陳曉松認為,這標志著人類對世界的探索,已從還原論為主導(dǎo),逐步過渡到與復(fù)雜性研究并重的新階段,“是一個好的時機”。“在這之后其實出現(xiàn)了一股關(guān)于復(fù)雜系統(tǒng)研究的熱潮,但如何交叉是個問題,所以我們一定要凝練方向。”
“現(xiàn)在有很多重大科學(xué)問題,單個人其實很難做出真正有影響和深入的貢獻。我們凝練方向,一方面是促成現(xiàn)有科研人員跨專業(yè)、跨學(xué)科、跨院系合作,實實在在地把問題做深、做透;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基于學(xué)校、學(xué)院的傳承和優(yōu)勢,將科學(xué)研究與國家的戰(zhàn)略需求和人類的科學(xué)發(fā)展相結(jié)合,去解決國民經(jīng)濟和國防建設(shè)中重大的系統(tǒng)性復(fù)雜問題。”陳曉松和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的風(fēng)格與宗旨就是“務(wù)實,不務(wù)虛”。

陳曉松團隊合影
“21世紀是復(fù)雜性科學(xué)的世紀”
正如北師大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擁有深厚的統(tǒng)計物理學(xué)基礎(chǔ),陳曉松這位新任掌門同樣也是從物理開始的。
“我在華中師范大學(xué)攻讀碩士學(xué)位時,師從劉連壽先生,是他引領(lǐng)我走進了理論物理學(xué)的大門。”陳曉松說。劉連壽先生主要從事理論物理和高能物理研究,陳曉松早年曾在相關(guān)領(lǐng)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早在1987年,由劉連壽先生推薦,陳曉松前往德國柏林自由大學(xué)攻讀博士學(xué)位,研究方向為“液體物理和統(tǒng)計物理”。旅德13年,從求學(xué)到工作,從柏林自由大學(xué)到亞琛工業(yè)大學(xué),他最大的收獲就是將“科學(xué)的發(fā)展要服務(wù)實際需求,理論研究要和物理實踐相結(jié)合”刻進了科研理念中。在這一時期,他始終都在關(guān)注國內(nèi)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發(fā)展,并在母校華中師范大學(xué)擔(dān)任教職。2000年,在中國科學(xué)院“百人計劃”的支持下,陳曉松正式回國,任中國科學(xué)院理論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理論物理所”)研究員。幾年后,一項新的工作令他開始涉足復(fù)雜系統(tǒng)。
這里又要提到美國圣塔菲研究所了。圣塔菲研究所在科研之外,還設(shè)立基金開展了一系列教育項目,面向全球普及復(fù)雜系統(tǒng)的核心思想。其中,持續(xù)時間最長的就是從1988年開始運轉(zhuǎn)的復(fù)雜系統(tǒng)暑期學(xué)校。2004年起,圣塔菲研究所與理論物理所聯(lián)合在北京開設(shè)暑期學(xué)校,每期錄取50~60名學(xué)員。陳曉松被任命為中方校長。“理論物理所和圣塔菲研究所先后合作辦了5屆暑期學(xué)校,我們邀請國際知名的學(xué)者來介紹他們的工作,激發(fā)學(xué)生們對復(fù)雜系統(tǒng)的興趣。”

北師大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組織活動合影
對陳曉松而言,復(fù)雜系統(tǒng)的確為他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有一位美國考古學(xué)家叫亨利·懷特,他把考古結(jié)果反饋到對當(dāng)年城市的結(jié)構(gòu)規(guī)模等相關(guān)問題的研究中;香港中文大學(xué)王士元教授也講道:語言學(xué)的演化并非一個獨立的體系,需要借助考古學(xué)、遺傳學(xué)等多個學(xué)科。而這些都涉及復(fù)雜系統(tǒng)。”陳曉松還提到圣塔菲研究所原所長杰弗里·韋斯特的例子,“他早年做過高能物理研究,后來開始探討生物學(xué)中普遍尺度定律的起源,從分子基因組的尺度擴大到線粒體和細胞,再到整個生物體和生態(tài)系統(tǒng)。在他看來,不論螞蟻還是大象,不論生態(tài)系統(tǒng)還是城市、社會網(wǎng)絡(luò)等,都可以通過規(guī)模法則這一‘尺度’變得可量化、可預(yù)測、清晰明了且極度統(tǒng)一。”
由此,陳曉松對復(fù)雜系統(tǒng)產(chǎn)生了極大興趣。復(fù)雜性科學(xué)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是一門新興的交叉性、綜合性學(xué)科,也是當(dāng)代科學(xué)發(fā)展的前沿領(lǐng)域之一。此前,人類對世界的探索還是以“還原論”為主,其核心思想和理念就是將研究對象還原成多個組成部分及個體。相比復(fù)雜系統(tǒng),還原論要古老得多,其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曾推動了牛頓力學(xué)的形成。到20世紀,以原子結(jié)構(gòu)的研究以及微觀粒子的探索為標志,還原論指導(dǎo)下的科學(xué)研究更是達到了一個頂峰,建立了量子力學(xué)、粒子物理的標準模型等物理學(xué)基本理論。
但與此同時,還原論的局限也越來越明顯。1972年,美國物理學(xué)家菲利普·安德森(1977年諾貝爾物理學(xué)獎獲得者)在《科學(xué)》雜志發(fā)表文章稱:將萬事萬物還原成簡單的基本規(guī)律,并不意味著從這些規(guī)律出發(fā)能夠重建宇宙,也不能依據(jù)少數(shù)個體的性質(zhì)簡單外推出多個體復(fù)雜系統(tǒng)的行為。菲利普·安德森認為:“復(fù)雜系統(tǒng)在不同層次會呈現(xiàn)全新的性質(zhì),研究和理解此類涌現(xiàn)行為,就其基礎(chǔ)性而言,與其他研究相比毫不遜色。”在中國,錢學(xué)森先生也曾在20世紀80年代指出:“系統(tǒng)學(xué)的建立,實際上是一次科學(xué)革命,它的重要性絕不亞于相對論或量子力學(xué)。”
“通俗地說,大家發(fā)現(xiàn),就算將組成部分研究得再透徹,也不一定能把整體弄明白。這不是簡單的‘1+1=2’。”陳曉松補充道。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復(fù)雜系統(tǒng)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已經(jīng)成為共識。學(xué)界認為:只有當(dāng)具有不同背景的科學(xué)家利用互補技術(shù)合作解決共同的問題時,才能解決科學(xué)中一些最重要的問題。此時,復(fù)雜系統(tǒng)科學(xué)的發(fā)展,不僅能夠帶來自然科學(xué)的變革,彌補人類對自己所處宏觀尺度科學(xué)規(guī)律認識的不足,而且可以滲透到社會復(fù)雜系統(tǒng)及社會科學(xué)的研究中。英國理論物理學(xué)家霍金更是斷言,“21世紀是復(fù)雜性科學(xué)的世紀”。
作為一個行動派,陳曉松決定要投身系統(tǒng)科學(xué)。“理論物理所學(xué)風(fēng)開放,使我能夠接觸到理論物理各領(lǐng)域及相關(guān)學(xué)科,與彭桓武、周光召、郝柏林等老一輩科學(xué)家們的接觸,也使我受益良多。”陳曉松表示,理論物理所的良好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使他向復(fù)雜系統(tǒng)研究的過渡非常順利。之后的十幾年中,他在復(fù)雜系統(tǒng)的統(tǒng)計物理、相變與臨界現(xiàn)象、氣候系統(tǒng)的統(tǒng)計物理等方向上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他本人也從2007年起擔(dān)任理論物理所副所長,正當(dāng)一條光明的事業(yè)之路在腳下鋪開時,他卻有了新的考量。
“在理論物理所18年,受身邊環(huán)境和前輩科學(xué)家的影響,我體會到了要存平常心、做平常人、干平常事。”權(quán)衡之下,陳曉松更傾向于脫離管理崗,專心鉆研復(fù)雜系統(tǒng)科學(xué)。而在這個領(lǐng)域,北師大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我想到大學(xué)去,安靜地做些事。”陳曉松說。
乘東風(fēng),布局系統(tǒng)科學(xué)
2023年1月5日,國際期刊《自然·氣候變化》刊登的一篇論文,提出了基于氣候網(wǎng)絡(luò)的全新研究范式,并指出,作為地球氣候系統(tǒng)的臨界要素之一,亞馬孫雨林與其他的臨界要素之間具有“遙相關(guān)”特性。同期的評論文章中稱:“這是復(fù)雜網(wǎng)絡(luò)理論首次應(yīng)用于研究地球系統(tǒng)臨界點問題,這兩個研究領(lǐng)域的交叉為剖析全球氣候動力學(xué)提供了重要的見解。這項工作為全球范圍分析臨界要素開辟了一個全新領(lǐng)域。”4天后,《科技日報》頭版也對相關(guān)工作進行了專門報道。而這篇論文的通訊作者就是陳曉松。
“它甚至能影響到青藏高原”,陳曉松說,“這意味著,我國青藏高原可能是一個處于激活狀態(tài)的全新氣候臨界要素。”
此前,《自然》曾發(fā)文指出,地球氣候系統(tǒng)中的九大臨界要素已經(jīng)接近或處于臨界點狀態(tài)。所謂氣候臨界點,指的是全球或區(qū)域氣候從一種穩(wěn)定狀態(tài)到另外一種穩(wěn)定狀態(tài)的關(guān)鍵門檻。一旦臨界點被突破,則會引起地球氣候系統(tǒng)狀態(tài)不可逆轉(zhuǎn)的改變。研究這些臨界點及臨界點之間可能的連鎖反應(yīng),是一個關(guān)鍵科學(xué)問題。為此,北師大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陳曉松教授、樊京芳教授團隊,國家安全與應(yīng)急管理學(xué)院楊賽霓教授聯(lián)合多國學(xué)者開展了相關(guān)研究。
“我們發(fā)現(xiàn)亞馬孫雨林和青藏高原之間的各種極端氣候在氣候變化下是同步的。”陳曉松指出,這一結(jié)論得到了大量氣候模式數(shù)據(jù)的驗證,他們還以此揭示出其遙相關(guān)的傳播路徑在氣候變化下也是穩(wěn)健的。“亞馬孫雨林號稱‘地球之肺’,青藏高原被譽為‘亞洲水塔’,它們之間存在穩(wěn)定的遙相關(guān),也為我國研究和實現(xiàn)‘雙碳’目標提供了新的視角。”陳曉松強調(diào)。
實際上,相變與臨界現(xiàn)象不只存在于物理系統(tǒng)和氣候系統(tǒng),它們還廣泛發(fā)生在從自然界到社會的各種復(fù)雜系統(tǒng)中。“平衡系統(tǒng)微觀態(tài)的分布是已知的,而復(fù)雜系統(tǒng)一般處于非平衡態(tài),其微觀態(tài)分布以及序參量一般來說都是未知的,這就給研究復(fù)雜系統(tǒng)的相變與臨界現(xiàn)象及其動態(tài)演化提出了挑戰(zhàn)。”2019年,陳曉松團隊在《中國科學(xué):物理學(xué) 力學(xué) 天文學(xué)》雜志上發(fā)表了《復(fù)雜系統(tǒng)的本征微觀態(tài)理論》。
本征微觀態(tài)方法開辟了研究復(fù)雜系統(tǒng)相變與臨界現(xiàn)象的新路徑,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統(tǒng)一地處理平衡態(tài)與非平衡態(tài)復(fù)雜系統(tǒng)的相變與臨界現(xiàn)象。在此基礎(chǔ)上,他們又在國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重點項目的支持下,開展了“本征微觀態(tài)的重整化群理論”研究,相關(guān)論文2022年發(fā)表在《中國物理快報》上。“臨界現(xiàn)象重整化群理論是美國物理學(xué)家肯尼斯·威爾遜于1971年提出的,他也因此獲得1982年諾貝爾物理學(xué)獎。這一理論被廣泛應(yīng)用到研究哈密爾頓量已知系統(tǒng)的臨界現(xiàn)象,但如今復(fù)雜系統(tǒng)的相變與臨界現(xiàn)象往往難以給出哈密爾頓量的具體形式。”陳曉松團隊的研究則突破了這一瓶頸,可以統(tǒng)一地處理廣泛的平衡和非平衡復(fù)雜系統(tǒng)臨界現(xiàn)象。
“從物理系統(tǒng)到生物、地球系統(tǒng),跨越很大。”但陳曉松對此很有信心。近年,他還在主持數(shù)理學(xué)部重點項目“復(fù)雜系統(tǒng)相變臨界現(xiàn)象”研究。陳曉松談到人類社會與地球系統(tǒng)其實是高度耦合、相互影響的,他希望能夠?qū)で蟮降厍蛳到y(tǒng)相變與全球社會系統(tǒng)相變之間存在的聯(lián)系。“對于我們提及的創(chuàng)新方法,同行還是認可的。”他說。
作為北師大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院長,陳曉松在談“跨越”時再次強調(diào)了跨學(xué)科和跨學(xué)院協(xié)作。為此,他鼓勵學(xué)院研究者們與來自數(shù)學(xué)科學(xué)學(xué)院、統(tǒng)計學(xué)院、人工智能學(xué)院、腦認知與學(xué)習(xí)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學(xué)者展開深度合作,并契合相關(guān)發(fā)展方向引進人才。“現(xiàn)在學(xué)院團隊已經(jīng)有30多位學(xué)者,大家對于學(xué)院凝練學(xué)科方向、摒除同質(zhì)化競爭的發(fā)展也有了共識。”
陳曉松尤其看重年輕科技人才的成長與發(fā)展。“比如樊京芳教授,他曾在理論物理所讀博,現(xiàn)在已經(jīng)在復(fù)雜系統(tǒng)相變與臨界現(xiàn)象、極端氣候的預(yù)測及影響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國際影響力的成果。”陳曉松舉例道。這幾年,他還從北師大全球變化與地球系統(tǒng)科學(xué)研究院、北京郵電大學(xué)、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找到了數(shù)位潛力股。“這些年輕人都很有想法,學(xué)院也會為他們營造創(chuàng)新環(huán)境,希望他們能盡快成長起來,使我們在系統(tǒng)科學(xué)發(fā)展方向上的布局真正鋪開。”
言談中,陳曉松流露出自信的神色。他相信,北師大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雖然面臨著挑戰(zhàn),但也身處大機遇之中。2020年,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堅持系統(tǒng)觀念”列為“十四五”時期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到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不僅提出了“系統(tǒng)集成”“系統(tǒng)完善”“系統(tǒng)治理”“系統(tǒng)保護”“系統(tǒng)性變革”等概念,而且將“堅持系統(tǒng)觀念”作為習(xí)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核心要義之一,強調(diào)要不斷增強“系統(tǒng)思維”。
對系統(tǒng)科學(xué)來說,這無疑是一股東風(fēng)。陳曉松和他的同行者們,正期待著能在北師大這方沃土上,堅持系統(tǒng)觀念,乘“東風(fēng)”之力,掛云帆濟滄海,為系統(tǒng)科學(xué)學(xué)院創(chuàng)造下一個明媚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