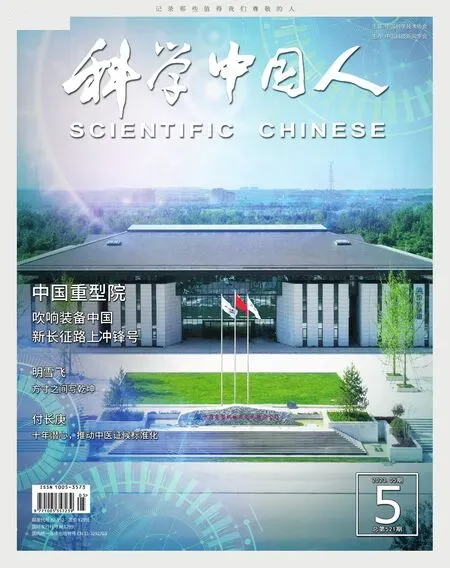矢志探索水資源 腳步丈量科研路
——記同濟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水利工程系研究員王喜華
張 聞 李文博
《浪淘沙·問路》
六瓣舞翩躚,素裹人間。山中寺院又炊煙。昔日仍能尋細徑,長嘆云天。
探索數千年,一日知源,舊時遺夢未及諳。但問心兄無怨悔,不羨飛仙。
——王喜華作于吉林長春,2009
水是萬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對于有著古老農耕傳統的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部水資源研究史。而王喜華致力奮斗的事業始終與水有著不解之緣,從2005年考入吉林大學水文及水資源工程專業那一天起,他的事業就與水資源緊緊聯系在一起。直到今天,他仍然奮斗在水資源探索的最前沿。
20世紀90年代以來,洪水、干旱、水質污染、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愈加嚴重,直至今日相關問題仍是困擾國計民生的關鍵因素。為了將研究更好地面向社會所需,近些年來王喜華針對當前我國的水資源短缺及水污染問題,選取了水文水資源領域最為前沿的課題之一——地下水-地表水交互作用帶——為研究對象,開展了大量科研探索,特別是在地下水-地表水的交互作用系統中的水量轉化,以及三氮、重金屬等污染在系統中的遷移轉化規律和溯源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性科研成果。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十幾年來,我一直和水打交道,足跡幾乎遍布了中國的各大江河湖泊,并實地調查了諸多邊遠地區的水資源短缺及污染問題。特別是當我能夠將所學的科學知識運用到水資源研究中,扎扎實實為祖國的水污染研究,為人民的生活作出一點點貢獻時,是我最開心、最欣慰的時候。”王喜華說。伏流無聲,水潤萬物。王喜華蹚過青春之河,在水科學研究中留下了自己堅實的科研足跡。
與水結緣,無心插柳柳成蔭
《七絕·游黃果樹大瀑布》
數里聞聲沫雨飄,一墻白練掛天條。
疑棲仙子滌裳處,待日飛升奉九霄。
——王喜華作于貴陽,2018
“當初進入與水資源相關的專業領域,可以說是無心之舉。”如今談起與水資源領域研究的結緣,王喜華始終認為其中存在著一種冥冥中注定的機緣。
事實上,在2005年參加高考時,王喜華對專業的選擇并沒有太明確的方向,而水文及水資源工程專業也僅僅是他所報考的眾多志愿中的一個,也許是命運的驅使,他被吉林大學水文及水資源工程專業成功錄取,自此開始了自己在水資源領域的科研逐夢路。
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大學本科4年間,王喜華沒有一刻懈怠,憑借著優異的學習成績,他順利獲得了保研機會,師從吉林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副院長盧文喜教授進行研究學習。當時盧文喜教授關于節水灌溉的研究項目正在著手立項工作,在他的支持與引領下,王喜華親身參與到了科研項目的立項、實驗方案設計、野外施工及儀器檢測、野外數據的采集與分析、項目結題等環諸多環節中,深刻體會到了一個完整的科研項目所經歷的漫長過程與期間的種種不易。為了得到更加精準的實驗數據,王喜華在生產基地住了一年。野外荒涼的環境、冬季難忍的嚴寒,讓王喜華飽受艱辛,但“怕走崎嶇路,莫想登高峰”的科研精神給了他攻克艱難的勇氣與決心,并讓他深刻認識到扎根現實、科研實踐對于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這個研究項目一下子把我從理論課本上虛無縹緲的狀態拉到了面向實際問題中來,對我的科研人生產生了重要影響。”王喜華說。能夠在研究生階段有這樣的科研歷練機會,給王喜華的科研人生留下了十分難忘的回憶,也為他今后的科研之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王喜華帶領團隊在江西省鄱陽湖流域進行調研(從左到右依次是:博士生賈順卿、王喜華、碩士生毛博洋、博士生劉澤軍)
維系生態,建立區域地下水適宜水位模型
《七絕·訪棲霞古寺》
棲霞禪寺棲霞山,千載興衰千佛巖。
遠送鐘聲紅葉谷,金陵難渡水凝寒。
——王喜華作于南京,2018
力學篤行,學有所用。王喜華始終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就是服務社會、服務人民,用科技增進民生福祉。如何在這條道路上找到自己的目標與方向,真正做到“水潤民生”,一直是驅使王喜華躬行不輟的目標與動力。在中國科學院大學環境科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時,王喜華就關注到了地下水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密切關系,并開展了一系列探索。
科學家們發現地表水與地下水之間實際上是相互轉化、相互制約、相互聯系的統一整體,而分開研究會產生一系列問題。地下水使用過量后會造成地下水水位降低、直接或間接地導致地表植被枯萎甚至地面塌陷。特別是地下水在水、陸及海岸交界處等生態環境和相關景觀的維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維持某些關鍵生態系統生態完整性的關鍵因子。“如果在水資源比較缺乏的干旱地區,人口的大量增加,勢必導致地下水被大量開采,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原有的植物就會退化甚至消亡,人類生產生活也會受到極大影響。”王喜華說。在這一背景下,王喜華和研究團隊成員們,通過科研探索,突破生態因素的應用瓶頸,將不同植被的生態信息作為主要量化指標,建立了基于地表生態植被因素的區域尺度地下水適宜水位模型(EISGD)。這一模型利用極限思維進行調控,合理地利用水資源,以減少對生態的損害,進而保障區域生態的平衡。在博士生導師章光新研究員的推薦下,王喜華博士階段部分相關研究成果成功被國務院辦公廳內部刊物《專報信息》采納,為我國重要農業區地下水資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
異國求學,開辟水污染研究新篇章
《長相思·風飛花》
風飛花,雨飛花。松柏相依鳴綠蛙,飛奔池里鴨。
思無涯,緒無涯。夜雨無聲夢至家,朝來萬里霞。
——王喜華作于加拿大,2020
博士畢業后,王喜華漸感理論知識的不足,并有了前往國外深造的想法。工作3年后,他順利獲得國家留學基金委的全額獎學金資助(CSC),前往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學院開啟了自己的博士后研究生涯。在這里,王喜華極大地開闊了科研視野,除了積極與博士后導師沃爾特·A.伊爾曼(Walter A.Illman)教授合作,開展非均質參數的反演及對溶質運移影響研究外,他還選擇旁聽學院其他著名教授的課程,學習和掌握新的知識體系以及先進的教課方式,這些經歷讓王喜華倍感興奮,收獲頗豐。其中,在全程旁聽南迪塔·巴蘇(Nandita Basu)教授的“生態水文學建模”課程時,他的靈感得到了極大的觸發,并將其研究方向與博后導師方向相結合,融匯成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即硝態氮的遷移轉化及對非均質性的響應等研究,開啟了自己的水污染研究之路。尤其是在博士后的第二年,全球新冠疫情暴發,王喜華一人孤懸海外,閉關在住所近一年,克服了重重心理、身體以及科研的巨大壓力,終于學成歸國。
學以致用,探究伊洛河流域水污染
《五絕·過龍門香山寺訪樂天冢》
千年文脈傳,東瀛奉神仙。
歌賦有九老,詩魔一樂天。
——王喜華作于河南洛陽,2021
做研究不能閉門造車,必須實地調研考察,獲取第一手資料。在多年的科研旅程中,王喜華頻繁往返于全國各地之間,研究區域水資源的合理利用與污染問題。也正是一次次的實地調查與探索,讓他真正看到了全國各地水資源發展所存在的真實問題。
長期以來,河南都是人口大省、農業大省,也是我國重要的經濟大省,而這里也是王喜華開展水資源調查的重要地點之一。在此之前,王喜華曾和團隊成員在河南洛陽進行了3年的野外考察工作。通過調研,他們發現在中國城市化進程逐漸加速的背景下,地表水-地下水的交互作用也會產生相應的改變,而其產生的一系列污染問題都是未知的。在之前的研究基礎上,王喜華就將地下水-地表水交互作用帶作為自己多年來扎根探索的重點,特別是在采用水化學、同位素、熱追蹤結合數值模擬方法研究不同尺度上的地下水-地表水的交互作用系統中的水量轉化,以及三氮、重金屬等污染在系統中的遷移轉化規律、溯源研究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世界范圍內的大量科學研究已證明氮污染對人類飲用水和農業存在潛在威脅。但目前,人們對流域尺度地表水、沉積物和地下水系統中的氮時空變化特征及氮污染來源與比例的認識尚不充分。而識別流域尺度的氮素在地表水、沉積物和地下水之間的時空遷移過程,可為區域水污染控制和管理提供重要信息,尤其是人類污染活動密集的城市及周邊重要農業地區。在這一背景下,王喜華團隊將伊洛河流域作為研究根據地,對其存在的污染物展開了一系列科研調查。
為了得到更為準確的實驗數據,王喜華團隊克服一切困難,開始了漫長的現場扎根生活。最終他們成功采用雙同位素、水力學、水文地球化學等多種方法,于2018—2020年在伊洛河流域旱、雨季節4個時段采集400余個樣品,獲得伊洛河流域地下水、沉積物和地表水中NO3--N、N H4+-N、N O2--N和總氮的時空變化特征、來源及比例。在研究數據的基礎上,他們撰寫了相關理論文章,并有多篇文章成功發表在環境領域學術期刊《總體環境科學期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經過研究證實,相關結果可用于區域制定有效的水資源管理策略、控制重要農業區的氮污染,對于重要農業區的糧食生產以及區域水資源的生態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砥礪前行,不負水科學研究使命
《五絕·晚夜黃花》
無人孤賞芳,自綻晚風涼。
妖卓舞清影,醉吾是遠香。
——王喜華作于加拿大,2020
正所謂“實踐出真知”,在理論與應用領域探索開拓的道路上,王喜華也逐漸發現近些年來環境生態與水文水利行業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相較于室內實驗而言,野外調查采樣與試驗更需要數據、時間,需要科研工作者更多的耐心、專注度和不畏艱難的科研探索精神。然而,近年來我卻發現相關領域越來越重視室內模擬、實驗,野外探索越來越少。”談及此,王喜華充滿了遺憾與惋惜。
一直以來,王喜華始終認為,在不充分做野外調研的前提下,進行室內實驗模擬,本身就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行為。而在十幾年的科研征途中,他始終堅定將野外調研作為自己科研實驗的根基,毫不動搖。這種深入現場了解民生之所需的習慣,王喜華一直沿襲至今。
自2021年10月來到同濟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水利工程系工作以來,王喜華科研探索的腳步從未停歇。2022年9月,由于遭遇全球嚴重干旱,我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的水域面積創下了歷史新低,部分河段甚至干涸,露出了河床。得知這一消息之后,王喜華馬上帶領學生出發,在鄱陽湖區域整整調研了8天,采集了300多份樣品。現如今,他也正在引領團隊成員們根據采集的樣品,對鄱陽湖干旱原因及干旱對水質的影響進行實驗探索,相關工作均在有序開展中。
科研之外,王喜華也十分重視學生的培養工作。在王喜華的科研歷程中,導師便是指引他科研之路的燈塔。王喜華的碩士生導師盧文喜教授、博士生導師章光新研究員,給了他極大的科研自主性,為他自主科研能力的提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此之后,王喜華又有幸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胥毅軍教授的指導下極大地加強了英文論文的撰寫能力,僅在博士階段他就成功發表了5篇高水平《科學引文索引》(SCI)文章(2013—2015年),及至后來,在加拿大從事博士后階段,他在沃爾特·A.伊爾曼教授和南迪塔·巴蘇教授課題組開拓了科研視野和新的研究領域,為后來的科學研究指明了方向。而這一切與各階段老師們的耐心指導息息相關。2022年,王喜華在同濟大學順利組建了屬于自己的課題組,正式成為一名團隊的管理者。在之前導師的啟發與自己的研究經驗基礎上,王喜華十分注重對學生野外調研能力及思辨能力的培養。在他看來,水科學研究最終都要回歸實際,而科研人員首要具備的就是吃苦的能力。除此之外,他也十分鼓勵學生能夠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開展科研工作,做一名敢于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科研工作者,在科研中找到自己努力的目標與方向。

王喜華在加拿大與著名語言學家、收藏家戈登·斯萊塔格(Gordon Slethaug)教授及其夫人瑪麗女士一起鑒賞古董
詩詞博古,做多維生活的愛好者
《七律·謁宋陵》
嵩山洛水筑寢宮,樓闕巍峨郁青蔥。
杯酒釋兵匹夫勇,詩書繪畫文人庸。
一朝二度攻城破,九帝十陵盜墓空。
千載興衰倏而過,老農倚臥像生中。
——王喜華作于河南鞏義,2018
我們很難想象把詩人、散文家、古董收藏及鑒賞家、青年科學家這一個個獨立的稱號集中到一個人的身上將會如何,而王喜華就是這樣的存在。“他活得太灑脫了”“太具浪漫主義情懷”“當代徐霞客”,和王喜華有過深入接觸過的人常會對他有這樣的評價。
王喜華的愛好極其廣泛。他熱愛旅行,足跡遍布我國的主要大城市。歸國后,他熱戀故土之情不減,并利用7個月時間開啟了全國游走模式。游名山、訪古寺、謁皇陵、探窯址、窺石窟、宿古城、觀博物、嘗美食、考風土、識人情。一路走來,行萬里路,遇無數人。探歷史遺脈,發幽古之思。
王喜華喜歡文學和歷史,并對詩、詞、散文、書法、繪畫均有涉獵,并各有所長。正如朋友評價他:“真正把業余玩成了專業。”他所撰寫的詩、詞、散文成功被收錄在《中國當代作家詩人精品集》(團結出版社2022年版)中;多年來,他遍訪中國古代歷朝帝王陵墓,實地尋訪與考察,并在這一過程中,糾察遺漏信息,觸摸歷史真相。
王喜華熱衷古董收藏與鑒定,曾踏訪中國古代南、北方20余座千年古窯址及專項古陶瓷博物館,覆蓋中國古代“八大窯系”“五大名窯”等主要窯口;他收藏頗豐,喜歡用科學的思維,借助古物去考究歷史演進中遺落的信息;他眼光獨到,鑒定經驗豐富,擅長鑒定中國古代高古瓷及明清貿易瓷。多年來,他為國內外古董收藏愛好者提供了近萬人次的無償而專業的古董鑒定,贏得一致贊譽和尊重。王喜華熱愛生活,樂觀、灑脫的性格時刻影響著無數與他接觸過的人。
治水興水澤沃土,水潤民生繪新篇。過去20年,中國在水資源研究與污染治理技術方面已經取得巨大進步。作為一名青年研究者,王喜華仍舊使命在肩。未來他希望能從自己的專業領域出發,跟團隊成員們一起做更多有意義的事,在中國的更多地區留下自己水資源探索的腳步,用科研更好地惠及祖國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