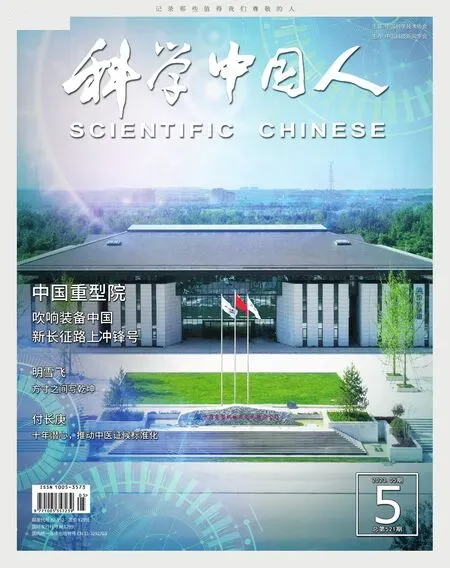奮楫前沿,做科研的追光者
——記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研究員王文鵬
衛婷婷

王文鵬
在《山海經·大荒南經》中,曾有這樣的描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羲和,作為中國古代神話中10個太陽的母親,掌管著安排10個太陽的輪流上崗的權力。而我國知名大科學裝置“羲和激光裝置”的命名靈感,也正來源于此。
第一次接觸到“羲和激光裝置”時,王文鵬剛剛博士畢業不久。在研究所領導的支持下,他深入到“羲和激光裝置”的建設過程中,打開了科學研究新的大門。作為我國自主研發的超強超短激光裝置,“羲和激光裝置”在世界上首次實現了10拍瓦的激光放大輸出,被2018年1月的《科學》雜志列舉為國際上自1960年第一臺激光器發明以來,在激光脈沖功率提升方面取得的第五大里程碑。“在這一過程中,我意識到了怎樣作為其中的一分子,整體推動大科學裝置的良好運行,這對于我的科研技術、科研水平,是不同以往的提升與促進。”王文鵬說。
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科學裝置就是科學家的“武器”,是我國搶占未來科技競爭制高點的重要砝碼。從一位初出茅廬的大學生,到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研究員,王文鵬多年來扎根在超強激光驅動等離子體粒子加速這一國際學術熱點領域開展了大量工作。以夢為馬,初心如磐。他始終想通過自己的力量,為中國的前沿科研事業發展做些事。而現如今他所取得的每一項成果,都是自己十多年“追光”之旅的堅實印記。
以夢為馬,播下科研的種子
南鄰黃海,北瀕渤海,與遼東半島對峙,這里是山東煙臺,也是王文鵬的故鄉。海的博大,賦予了煙臺獨特的人文氣質,歷史上這里曾誕生了多位名人學者。而王文鵬的科研理想,也是在這片熱土上萌芽的。
從小,王文鵬就是一名有著強烈好奇心的孩子。自初中二年級時開始接觸物理學科,他就對這一領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中學時期,在老師的推薦下,王文鵬參加了學校舉辦的物理競賽,并順利獲得了相關獎項。而正是這次獲獎經歷讓王文鵬受到了極大的鼓勵,物理的種子開始在他的心里生根。在正向驅動之下,王文鵬對于物理的興趣愈漸濃厚。在他看來,數學更多的是公式或者原理性的知識,而物理能夠幫助人們解釋世界上的各種事物,更具形象化,他迫切希望深入這一領域中,學習更多能夠學以致用的科研知識。
在此之后,王文鵬隨著對物理專業學習的日漸深入,對科研的興趣愈加濃厚,最終選擇在研究生階段進入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強場激光物理國家重點實驗室進行光學方向學習。
來到這一平臺之后,王文鵬師從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研究員徐至展院士開展研究工作。當時,綜合國內外在物理領域的發展情形,徐院士敏銳地洞察到激光驅動等離子體相互作用是目前國際上的研究熱點,未來發展潛能無限。而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在這一領域具有極大的研究優勢,相關方向處于世界發展前沿。在他的引領下,王文鵬順利接觸到了超強超短激光的產生及其驅動粒子加速這一研究方向。事實證明,徐院士的預測沒錯,此后多年間這一領域在國際上的發展極為迅速。至今,王文鵬想起來仍十分感謝徐院士對自己的科研引領。“如果當時的研究方向稍微偏離一點,可能發展的途徑就南轅北轍了。”王文鵬感嘆道。
面向前沿,從科研跟隨到原始創新
追光之路對王文鵬來說是一段奇妙的旅程,從踏上這個旅程開始,他就通過自己的力量,克服了許多艱難與險阻。從一名初出茅廬的學生,到如今可以獨當一面的科研人,王文鵬的成長,離不開學校領導的鼓勵支持和在一次又一次的科研錘煉中所積累的經驗。
一路走來,王文鵬始終清楚自己的劣勢所在。“英語水平有待提高”“科研眼界還需繼續拓寬”……面對自己亟須成長的地方,他從未躊躇不前,而是積極“走出去”鍛煉自己的能力,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也給了他很大的發展機會,在校領導的推薦下,王文鵬積極參加上海市的科普講解大賽,并獲得了“最佳科普講解員”。“在科普講解的過程中,我打開了自己狹隘的認知邊界,在與國內外知名的專家學者溝通的過程中,我的科研視野也得到了極大的拓寬。”王文鵬說。走出自己的舒適區,讓王文鵬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這也讓他今后有勇氣面對更多科研路上的挑戰與課題。
“追光”之路總是崎嶇的,但越是艱難越要向前。
留所工作幾年后,王文鵬憑借優秀的專業能力,得到了參與“羲和激光裝置”管理及運行的機會。作為物理組的組長,他參與到大裝置的運行管理工作之中,以協助國產激光裝置在后期的運行過程中做出更多出色的成果。功夫不負有心人,“羲和激光裝置”建設項目于2016年立項,僅僅經過兩年的時間,就在世界上首次實現了10拍瓦的激光放大輸出,脈沖壓縮后寬度達到飛秒量級,相當于將10個太陽輻射到地球的總功率匯聚到一根頭發絲這樣的尺度。而這一震驚世界的成果,離不開羲和激光團隊所付出的點滴心血,王文鵬有幸成為其中一分子。“因為‘羲和激光裝置’整體的建設是環環相扣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學到了如何與團隊的工作人員更好地協作,相較于博士階段更好地提升了我的科研協作能力。”王文鵬說。
要增強我國的科研競爭力,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就需要科學家心無旁騖地在基礎科學的“無人區”進行自由探索。雖然在涉足相關領域時,鮮少有前人的經驗作為參考,失敗也在所難免,但是王文鵬始終堅守著這一信念。在多年的研究經驗基礎上,他一直在嘗試0到1之間的原始創新,并在這一基礎上開拓了拉蓋爾-高斯激光、超強渦旋激光這一研究方向。
20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分別頒給了美國科學家阿瑟·阿什金、法國科學家熱拉爾·穆魯以及加拿大科學家唐娜·斯特里克蘭,以表彰他們在激光物理領域的突破性發明。1970年,阿瑟·阿什金第一次發明光鑷技術并將其應用于生物學領域,實驗發現:利用連續激光的光壓可以實現微米量級粒子的加速和捕獲。1985年,熱拉爾·穆魯和唐娜·斯特里克蘭兩人則發明了啁啾脈沖放大(C P A)激光技術,開啟了相對論飛秒激光驅動等離子體相互作用的大門。在這兩項研究的成果的基礎上,王文鵬發現他們之間并沒有那么緊密的聯系。

王文鵬(左一)受邀參加中國科學院科學傳播局活動
“如果將兩項科研成果相結合會不會有新的發現呢?”
在這一背景下,王文鵬與團隊獨辟蹊徑將拉蓋爾-高斯(LG)激光模式應用到相對論等離子相互作用過程中,開啟了相對論L G激光驅動等離子體相互作用的大門。最終,他們成功實現了將20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中的光鑷拓展到相對論領域,開辟出一種新型相對論光鑷(L G激光)操控粒子手段。在國際上首次在百T W激光系統上實現了重頻相對論L G激光的產生與應用。在相關成果的基礎上,他們在《物理評論快報》(Phys. Rev. Lett.)相繼發表了兩篇相關文章。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相對論“渦旋刀”驅動操控的粒子束具有高電荷量、高準直性的特點且操控簡單,更容易獲得高品質束流,對粒子加速、超快電子衍射、超快電子成像、加速器中粒子注入、慣性約束聚變快點火等應用具有重要意義。
任何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這項研究成果的誕生背后,王文鵬團隊也經過多次投稿、修改,飽嘗失敗、迷茫、困惑之后,科研成果才最終問世。“在此之前,我們一直在跟隨著別人的計劃慢慢推進,現在我們的研究成果可以讓其他大學的科學家跟我們主動尋求合作。從跟著別人跑,到帶著別人和我們一起跑、一起合作,我覺得這就是0到1原始創新的意義所在。”王文鵬說。而這些成果的取得也給了他堅持創新的無限勇氣,鼓勵他永遠保持對科研的求知欲。
科研反哺,團隊成員破浪前行
薪火相傳,生生不息。一路走來,王文鵬受徐至展院士等科研前輩的影響至深。“徐院士真的把我們當孩子一樣,對我們的要求十分嚴格。在博士畢業論文的撰寫過程中,徐院士給了我很多專業而又細致的指導,甚至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放過。長期以來,他身上的認真與嚴謹也在無形中感染著我。”王文鵬說。如今在指導團隊學生進行理論文章撰寫時,王文鵬也會盡自己所能給予他們十分嚴謹而又專業的建議與指導,以保證他們的科研工作能夠更加順利進行。
“向著自己的目標,鉚足勁向前走”,一直以來,王文鵬從未放松對自己的要求,碩博期間他就是有名的“拼命三郎”,很長一段時間都堅持著每天凌晨1點睡覺,早上6點起床的作息,直到身體出現了一些問題他才決心改善這一狀態。
在王文鵬看來,每個人的專業能力沒有高低之分,重要的是態度端正以及勤奮踏實。在學生培養的過程中,他時常忠告學生科研積累的重要性,并希望他們能夠抓住人生中的黃金時期,盡全力做出更多創新性科研成果。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壘土。十多年的科研旅程,王文鵬不斷積累、沉淀,先后承擔了12項科研項目,而在與團隊成員并肩作戰的過程中,王文鵬對于世界的看法及對于科研反哺的思考也站在了更大的維度。在他看來,現如今的自己只是基于現有的認知,實現了小小的科研突破。而這一科研突破,放眼于整個科研領域,又是那么渺小。他始終認為,科研不是單打獨斗,只有將個人的價值融入團隊之中,才能更好地推動一些工程項目的實現。而“為做出世界頂級科研成果而戰斗”便是王文鵬團隊的研究使命。多年來在科研路上摸爬滾打,現如今王文鵬所在的科研團隊已經發展到了十幾人的規模。“勝則舉杯相慶,敗則生死相扶”,經過多年的團隊建設,一路走來王文鵬所在的科研團隊始終“擰成一股繩”,朝著世界頂級的科研成果進發。而與他們并肩作戰,王文鵬的內心也充滿著自豪感。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歷史的長河奔騰而過。近些年來,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社會需求的發展,王文鵬也在不斷微調著自己的研究方向。未來,面對我國的光刻機及芯片等領域的研究困境,他還將和團隊從基礎物理的角度出發,進行研究開拓,真正地將科研服務于國家所需。“雖然時代在變化,但人活在世界上,總是要追求一點卓越的東西。”王文鵬說。在科學之光的指引下,他還將奮楫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