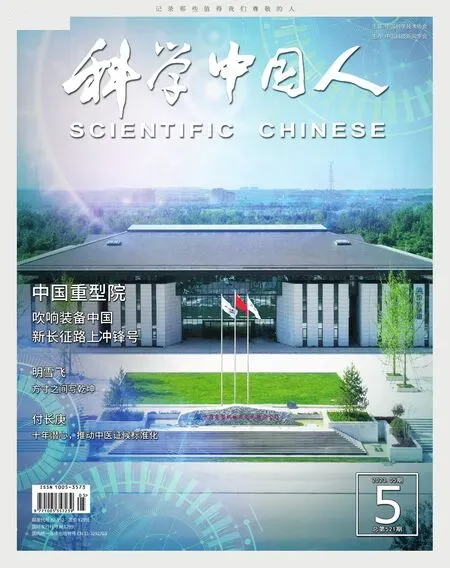格物窮理,明德篤行
——記杭州師范大學物理學院教授楊澤超
孫雅琴

楊澤超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4句從我國典籍中精簡出的人生哲理共同構成了杭州師范大學(以下簡稱“杭師大”)物理學院的辦學宗旨:格物窮理,明德篤行。“這也是引領我在科研道路上前行的基本方針”,剛加入學院不到1年的青年學者楊澤超說。而他與杭師大的結緣更像是某種意義上的“志同道合”:作為多年來堅守在生長合成二維石墨炔、二氧化硅等新材料及開發新型快速掃描隧道顯微鏡儀器領域中的年輕科學家,他同正處上升期的學院平臺一樣,朝氣蓬勃、自由生長。
走入二維微觀世界
就在十幾年前,二維材料對于人類來說還只停留在科幻層面。那種電子僅可在兩個維度的亞納米尺度上運動的材料對當時的學界來說,其牢靠穩定的程度并不夠可信。因為傳統科學認為,在單層原子的二維結構中熱激發會驅使原子上下移動,從而重新構建成能量更穩定的三維結構。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二維材料一直沒有得到學界的認可,直到石墨烯的出現才打破了這一認知。那是2004年,也恰逢楊澤超高考擇校之際。
與二維材料和新型器件相關的專業宣傳信息似乎在當時一躍成為理工科學子眼中的“焦點”。“光信息技術未來很有可能超越電子信息技術,成為新時代的一支潛力股。”身處其列的楊澤超從尚不發達的信息渠道中堅定了自己的想法,進而報考了在光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名列前茅的哈爾濱工業大學。但很快,他卻發現,原來這屬于物理學的大范疇,并不是想象中一片完全未知且神秘的藍海。“不過這也很好,物理學是對許多實用技術起支撐作用的深層科學,只要踔厲奮發,必將在廣闊天地內大有可為。”正如他所言,在之后的求學歲月中,他將自己的心態一直調整、維持得很好,慢慢地甚至將其潛移默化成為自己的興趣所在,享受著汲取知識的每分每秒。
但真正使楊澤超看到物理學魅力的還要屬發生在大學三年級時的一次學術分享會。那時,他親眼見到了諾獎得主的風采——納米技術之父亨利希·羅勒(Heinrich Rohrer)帶著助力他榮登1986年諾貝爾獎寶座的掃描隧道顯微鏡核心科技走入了楊澤超的生命。那也是楊澤超第一次知道,在掃描隧道顯微鏡的視角之下,可以直接進入納米世界,旁觀原子的結構與變化,甚至可以自由操縱它們。這對于楊澤超來說有著莫大的吸引力,于是他決定,投身相關研究。
這條從理論認知走向實踐操作的道路花費了楊澤超不短的時間,直到前往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物理學院,師從何塞·伊格納西奧·帕斯夸爾教授(Jose Ignacio P a s c u a l)和卡塔琳娜·弗蘭克教授(Katharina Franke)攻讀博士的時候,他才親眼見到了掃描隧道顯微鏡的本體。“我當時做實驗采用的是低溫掃描隧道顯微鏡,它的整個掃描成像部分都被安置在液氦溫度的環境中(約-272℃),通過它,我以原子分辨率測量了一種功能分子的結構和電子性質,從而為其在有機太陽能電池中的應用提供了重要的參數信息。”
由靜至動開辟新知
親自動手參與實驗之后,楊澤超才覺得自己對儀器、對科研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了解,這也為他在之后進入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弗里茨·哈伯研究所(Fritz Haber Institute of the Max Planck Society)開展博士后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過那時他不會想到的是,這一次的挑戰不是規范使用儀器,而是從零開始搭建。
在導師漢斯·約阿希姆·弗羅因德(Hans-Joachim Freund)教授的引導下,楊澤超很快意識到低的時間分辨率會嚴重制約掃描隧道顯微鏡對表面結構動力學過程的觀測。對比而言,在表面化學反應、材料生長和結構相變等過程中,原子或分子的運動變化通常發生在毫秒或微秒量級,但商品化掃描隧道顯微鏡的成像時間通常在分鐘量級。因此,提高掃描隧道顯微鏡的掃描速度自然成為以原子分辨率實時實空間研究表面結構動力學過程的理想解決方案。基于這種思路,加上導師的鼓勵與支持,楊澤超很快沉下心來,作為開發團隊的核心科研人員開啟了自己的探索。他的目標是在保有原子分辨率的前提下,力爭將掃描成像速率提升至100幀/秒以上,這意味著要將商品化掃描隧道顯微鏡的成像速率提高2萬倍以上,難度可想而知。所幸,成果是喜人的——一套歷時5年打造而成的變溫快速掃描隧道顯微鏡系統最終實現了楊澤超此前的所有想象。
在這套自研的儀器中,楊澤超團隊采用了緊湊的粗進針設計和復合型掃描探頭結構,針對性解決了傳統掃描隧道顯微鏡在快速掃描時圖像畸變和快速慢速掃描不易切換等硬件方面的問題;在控制系統方面,他們開發了新型螺旋掃描模式,并應用快速總線技術處理大流量數據,實現視頻級S T M圖像的實時顯示;在溫度調控方面,他們則引入對掃描探頭的反向冷卻機制,并優化顯微鏡各部件的機械耦合方式,從而實現對高溫樣品的原位成像。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此類兼具高時-空分辨和高溫功能的掃描隧道顯微鏡儀器在國內外尚無成熟的商品化產品。“這套設備將成為研究納米材料‘時間-結構-性質’構效關系的理想科研儀器,將為表面物理和化學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實驗手段,在原位實時實空間研究表界面原子擴散、薄膜材料生長和化學反應等領域均具有重要意義。”楊澤超自豪地介紹道。
2022年,楊澤超結束了自己的海外求索生涯,正式歸國加入杭師大物理學院。“沒想過要在國外待太久,畢竟將所學落在祖國大地上才算學有所得。”他如此描述自己的歸國初心。
杭師大物理學院“年齡”尚小,但目前已處于學校重點建設學科之列。學校和學院對于科研人才的重視和對科技創新不遺余力的支持,也讓楊澤超對杭師大平臺十分感激,深覺只有孜孜不倦才能不辜負多方期望。幸而上天眷顧勤奮的人,目前一套高溫快速掃描隧道顯微鏡原型機已經設置在杭師大物理學院的實驗室內。
既然前沿設備已經就位,那么有關納米結構演化動力學的研究也該順理成章地提上日程,這對于開發新材料和新型催化劑具有重要意義,楊澤超深諳此理,因此從未懈怠。據他介紹,玻璃材料中微觀結構動力學過程的實時實空間觀測是實驗凝聚態物理領域現存的重大難題之一。在金屬釕(R u)表面生長的二維二氧化硅薄膜具有原子尺度的平滑結構,是適合掃描隧道顯微鏡表征的理想材料體系,或許可以成為破題之義。利用他此前搭建的高溫快速掃描隧道顯微鏡研究二維二氧化硅中晶態-非晶態結構轉變過程中的原子運動動力學機制,有望為最終理解玻璃的本質和解釋玻璃相變提供更多可用信息。
除了基礎研究,楊澤超對于科研的現實意義也從未松懈關注。微電子器件是時下熱門的轉化方向,“隨著石墨烯的現世,二維半導體材料由于新奇的電子特性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關注。然而絕緣材料也是制備電子器件的不可或缺因素”,他解釋道,“與石墨烯類似,通過機械剝離法可將二維二氧化硅薄膜轉移到其他基底上。作為寬帶隙材料,它完全可以被應用于范德瓦爾斯異質結器件中的絕緣層。”但從現實層面來講,這種構想也并非沒有問題,他的前期研究發現,二維二氧化硅薄膜往往具有大面積缺陷,即孔洞。孔洞的出現會使機械剝離法轉移的成功率直線下降,從而直接影響到其作為絕緣層的性能。那么,究竟如何探究二維二氧化硅的生長動力學機制,并將其與現實生產相結合,通過優化制備條件合成高質量的晶態二維玻璃薄膜,為其在二維異質結器件中的應用鋪平道路,會是楊澤超及團隊未來要攻克的難關。可以預見的是,前路漫漫,道阻且長,但他們已經枕戈待旦、做好了迎接新知的準備。
物理學科的本質在于推究萬物之本源,探尋自然的普遍規律,追求至善致遠的生命境界。但這一遠大的理想絕非僅憑幾個人的力量可以達到,因此,楊澤超也呼吁業內同仁積極攜手、開展合作,力求讓理學的智慧之花盛開在祖國的每一寸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