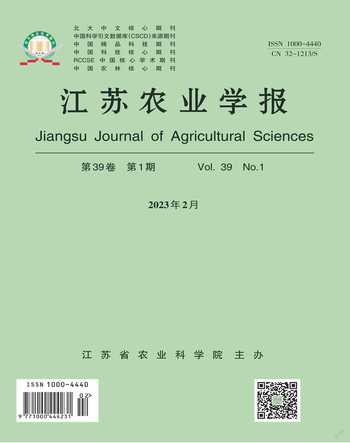大蒜內生巨大芽孢桿菌對鄰苯二甲酸酯的共代謝降解特性及代謝途徑分析
肖霞霞 楊云 馬麗雅 馮發運 葛靜 李勇 王亞 余向陽 馬桂珍



摘要: 土壤鄰苯二甲酸酯(PAE)污染對生態環境和農產品安全均構成威脅。為實現PAE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復,明確共代謝基質對微生物降解PAE的影響機制,從PAE污染的大蒜中篩選獲得能降解PAE的內生菌。通過生理生化特征和16S rRNA基因測序對其種屬進行了鑒定,并研究了內生菌對6種PAE的共代謝降解特性,優化了共代謝降解條件,初步探索了共代謝條件下內生菌對PAE的降解代謝途徑。結果表明:從大蒜中共篩選出3株能降解PAE的內生菌DGB-1、DGB-3和DGB-8,經鑒定3者皆為巨大芽孢桿菌(Bacillus megaterium)。3株菌株均能以6種PAE為碳源生長,但處理3 d后PAE的降解率僅0.89%~10.40%,降解能力較弱。添加D-纖維二糖為共代謝基質后,3株菌株對6種PAE的降解率均顯著提升,其中菌株DGB-1和DGB-3處理3 d后能完全降解20 mg/L質量濃度的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和鄰苯二甲酸丁芐酯(BBP)。以DGB-1為供試菌株,發現吐溫80添加量、碳源種類、碳源濃度和接菌量對6種PAE的降解率均有顯著影響,最佳降解條件為吐溫80添加量0.025%,碳源為D-纖維二糖、濃度為10 mmol/L,接種菌液OD600為0.2。最佳降解條件下,當6種PAE質量濃度為50 mg/L時,鄰苯二甲酸二甲酯(DMP)、鄰苯二甲酸二乙酯(DEP)、DBP、BBP、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和鄰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在MSM培養基中的降解半衰期分別為9.01 d、2.27 d、2.13 d、1.99 d、7.84 d和6.72 d。菌株DGB-1不攜帶質粒,其PAE降解基因位于該菌染色體上;菌株DGB-1可通過水解作用完成對DBP、DEHP和DnOP的第一步降解,但水解作用均較弱;菌株DGB-1對6種PAE的降解代謝需要其細胞膜上的呼吸鏈系統參與,氧化還原反應增強可顯著促進菌株DGB-1對6種PAE的降解。本研究為進一步利用內生菌進行PAE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復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 內生菌;共代謝;鄰苯二甲酸酯;降解途徑
中圖分類號: Q939.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4440(2023)01-0106-12
Co-metabolic 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tabolic pathways analysis of phthalic acid esters by endophytic Bacillus megaterium in garlic
XIAO Xia-xia1,2, YANG Yun1,2, MA Li-ya2, FENG Fa-yun2, GE Jing2,3, LI Yong2, WANG Ya2,3, YU Xiang-yang2,3, MA Gui-zhen1
(1.School of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iangsu Ocean University, Lianyungang 222005, China;2.Institute of Food Safety and Nutrition, Jiang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anjing 210014, China;3.School of the Environment and Safety Engineering,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Soil phthalic acid esters (PAEs) pollution is a threat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bioremediation of PAEs contaminated soil and clarif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metabolic matrix on the degradation of PAEs by microorganisms, endophytic bacteria capable of degrading PAEs were screened from PAEs contaminated garlic. The strains were identified by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16S rRNA gene sequencing, and the co-metabolic 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ix PAEs by endophytes were studied. The co-metabolic degradation conditions were optimized, and the degradation metabolic pathway of PAEs by endophytes under co-metabolic condition was preliminarily explor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endophytic bacteria DGB-1, DGB-3 and DGB-8 capable of degrading PAEs were screened from garlic, and they were identified as Bacillus megaterium. Although three strains of bacteria demonstrated the ability to utilize six different types of PAEs as carbon sources for growth, their capacity for PAEs degradation was limited. After a three-day treatment, degradation rates ranged from 0.89% to 10.40%. After adding D-cellobiose as co-metabolism substrate, the degradation rates of six PAEs by the three strain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mong them, DGB-1 and DGB-3 strains could completely degrade 20mg/L dibutyl phthalate (DBP) and butyl benzyl phthalate (BBP) after three days of treatment. Using DGB-1 as test strain, it was found that the addition amount of Tween 80, carbon source type, carbon source concentration and inoculation dose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degradation rates of six PAEs. The optimal degradation conditions were as follows: the addition amount of Tween 80 was 0.025%, the carbon source was D-cellobiose, the concentration was 10 mmol/L, and OD600value of bacterial solution was 0.2. Under the optimal degradation conditions, when 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s of six PAEs were 50 mg/L, the degradation half-lives of dimethyl phthalate (DMP), diethyl phthalate (DEP), DBP, BBP, di-(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 and di-n-octyl phthalate (DnOP) in inorganic salt medium were 9.01 d, 2.27 d, 2.13 d, 1.99 d, 7.84 d and 6.72 d, respectively. The strain DGB-1 did not carry a plasmid, and its PAEs degradation genes were located on the chromosome. DGB-1 could complete the first step degradation of DBP, DEHP and DnOP through hydrolysis, but the hydrolysis reactions were weak. The degradation of six PAEs by the strain DGB-1 require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respiratory chain system on the cell membrane. The enhanced redox reac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degradation of six PAEs by the strain DGB-1.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use of endophytic bacteria for bioremediation of PAEs contaminated soil.
Key words: endophytic bacteria;co-metabolism;phthalic acid esters;degradation pathways
鄰苯二甲酸酯(PAE)常作為增塑劑應用于農用地膜、棚膜等塑料制品的生產中,塑料產品中PAE含量約占總質量的10%~60%[1]。PAE在合成材料中常以非化學共價鍵形式存在[2],容易被釋放到大氣、水體等環境介質中,并最終造成耕地土壤PAE污染[3]。中國設施大棚土壤中PAE污染狀況不容樂觀,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等地區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農田土壤中的主要PAE污染種類為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和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平均含量高達9.23 mg/kg和11.00 mg/kg[4],遠高于美國環保局制定的土壤PAE控制標準[5]。PAE具有較強的生殖毒性和“三致”效應[6],土壤PAE污染不但對生態環境和農產品安全構成嚴重威脅,還可通過食物鏈積累放大進一步增加人體PAE暴露風險。因此,如何實現耕地土壤中PAE的高效去除已成為生態環境領域的研究熱點和難點。
在土壤PAE治理技術中,物理修復工程量大、成本昂貴;化學修復效率高、降解譜廣,但降低地力并增加修復成本;植物修復效率低、周期長[6]。利用微生物修復土壤無二次污染,頗具優勢,在降解土壤PAE中具有較好的應用潛力[7]。國內外針對PAE降解菌的分離篩選及功能研究已開展多年,目前已有包括假單胞菌(Pseudomonas sp.)、鞘氨醇單胞菌(Sphingomonas sp.)和巨大芽孢桿菌(Bacillus megaterium)在內的超過80個PAE降解菌得到了詳細的研究報道[6,8-9]。但這些 PAE降解菌主要從水體、土壤及污泥等環境介質中分離獲得,而從植物體內分離篩選具有降解PAE功能內生菌的報道較少[10]。在植物根際接種內生菌不但顯著促進了土壤中農藥、多環芳烴等有機污染物降解,也明顯加速了植物體內有機污染物降解速率[11-13]。因此,利用植物內生菌同時去除耕地土壤和作物體內的PAE具有重要應用潛力,對于PAE污染土壤的修復和降低人體PAE暴露風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0]。
多數PAE降解菌能以一種或多種PAE為碳源進行生長代謝[8]。然而,自然環境中碳源種類繁多,降解菌對PAE的代謝途徑、降解速率等特征可能因其他碳源存在而發生顯著改變[14]。此外,當土壤中污染物濃度較低時,微生物生長代謝所需的生長基質不足,微生物可能利用其他生長基質以提供生命活動所需的碳源和能源[15],這些碳源物質可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和相關降解酶活性,從而加速污染物的共代謝降解[16]。因此,開展微生物對PAE的共代謝降解研究,對于強化功能細菌對PAE污染土壤的修復作用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本實驗室前期研究發現,大蒜及其產地土壤中存在PAE污染風險。其中,大蒜中的主要PAE污染種類為DBP,大蒜產地土壤中主要PAE檢出種類為DMP(鄰苯二甲酸二甲酯)、DEP(鄰苯二甲酸二乙酯)、DBP和DEHP等[17]。基于此,本研究從PAE污染大蒜中篩選獲得具有降解PAE功能的內生菌,通過生理生化試驗、結合16S rRNA基因測序對內生菌進行種屬鑒定,考察了不同內生菌對PAE的共代謝降解特性,優化了共代謝降解條件,初步探索了內生菌對中國土壤中主要PAE污染類型的降解代謝途徑,分析了共代謝底物對PAE降解途徑的影響。研究結果可以豐富內生菌強化PAE降解代謝理論,為進一步利用內生菌進行PAE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復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儀器和試劑
1.1.1 主要儀器 氣相色譜儀(島津Nexis GC-2030,日本島津公司產品)、掃描電子顯微鏡(蔡司ZEISS EVO-LS10,德國蔡司集團產品)、離子濺射儀(CRESSINGTON 108auto,英國cressington公司產品)、臨界點干燥儀(Quorum K850,英國Quorum公司產品)、全波長酶標儀(Biotek EPOCH2,美國BioTek公司產品)、超純水機(Millipore,美國 Merck Millipore 公司產品)、數顯型多管式旋渦混合儀(DMT-2500,鄭州明天儀器設備有限公司產品)、超聲波清洗器(KQ-500DV,昆山超聲儀器有限公司產品)、高通量樣品磨樣機(CK-2000,北京托摩根生物有限公司產品)、高速冷凍離心機(中科中佳KDC-220HR,安徽中科中佳科學儀器有限公司產品)。
1.1.2 化學試劑 99.0% DMP、99.5% DEP和99.0% DEHP,購自上海麥克林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9.5%DBP購自上海凌峰化學試劑有限公司;98%鄰苯二甲酸丁芐酯(BBP)和98%鄰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購自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種PAE(DMP、DEP、DBP、BBP、DEHP和DnOP)混合標準液:用天平稱取6種PAE各1.0 g,用色譜級乙腈將其定容至100 ml,配置成6種PAE質量濃度分別為10 000 mg/L的標準液。
色譜級正己烷購自北京邁瑞達科技有限公司;色譜純乙腈購自德國Merck公司;硫酸錳購自國藥集團化學試劑有限公司;硫酸鎳購自成都科龍化工試劑廠;2.4-二硝基苯酚(DNP)購自美國Sigma-Aldrich公司。
1.1.3 培養基 無機鹽培養基(MSM): MgSO4·7H2O 0.40 g、 K2HPO40.20 g、 (NH4)2SO40.20 g、 CaSO40.08 g、微量元素溶液1 ml,去離子水定容至1 L,調節pH值為7.2±0.2,121 ℃高壓蒸汽滅菌20 min備用。微量元素溶液參考Ma等[18]的方法配制。
R2A培養基:胰蛋白胨0.25 g、酸水解酪蛋白0.50 g、酵母浸粉0.50 g、可溶性淀粉0.50 g、磷酸氫二鉀0.30 g、硫酸鎂0.10 g、丙酮酸鈉0.30 g、蛋白胨0.25 g、葡萄糖0.50 g,去離子水定容至1 L,調節pH值為7.2±0.2。
LB液體培養基:牛肉膏5.0 g、蛋白胨10.0 g、NaCl 10.0 g,去離子水定容至1 L,調節pH值為7.0±0.2,121 ℃高壓蒸汽滅菌20 min備用。固體培養基分別在上述液體培養基中加瓊脂15 g,滅菌后備用。
20 mmol/L PBS緩沖液:NaH2PO4·2H2O 0.592 8 g、Na2HPO4·12H2O 5.799 6 g,超純水定容至1 L,調節pH值為7.4。
1.2 PAE降解菌的分離篩選、純化與鑒定
1.2.1 菌株的分離篩選與純化 供試大蒜(Alliumstivum L.)品種為大青稞,采集自江蘇省農業科學院蔬菜試驗田。該試驗田長期用于PAE污染修復試驗,PAE污染質量分數約80mg/kg。待大蒜生長至鱗莖膨大期,隨機采集5株大蒜苗帶回實驗室,自來水清洗后,參考馮發運等[19]的方法進行莖葉部分表面消毒。用無菌剪刀將消毒后的大蒜莖葉樣品剪成2~3 cm小段,取4段樣品置于10 ml滅菌的塑料離心管中,添加1 ml無菌水和2顆滅菌的氧化鋯陶瓷珠,利用高通量樣品磨樣機700 r/min研磨5 min。取研磨液100 μl轉入100 ml的LB培養液中,30 ℃、180 r/min搖床振蕩培養12 h,5 000 r/min離心5 min收集菌體, MSM清洗3次,將菌體重懸于MSM培養液中,取100 μl菌懸液均勻涂布于MSM固體培養基,該培養基含6種質量濃度均為20 mg/L的PAE。30 ℃條件下培養48 h后,挑取單菌落在以PAE為碳源的MSM固體培養基上劃線,對目標菌株進行分離純化。重復操作5次后,挑選能以PAE為碳源生長的菌株,轉入20%甘油中-80 ℃保藏。
1.2.2 菌株鑒定 將保藏的內生菌轉接至LB培養液中,30 ℃條件下培養24 h,獲得活化菌株。利用革蘭氏染色法對細菌進行分類。
氨芐青霉素抗性:將內生菌接種于氨芐青霉素終質量濃度為50 mg/L的LB培養液中,30 ℃、180 r/min搖床培養24 h,觀察細菌生長情況。
菌落形態:將活化的菌株在LB培養基上劃線,置于30 ℃的恒溫培養箱中培養24 h,待菌落形成后,觀察并記錄其形態、大小、顏色。
細菌形態:內生菌在LB培養液中30 ℃、180 r/min振蕩培養12 h,離心收集菌體,20 mmol/L的PBS緩沖液清洗菌體3次,每次10 min。通過光學顯微鏡初步觀察菌株的形態特征。然后,向菌體中加入終體積分數2.5%的戊二醛,混勻后室溫下浸泡12 h,8 000 r/min離心5 min,棄上清液收集菌體,用酒精進行梯度洗脫,最后用100%酒精浸泡3次,每次30 min,利用掃描電子顯微鏡進一步觀察菌株的形態特征。
細菌16S rRNA基因測序委托北京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將獲得的菌株16S rRNA序列在NCBI中進行BLAST分析,與GenBank數據庫中的基因序列進行同源性比較。利用MEGA7.0軟件采用鄰位連接法(Neighbour Joining)繪制系統發育樹。
1.3 菌株生長曲線的測定
將篩選出的菌株挑取單菌落接種于50 ml LB液體培養基中,在30 ℃、180 r/min下振蕩培養30 h,獲得種子液,用滅菌的LB培養液調節種子液細菌含量,使其600 nm處吸光值(OD600)為1.0。將種子液取1ml接種于100 ml LB培養基中,每隔2 h測定1次OD600值,連續測定30 h,以OD600為縱坐標,時間為橫坐標,繪制菌株生長曲線。
1.4 菌株對PAE的降解試驗
1.4.1 共代謝降解試驗 以篩選的菌株為供試菌株,以D-纖維二糖為生長基質、PAE為共代謝底物,開展共代謝降解試驗。將篩選得到的菌株分別接種于LB液體培養基中,搖床培養14 h,離心收獲菌體,MSM清洗三遍。取197.6 ml MSM液體培養基,依次添加10%吐溫80(助溶劑)2 ml[20]、10 mg/ml的6種PAE混合標準液0.4 ml,將其充分混勻后取20 ml分裝于玻璃錐形瓶中,作為未接種菌液樣品的對照組(CK),將清洗好的菌株重懸于剩余MSM培養液中,調整培養液初始OD600為0.1,分裝于玻璃錐形瓶中,設置加D-纖維二糖和不加D-纖維二糖兩個處理。加糖濃度為10 mmol/L。將玻璃錐形瓶密封后于180 r/min、30℃搖床中培養3 d,取樣檢測MSM培養基中PAE質量濃度。每處理3次重復。
1.4.2 共代謝降解條件優化 選擇降解能力強,且具有氨芐抗性的菌株開展共代謝降解條件優化試驗。以吐溫80添加量0.1%、10 mmol/L的D-纖維二糖、培養液初始OD6000.1為初始值,開展吐溫80添加量(0.006%、0.012%、0.025%、0.050%和0.100%),碳源種類(D-葡萄糖、D-果糖、D-纖維二糖、蔗糖和麥芽糖),碳源添加量(1 mmol/L、5 mmol/L、10 mmol/L、20 mmol/L和50 mmol/L),細菌接種量(OD600為0.05、0.10、0.20、0.30、0.40和0.50)對菌株生長及PAE降解的單因素影響試驗,依次確定最佳吐溫80添加量、最佳碳源種類、最佳碳源添加量、最佳初始接菌量。試驗步驟及其他試驗條件參考方法1.4.1,以不接菌液處理為對照,每組3次重復。
在最優條件下,進一步研究了菌株對不同質量濃度PAE(1 mg/L、5 mg/L、10 mg/L、20 mg/L和50 mg/L)的降解能力。分別在1 d、2 d、3 d、5 d和7 d取樣測定菌株含量(OD600)和MSM培養液中PAE殘留量,并計算PAE降解率和半衰期[21]。
式中:C0為初始PAE質量濃度(mg/L);Ct為t時間的PAE質量濃度(mg/L);k為降解速率常數(d-1);t1/2為半衰期(d)。
1.5 PAE降解菌代謝途徑分析
1.5.1 細菌質粒DNA的提取 將篩選獲得的菌株DGB-1轉接于LB液體培養基中,30 ℃,180 r/min培養14 h,取2 ml菌液,根據AxyPrep質粒DNA小量試劑盒提取質粒,菌塊中添加100 mg/ml的溶菌酶10 μl,供試菌株設置2個重復,枯草芽孢桿菌菌株W34為對照(該菌確認含有質粒)。取8 μl質粒,加入2 μl的5×Loading buffer,混勻,在1.0%瓊脂糖凝膠上進行電泳檢測,電壓為130 V。通過凝膠成像系統進行觀察,與Marker比較確定質粒大小。
1.5.2 胞內粗酶液對6種PAE的降解 胞內粗酶液制備:取10%的吐溫80 0.4 ml分別加入159.6 ml MSM和R2A培養基中,得到吐溫80含量為0.025%的MSM培養基和R2A培養基。將DGB-1接種于200 ml的LB中,30 ℃、180 r/min培養14 h。離心收獲菌體,MSM培養液清洗3遍,分別重懸于20 ml R2A和MSM培養基中,調整菌液含菌量,使得初始OD600為0.1。設置加菌、菌+糖、菌+PAE、菌+糖+PAE 4個處理,加糖處理D-纖維二糖濃度為10 mmol/L,加PAE處理6種PAE處理質量濃度均為20 mg/L。30℃、180 r/min搖床振蕩培養3 d,離心收獲菌體,20 mmol/L PBS清洗3次,置于-20 ℃冰箱冷凍2 h后,取出菌體于滅菌研缽中,依次加入液氮和20 mmol/L的PBS緩沖液進行研磨,研磨液(粗酶液)轉入5 ml容量瓶中并用PBS緩沖液定容后,置于冰浴中保存備用。
PAE體外降解試驗:取1.98 ml粗酶液,轉入10 ml玻璃試管中,添加20 μl 1 000mg/L的6種PAE標液(溶劑為乙腈),使PAE終質量濃度為10 mg/L,用無菌橡膠塞密封后,置于37 ℃培養箱中反應4 h后,向試管中添加2 ml正己烷提取PAE,利用氣相色譜法(GC)分析粗酶液中PAE含量。
1.5.3 DNP(2,4-二硝基苯酚)、Mn2+和Ni2+對6種PAE降解的影響 取10%吐溫80 0.4 ml、10 g/L的6種PAE混合液0.32 ml加入159.28 ml的無機鹽培養基中,得到吐溫80含量0.025%、PAE含量20mg/L的無機鹽培養基。將菌株DGB-1接種于LB培養基,30 ℃、180 r/min下培養14 h,菌液離心棄上清液后獲得菌體,MSM培養基清洗3次,將清洗后的菌體重懸于上述無機鹽培養基中,調整細菌含量使得培養基初始OD600為0.2。設置2組試驗,第1組設置4個不同的處理,分別為不加糖不加DNP(-糖-DNP)、不加糖加DNP(-糖+DNP)、加糖不加DNP(+糖-DNP)和加糖加DNP(+糖+DNP)。其中,DNP終濃度為0.5 mmol/L,D-纖維二糖終濃度為10 mmol/L;第2組設置5個不同的處理,分別為加糖(+糖)、加糖加0.1 mmol/L Mn2+(+糖+0.1 mmol/L Mn2+)、加糖加1.0 mmol/L Mn2+(+糖+1.0 mmol/L Mn2+)、加糖加0.1 mmol/L Ni2+(+糖+0.1 mmol/L Ni2+)、加糖加1.0 mmol/L Ni2+(+糖+1.0 mmol/L Ni2+),D-纖維二糖終濃度為10 mmol/L。以不加細菌而加入等體積滅菌生理鹽水的處理為空白對照,每處理3次重復,搖床中振蕩培養,3 d后取樣測定OD600、提取MSM培養基中的PAE,并利用GC法測定PAE含量。
1.6 樣品中PAE提取及檢測分析
MSM培養基中PAE提取:參考Li等[22]的提取方法稍加改進,移液器移取2 ml MSM培養基,移入10 ml玻璃管中,添加2 ml正己烷,多管式旋渦混合儀2 000 r/min渦旋2次,每次5 min,超聲提取2 min,離心5 min后取上層有機相,利用氣相色譜儀分析6種PAE含量。
采用GC法分析樣品中PAE含量,儀器色譜工作條件如下:色譜柱為SH-Rtx-5(30.00 m×0.25 mm,0.25 μm);載氣為高純氮氣,輔助氣體為高純氫氣 和普通空氣,色譜柱流量1.21 ml/min,分流比2.0,進樣量1.0 μl,進樣口溫度280 ℃。柱箱升溫程序:初始溫度120 ℃,保持1 min,以20 ℃/min速率升溫至220 ℃,以5 ℃/min速率升溫至235 ℃,以10 ℃/min速率升溫至245 ℃,以5 ℃/min速率升溫至255 ℃,保持2 min,再以10 ℃/min速率升溫至275 ℃,保持2 min。
1.7 數據處理
采用Excel 2016和Origin 2021軟件制圖。采用SPSS 22.0進行數據統計分析,不同試驗組間差異性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或Tukeys多重比較法進行顯著性檢驗。
2 結果與討論
2.1 PAE降解菌的分離與鑒定
通過多次分離純化后,獲得3株可以PAE為碳源生長的植物內生細菌,分別命名為DGB-1、DGB-3和DGB-8。革蘭氏染色后3株菌株均呈現紅色。氨芐青霉素抗性試驗結果顯示,DGB-1和DGB-8可耐受50 mg/L的氨芐青霉素,但DGB-3不具有氨芐青霉素耐受性。3株菌株的菌落均為圓形、乳白色、不透明,其中DGB-1、DGB-3菌落邊緣整齊(圖1a和圖1b),而DGB-8菌落邊緣呈鋸齒狀(圖1c)。
在光學顯微鏡下,3株菌株均為長桿狀(圖1d~圖1f);掃描電鏡結果進一步證明3株菌株為桿狀細菌,其中DGB-1和DGB-3形態較為類似,呈短鏈排列(圖1g和圖1h),而DGB-8則呈長鏈排列(圖1i)。將3株細菌的16S rRNA基因序列與NCBI數據庫中的序列進行比對,并通過鄰接法構建系統發生樹。結果表明,3株菌株與巨大芽孢桿菌(Bacillus megaterium)相似度最高,其中DGB-1和DGB-3的親緣關系較近,DGB-8與上述2株菌株親緣關系相對較遠,而與巨大芽孢桿菌EGI278的親緣關系更為接近。DGB-1、DGB-3和DGB-8與同樣能利用DMP、DEP、DBP、DEHP和DnOP等多種PAE為碳源生長的美人蕉內生巨大芽孢桿菌YJB3[10]的親緣關系相對較遠(圖2)。基于3株菌株的生理生化特征和16S rRNA基因測序鑒定結果,DGB-1、DGB-3和DGB-8均鑒定為巨大芽孢桿菌。
2.2 菌株的生長曲線
如圖3所示,LB培養基中菌株DGB-1、DGB-3和DGB-8在0~4 h生長較慢,處于遲緩生長期;4 h后細菌繁殖速度明顯加快,進入對數生長期;12 h時后3株菌株生長速率又再次減慢并在24 h后逐漸進入穩定生長期。此外,在細菌培養的30 h內,DGB-1和DGB-3的生長速率無顯著性差異;4~12 h,DGB-8的生長速率顯著低于DGB-1和DGB-3,14 h后3株菌株的生長速率無顯著性差異(圖3)。基于3株菌株的生長特點,選擇接種14 h菌齡的細菌開展后續PAE降解試驗。
2.3 菌株的共代謝降解
如圖4所示,不加糖的情況下,處理3 d后,加菌處理組MSM培養液中的PAE含量僅比對照下降0.89%~10.40%,僅DGB-1菌株對DBP和BBP的降解率與CK有顯著差異。這說明不加糖情況下DGB-1、DGB-3和DGB-8對6種PAE的降解能力均較差。添加D-纖維二糖后,菌株DGB-1對DMP、DEP、DBP、BBP、DEHP和DnOP的降解率分別為47.8%、89.5%、100.0%、100.0%、56.4%和79.4%;菌株DGB-3對DMP、DEP、DBP、BBP、DEHP和DnOP的降解率分別為50.7%、90.9%、100.0%、100.0%、53.2%和74.9%;菌株DGB-8對DMP、DEP、DBP、BBP、DEHP和DnOP的降解率分別為11.1%、20.8%、30.5%、29.4%、10.1%和13.2%。以D-纖維二糖為共代謝基質,可顯著提高3株菌株對6種PAE的降解能力。DGB-1與DGB-3對6種PAE均有較高的降解能力,兩者之間無顯著差異,而DGB-8對6種PAE的降解率均顯著低于DGB-1和DGB-3。Feng等[10]的研究結果也表明,添加醋酸鈉作為外源碳源可顯著促進巨大芽孢桿菌YJB3對PAE的共代謝降解[23]。這可能是由于PAE、多環芳烴(PAH)等有機污染物很難直接作為碳源被微生物利用[23],而糖類、有機酸和氨基酸等化合物在為微生物提供營養的同時,也可為微生物生長代謝提供電子受體或供體,從而促進微生物對有機污染物的降解能力,該共代謝現象在高分子量、難降解的有機污染物中較為常見[16,24]。
由于DGB-1具有較好的PAE降解能力,且對氨芐青霉素有較高的抗性,所以選擇DGB-1開展共代謝降解條件優化試驗。
2.4 菌株DGB-1的共代謝降解條件優化
2.4.1 PAE生物降解的影響因素 吐溫80常作為增溶劑促進介質中PAE溶解[20]。不同初始吐溫80添加量對6種PAE降解率的影響如圖5A所示。 吐溫80添加量在0.006%~0.100%,DBP和BBP的降解率均接近100%;而DMP、DEP、DEHP和DnOP的降解率隨著吐溫80添加量增加呈先增加后下降的趨勢。當吐溫80添加量為0.025%時,6種PAE的降解率均達最大值(圖5A),因此最佳吐溫80添加量為0.025%。
在吐溫80添加量為0.025%條件下, 不同共代謝基質(碳源種類)對6種PAE降解率的變化如圖5B所示。與不加碳源的CK比,所有碳源處理組6種PAE的降解率顯著增加,說明5種碳源均可促進DGB-1對6種PAE的降解。這可能與添加碳源顯著促進了細菌生長有關。通過酶標儀檢測菌液的OD600,發現添加碳源處理組OD600(0.535~0.690)顯著高于CK(0.107),即添加碳源,DGB-1的生物量得到顯著提升。從碳源類型看,二糖(麥芽糖、蔗糖和D-纖維二糖)對DBP、BBP、DEHP和DnOP的促降解效果顯著優于單糖(葡萄糖和果糖)。然而,二糖處理組菌液OD600(0.535~0.568)均低于單糖處理組(0.639~0.690),說明細菌生物量增加不是促進PAE降解的唯一原因,可能參與二糖水解的部分酶類對PAE的降解有促進作用[25-26]。此外,添加D-纖維二糖后,DGB-1對DMP、DEP、DBP、BBP、DEHP和DnOP的降解率分別達34.6%、65.9%、100.0%、100.0%、50.5%和44.4%,對部分PAE降解率顯著優于麥芽糖和蔗糖。因此,最佳碳源種類為D-纖維二糖。
在最優吐溫80添加量的條件下,不同D-纖維二糖濃度對6種PAE降解率的影響如圖5C所示。隨著D-纖維二糖濃度的增加,DEHP和DnOP的降解率不斷增加,而DMP、DEP、DBP和BBP的降解率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趨勢。檢測DGB-1菌液的OD600,發現D-纖維二糖濃度為1 mmol/L、5 mmol/L、10 mmol/L、20 mmol/L和50 mmol/L時菌液OD600值分別為0.207、0.464、0.585、1.373和1.423,說明隨著碳源濃度增加DGB-1的生物量顯著增加。當D-纖維二糖初始濃度為10 mmol/L時,除DEHP和DnOP外的4種PAE降解率均達到最大值,因此最優碳源濃度為10 mmol/L。
不同接菌量對菌株DGB-1降解PAE的影響如圖5D所示。隨著初始接菌量增加,6種PAE的降解率均呈增加趨勢,證明細菌生物量增加可促進PAE降解。此外,菌株DGB-1菌液的OD600由0.05增加至0.50,6種PAE的降解率僅增加1.25%~21.0%,說明細菌生物量增加不是影響6種PAE降解的主要因素。當初始接菌量OD600≥0.2時,菌株DGB-1對DEP、DBP、BBP、DEHP和DnOP 5種PAE的降解率增加不顯著,因此菌株DGB-1菌液的OD600等于0.2為最優初始接種量。
以上單因素試驗結果表明,菌株DGB-1的共代謝優化條件是吐溫80添加量0.025%、10mmol/L的D-纖維二糖為共代謝基質、適宜接菌量是菌液的OD600為0.20。此外,菌株DGB-1生物量的增加與PAE的降解率上升并不成比例,說明菌液生物量增加并不是提高PAE降解率的主要原因,添加碳源作為共代謝底物,菌株DGB-1細胞中催化PAE降解的酶活性增強可能是PAE加速降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2.4.2 最優條件下菌株DGB-1對6種PAE的降解特性 基于最優降解條件,菌株DGB-1對不同初始質量濃度PAE處理3 d后的降解特性如圖6所示。當PAE初始質量濃度≤20 mg/L,DGB-1可完全降解DBP、BBP和DEHP;DMP、DEP和DnOP的降解率最高可達48.6%、92.8%和100.0%,說明菌株DGB-1對6種PAE均具有良好的降解效果,且具備同時降解6種PAE的潛力。此外,6種PAE在MSM培養基中的降解動態均符合一級動力學方程(表1)。當PAE質量濃度為5 mg/L,DBP和BBP的t1/2值分別為0.66 d和0.91 d,說明菌株DGB-1對短鏈PAE(碳鏈長度<7)的降解速度較快。此外,菌株DGB-1對高相對分子質量、難降解的長鏈PAE如DEHP和DnOP的降解速度也很快(t1/2值分別為1.08 d和0.67 d)。當PAE質量濃度增加至50 mg/L,DGB-1對PAE的降解半衰期均明顯延長(DEP除外),其中DBP、BBP和DMP的半衰期延長1~2 d,而DEHP和DnOP的降解半衰期延長了6 d以上(表1)。這可能是由于高濃度PAE脅迫導致菌株DGB-1細胞生長速率的變化所致[27-28]。
2.5 菌株DGB-1的PAE降解途徑
微生物對PAE、PAH等有機污染物的降解主要依賴其降解酶[10,29],而酶的編碼基因可能位于其基因組或質粒上[30-31],細菌對PAE的降解也可能是質粒和染色體上基因共同作用的結果。然而,菌株DGB-1是否攜帶質粒、質粒基因組中是否含有PAE降解基因尚不清楚。
2.5.1 菌株質粒DNA提取 以含質粒的枯草芽孢桿菌W34為對照,提取了菌株DGB-1的質粒DNA。如圖7所示,菌株W34存在質粒,基因片段大小約2 kb,說明質粒提取方法適用于革蘭氏陽性菌。然而,添加菌株DGB-1質粒DNA的泳道無條帶,說明菌株DGB-1不攜帶可降解PAE基因的質粒。研究結果表明,菌株DGB-1的PAE降解基因位于該菌的染色體上。
2.5.2 粗酶液對PAE的降解作用 與細菌對其他有機污染物降解類似,細菌對PAE的降解主要依賴其酶的催化作用[27,32]。不同培養基培養3 d后,菌株DGB-1的粗酶液對6種PAE的降解作用如圖8所示。PAE脅迫條件下,與不加糖的CK比,加糖處理組DBP含量(圖8A和8B)、DnOP含量(圖8A)和DEHP含量(圖8B)顯著下降,說明PAE脅迫下加糖可激活DBP、DEHP和DnOP降解酶的活性。本研究發現加糖可以顯著促進菌株DGB-1對DBP的降解(圖4A),并且菌株DGB-1的粗酶液也具有一定的DBP降解能力,但粗酶液對DBP的降解率僅8.1%~12.8%(圖8A和8B),說明菌株DGB-1對DBP的水解作用較弱。此外,加糖處理組MSM培養基培養細菌制備的粗酶液不具備DEHP催化活性(圖8A),而寡營養培養基R2A培養細菌制備的粗酶液具有DEHP催化活性(圖8B),說明菌株DGB-1降解酶基因的啟動子可能為誘導型。然而,在PAE和D-纖維二糖的共同誘導下,雖然菌株DGB-1的粗酶液對DEHP和DnOP有一定的降解能力,但DEHP和DnOP的降解率僅為8.58%和7.78%,說明菌株DGB-1對DEHP和DnOP的水解作用也較弱。
2.5.3 細菌呼吸鏈系統對菌株DGB-1降解6種PAE的影響 上述分析表明,加糖條件下菌株DGB-1對DBP的降解率可達100%(圖4A),但菌株DGB-1的胞內酶粗提液對DBP的水解作用較弱(圖8),推測菌株DGB-1還存在其他的DBP降解代謝途徑。因此,進一步研究了呼吸鏈系統(氧化還原酶系)對菌株DGB-1降解PAE的影響。
DNP作為解耦聯劑可以抑制細菌細胞膜上的氧化磷酸化過程,從而抑制細菌的呼吸作用[33]。如圖9A所示,與CK相比,加糖不加DNP處理下,DMP、DEP、DBP、BBP、DEHP和DnOP的降解率分別為41.10%、81.26%、100.00%、97.67%、41.25%和79.41%,加糖加DNP處理組6種PAE的降解率分別為24.81%、51.20%、60.00%、48.80%、30.37%、61.47%,比加糖不加DNP處理均顯著下降,說明DNP抑制了6種PAE的降解。同樣不加糖時,加DNP處理的降解率亦低于不加DNP處理。此外,加糖不加DNP處理組與加糖加DNP處理組菌液OD600分別為0.766和0.761,表明DNP對菌株DGB-1生長的影響不顯著。說明菌株DGB-1細胞膜上的呼吸鏈系統參與了6種PAE的降解代謝。
Mn2+和Ni2+屬于過渡金屬離子,具有可變的氧化數,可與底物(PAE)發生電子交換作用,從而促進底物的氧化還原過程[34-35]。如圖9B和9C所示,添加Mn2+和Ni2+顯著促進了菌株DGB-1對6種PAE的降解,且隨著Mn2+和Ni2+濃度增加PAE降解率均呈增加趨勢。這說明細胞膜氧化還原反應的增強可促進PAE降解。
3 結論
從大蒜中篩選獲得3株PAE降解菌DGB-1、DGB-3和DGB-8,鑒定分析均為巨大芽孢桿菌(Bacillus megaterium)。雖然3株菌能以6種PAE為碳源生長,但對6種PAE的降解能力均較弱。糖類可顯著促進3株細菌對PAE的共代謝降解。添加糖類作為生長基質,菌株DGB-1和DGB-3對DBP和BBP的降解率可達100%。吐溫80添加量、碳源種類、碳源濃度和細菌接種量對菌株DGB-1生長及PAE降解均有顯著影響。最佳降解條件是吐溫80添加量0.025%,10 mmol/L的D-纖維二糖為共代謝基質,菌株DGB-1接種量OD600為0.2。研究還發現菌株DGB-1不攜帶質粒,說明該菌的PAE降解基因位于其染色體上。菌株DGB-1可同時通過水解和氧化還原2種途徑降解PAE。其中,在PAE和D-纖維二糖的共同誘導下,菌株DGB-1可通過水解途徑完成對DBP、DEHP和DnOP的第一步降解,但對這3種PAE的水解作用較弱;菌株DGB-1可通過氧化還原途徑降解DMP、DEP、DBP、BBP、DEHP和DnOP,添加Mn2+和Ni2+顯著提高了菌株DGB-1對這6種PAE的降解速率。
參考文獻:
[1] WANG J, CHEN G, CHRISTIE P, et al. Occurrence and risk assessment of phthalate esters (PAEs) in vegetables and soils of suburban plastic film greenhouse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5, 523: 129-137.
[2] MENG K, REN W, TENG Y, et al. Application of biodegradable seedling trays in paddy fields: Impacts on the microbial community[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656: 750-759.
[3] KONG S, JI Y, LIU L, et al. Diversities of phthalate esters in suburban agricultural soils and wasteland soil appeared with urbanization in China[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2, 170: 161-168.
[4] 馮宇希,涂茜穎,馮乃憲,等. 我國溫室大棚鄰苯二甲酸酯(PAEs)污染及綜合控制技術研究進展[J]. 農業環境科學學報, 2019, 38(10): 2239-2250.
[5] WANG J, LUO Y, TENG Y, et al. Soil contamination by phthalate esters in Chinese intensive vegetable production systems with different modes of use of plastic film[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3, 180: 265-273.
[6] FENG N X, LIANG Q F, FENG Y X, et al. Improving yield and quality of vegetable grown in PAEs-contaminated soils by using novel bioorganic fertilizer[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20,739:139883.
[7] CHENG J, LIU Y, WAN Q, et al. Degradation of dibutyl phthalate in two contrasting agricultural soils and its long-term effects on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8, 640: 821-829.
[8] 韓永和,何睿文,李 超,等. 鄰苯二甲酸酯降解細菌的多樣性、降解機理及環境應用[J]. 生態毒理學報, 2016, 11(2): 37-49.
[9] ZHAO H M, DU H, HUANG C Q, et al. Bioaugmentation of exogenous strain Rhodococcus sp. 2G can efficiently mitigate di(2-ethylhexyl) phthalate contamination to vegetable cultivation[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019, 67(25): 6940-6949.
[10]FENG N X, YU J, MO C H, et al. Biodegradation of di-n-butyl phthalate (DBP) by a novel endophytic Bacillus megaterium strain YJB3[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8, 616: 117-127.
[11]FENG F Y, ZHAN H L, WAN Q, et al. Rice recruits Sphingomonas strain HJY-rfp via root exudate regulation to increase chlorpyrifos tolerance and boost residual catabolism[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 2021, 72(15): 5673-5686.
[12]FENG F Y, GE J, LI Y, et al. Enhanced degradation of chlorpyrifos in rice (Oryza sativa L.) by five strains of endophytic bacteria and their plant growth promotional ability[J]. Chemosphere, 2017, 184: 505-513.
[13]SUN K, LIU J, GAO Y, et al. Inoculating plants with the endophytic bacterium Pseudomonas sp. Ph6-gfp to reduce phenanthrene contaminatio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5, 22(24): 19529-19537.
[14]張銀萍,王 芳,楊興倫,等. 土壤中高環多環芳烴微生物降解的研究進展[J]. 微生物學通報, 2010, 37(2): 280-288.
[15]GRANDCLEMENT C, SEYSSIECQ I, PIRAM A, et al. From the conventional biological wastewater treatment to hybrid processes, the evaluation of organic micropollutant removal: A review[J]. Water Research, 2017, 111: 297-317.
[16]王 亞,馮發運,葛 靜,等. 植物根系分泌物對土壤污染修復的作用及影響機理[J]. 生態學報, 2022, 42(3): 829-842.
[17]王 亞,肖霞霞,楊 云,等. 江蘇產區大蒜中鄰苯二甲酸酯含量檢測及溯源分析[J]. 環境科學, 2023. doi: 10.13227/j.hjkx.202204278.
[18]MA Z, LIU J, DICK R P, et al. Rhamnolipid influences biosorption and biodegradation of phenanthrene by phenanthrene-degrading strain Pseudomonas sp. Ph6[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8, 240:359-367.
[19]馮發運,朱 宏,李俊領,等. 一株小飛蓬內生毒死蜱降解菌的分離鑒定及其降解特性初探[J]. 農藥學學報, 2015, 17(1): 89-96.
[20]KONG X, JIN D, TAI X, et al. Bioremediation of dibutyl phthalate in a simulated agricultural ecosystem by Gordonia sp. strain QH-11 and the microbial ecological effects in soil[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667: 691-700.
[21]CHENG J, WAN Q, GE J, et al. Major factors dominating the fate of dibutyl phthalate in agricultural soils[J].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2019, 183: 109569.
[22]LI Y, YAN H, LIU Q, et al. Accumulation and transport patterns of six phthalic acid esters (PAEs) in two leafy vegetables under hydroponic conditions[J]. Chemosphere, 2020, 249: 126457.
[23]PANDEY J, CHAUHAN A, JAIN R K. Integrative approaches for assessing the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of in situ bioremediation[J]. FEMS Microbiology Reviews, 2009, 33(2): 324-375.
[24]RENTZ J A, ALVARE P J J, SCHNOOR J L. Benzo[a]pyrene degradation by Sphingomonas yanoikuyae JAR02[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8, 151(3): 669-677.
[25]CHEN X, ZHANG X L, YANG Y, et al. Biodegradation of an endocrine-disrupting chemical di-n-butyl phthalate by newly isolated Camelimonas sp. and enzymatic properties of its hydrolase[J]. Biodegradation, 2015, 26(2): 171-182.
[26]HUANG Y H, HUANG X J, CHEN X H, et al. Biodegradation of di-butyl phthalate (DBP) by a novel endophytic bacterium Bacillus subtilis and its bioaugmentation for removing DBP from vegetation slurr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8, 224: 1-9.
[27]ZHAO H M, HU R W, HUANG H B, et al. Enhanced dissipation of DEHP in soil and simultaneously reduced bioaccumulation of DEHP in vegetable using bioaugmentation with exogenous bacteria[J]. Biology and Fertility of Soils, 2017, 53(6): 663-675.
[28]CHANG B V, YANG C M, CHENG C H, et al. Biodegradation of phthalate esters by two bacteria strains[J]. Chemosphere, 2004, 55(4): 533-538.
[29]SUBASHCHANDRABOSE S R, VENKATESWARLU K, NAIIDU R, et al. Biodegra dation of high-molecular weight PAHs by Rhodococcus wratislaviensis strain 9: Over expression of amidohydrolase induced by pyrene and BaP[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9,651:813-821.
[30]PENG R H, XIONG A S, XUE Y, et al. Microbial biodegradation of polyaromatic hydrocarbons[J]. FEMS Microbiology Reviews, 2008, 32(6): 927-955.
[31]EATON R W. Plasmid-encoded phthalate catabolic pathway in Arthrobacter keyseri 12B[J]. Journal of Bacteriology,2001,183(12):3689-3703.
[32]XU W J, WAN Q, WANG W F, et al. Biodegradation of dibutyl phthalate by a novel endophytic Bacillus subtilis strain HB-T2 under in-vitro and in-vivo conditions[J].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2022,43(13):1917-1926.
[33]ZHANG S, RENSING C, ZHU Y G. Cyanobacteria-mediated arsenic redox dynamics is regulated by phosphate in aquatic environment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4, 48(2): 994-1000.
[34]XU J J, ZHU X L, ZHANG Q Q, et al. Roles of MnO2on performance, sludge characteristics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in anammox system[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8, 633: 848-856.
[35]TIAN H, LI J, MU Z, et al. Effect of pH on DDT degradation in aqueous solution using bimetallic Ni/Fe nanoparticles[J].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2009, 66(1): 84-89.
(責任編輯:石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