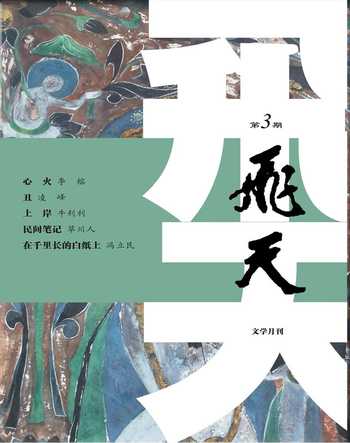冬藏(外一題)
付春生
冬天,大地都凍僵了,僵得只裹著冷。呼呼的風和零落的雪,把萬物吹壓得沒了蹤影。它們都躲了起來,知道這是一次休養生息的機會,是一個修心養性的季節,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和虛無縹緲的念頭,來一次徹底的深睡眠。
勞作了一年,父母怎舍得讓收回家的一切凍傷呢。從知事起,上一輩就告訴他們如何把一粒粒糧食珍藏起來,如何讓他們過冬。就像樹上的一片片葉子,上一茬知道如何傳給下一茬。我肚子里的那些,都是從父母的那片葉子上傳下來的,我從小就懂得這些。
“不要浪費一點點糧食,浪費了就是造孽哩。”“原來冬天不下雪,下的都是白面,老天爺后來發現有人竟用面餅當屁股墊,肺都氣炸了,就下起了雪。”鋪天蓋地的,這都是父母給我講的。一有空兒,他們就給我講。尤其是冬天,活兒很少,工夫多,各種神話故事,紛紛揚揚,讓我珍藏起來。雪沙沙地下著,冰冷冷的天,我看到一會兒是雪,一會兒是面,雪和面交互著,含混不清,在我面前恍恍惚惚。
每一種糧食或蔬菜瓜果,其實都有著不同的耐力。像紅薯,就特別怕冷,一冷就徹底完蛋了。它們的細皮嫩肉經不起風吹浪打,更經不起雪霜襲擊,只有把它們像嬰兒一樣藏起來,才安然無恙。那時的襁褓就是一個很深的地窖,細細的,暗暗的,有一丈多深,鉆進去,像鉆進了安樂窩。
我記得那年和父親打窖,是在一個深秋。天已經很涼了,我們脫掉外衣,讓自己盡量縮小,這樣才能在洞里容下。沙石很硬,硬得只有靠鐵鎬對付。我們拿著短把鎬和短把锨,輪流進入。在狹小空間里,這是能使用的唯一利器,碎石一點點鑿開,深度一點點掘進。這是一次和距離的較量,跟時間的拉鋸。靠磨,靠挺,靠耗,所有的碎石像鋸末一樣落下來,帶著一種遠古的混沌和幽暗,走向清晰和蘇醒。
我和父親交換了下眼神,看了下洞口,比我們高出了很多。該為紅薯鑿窩兒了,這是一次更艱巨的挑戰。因為要調轉走向,是一次更大的挑戰。向下刨還能借助上面的空間,而向側刨更困難,像猛獸困在籠里,根本用不上勁,我們就用釬子挖,以更慢的速度啃噬。
一點也不能含糊,如同螞蟻筑巢。我們不知用了幾天,終于把窩兒鑿得像樣了。那里可真暖和呀!不管外面的風刮得多急,雪下得多大,里面都溫暖如春,紅薯盡情地享受著溫馨和安寧。整個冬天,不管什么時候,我們掏出來,它們都面色紅潤,肌膚舒展,沒有一點被風雪夾擊的滄桑和斑痕,吃起來像剛從地里刨出來一樣。
當然,像紅薯這樣怕冷的瓜果并不多,大部分都有一定的耐凍能力。也許和紅薯天然長在土里有關吧。蘿卜、白菜和大蔥是皮實粗糲的孩子,是經常在泥土上滾打的娃兒。我家院子下面的石窖就是專為它們而設,從表面看,這里只有一個容下人進出的小口,但到了里面,則豁然開朗,四周都是用方方正正的石頭砌成,儼然一個偌大的地下室。這里的溫度自然和紅薯窖沒法比,但比暴露在空氣里要強多了。蔬菜天然是水性的,是被水澆灌長大的,也許潮濕些,更有利于保鮮,所以我每次把蔬菜掏出來,葉子水靈靈的,即使外面爛掉一層,里面還是鮮嫩嫩的,絲毫不影響它的本質。那時我總是下窖,時間久了,似乎聞到了一種與其它地方不一樣的味道。它們是多元的,共享的,包容的,有一個共同達成的協議,集體和解的方案,有爭論,有交鋒,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為人們提供足夠豐富的營養。
我家的玉米、花生、核桃都是喜干的,它們被置放在房頂上——一個用玉米稈編織的圓筒就是它們的家。這里接近陽光,接近風。當它們從地里收回來時,近乎潮濕濕的,這樣的狀態被直接收藏,肯定會發霉,爛掉。所以,要攤在房上不停地曬。曬掉它們的戾氣,盛氣和火氣。曬掉它們的霸氣,傲氣和豪氣。有時,我還會抓把嘗嘗,一邊嘗一邊和它們聊。這陽光真好啊——秋天的陽光!不冷不熱,不暴不烈。對它們是一次全面的滋養,一次徹底地放松和按摩,讓它們疏通經絡,調理血脈,渾身通透。我也被這暖洋洋的陽光曬得不想動彈了。有時,我問它們是否被曬好了,就拿一個耙子在它們身上來回劃拉。聲音和以前大為不同。剛開始,是沉悶的、渾濁的,慢慢地變成了清脆的、歡喜的。嘩嘩嘩,像楸葉上走過的風聲一樣。這是陽光把那些雜質都吃掉了。
我抓起一把,咔咔吃起來。母親說,要吃掉那些干癟的啊,飽滿的還用來當種子呢。這是一次清淺的訓誡,暗示著分級的開始。我們把那些壞的扔掉,怕一塊臭肉壞得滿鍋湯。然后把干癟的和飽滿的分開。那飽滿的是一級品、是明星,藏在圈里,占據一個很好的位置。而那些干癟的,供我們一年食用。我們曬核桃也是分級。重的、飽的,我們會把它們分出來賣掉,那些歪瓜裂棗的,藏起來自己吃。其實一棵樹上,能差到哪兒呢!
憨厚的、渾黃的,外表生著一層硬皮,里面濃甜的是瓜瓤。我家做小米飯時,少不了用這種南瓜瓤做調配。當熬到一定程度,瓤斷斷續續融進飯里,和酥軟軟的米有機結合,成了一種不分你我的狀態。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聯姻,瓜和米都等了太久,為的就是你搭臺我唱戲的合作。干柴烈火,小米的營養在提升,南瓜的甜味在發揮,一鍋色香味俱全的小米飯滾滾而來,呼呼而去。我總是吃不夠。但到了冬天,鮮美的瓜再也等不及了,它的骨子里耐不了嚴寒,更耐不住寂寞,常常一開口,細菌和病毒會趁虛而入,讓它一點點化膿,進入肌理,最終全盤擴散,像人得了癌一樣,無可救藥。
我母親是保存南瓜的高手。入冬的時候,她會把南瓜皮一點點削掉,像木匠一樣,把桑樹皮錛下。接下來,就是一次生動的分割了。不用畫線,不用打稿,母親知道從哪里下刀,從哪里游走,在哪里停頓。一年年操刀,她早胸有成竹了,知道瓜的硬度,瓜的粘度。脾氣秉性,她摸得通通透透。她是一個裁剪師,更是一個設計者,沿著一個螺旋弧線,讓刀回環往復,舒緩婉轉。夕陽下,我看到一圈圈瓜條分割下來,瞬間就變成了一條彎曲的河。母親心靜如水,像個拉胚師傅一樣,隨著手中的感覺,心手合一,雜念全無。她一根根筋,一條條脈,架子上掛得滿滿當當。如果不下雨,幾天就能干。再打好捆,一捆捆裝進箱里。等做飯的時候,剪下一段,在綿長的日子里細水流長。
過去,農家的糧食不夠吃,就想到了用其它食物替代。最充足的當屬紅薯。富含淀粉,蛋白質等成分,是做面粉的好原料。大地多情,能讓一種物質又當瓜,又當糧,這是大地溫暖的關懷!每到初冬,萬木蕭瑟,母親就開始拿這個操刀了。光溜溜的,不似南瓜那么大,用刀切太費工了——綿軟細條只適應于南瓜脫胎,而片片“飛蝶”才是紅薯的化身。讓它蝶變的是一個礤床子,有一個鋒利的利刃,還有一道留有一定寬度的罅隙。紅薯從這里經過,在刀刃上切削,借助著罅隙的束約,厚薄均勻的“蝴蝶”翩翩飛出。這不需要太大技術,只要有耐心,有力量,就能讓更多的紅薯破繭化蝶,紛飛起舞。
那間屋后的枯草上,是“蝴蝶”棲息的地方。它們身子太濕,要靠風的力量烘干。不是一只、兩只,而是千只、萬只。那灰白的翅膀把整個草的絨毯都掩埋了,陽光在上面跳舞,把原本平展展的表面繃得鼓了起來。這是干的象征,是能冬藏的告示,一袋一袋裝起來,再也不會腐爛。
尚留一絲母體的淡淡味道,紅薯面發甜,顏色發黑,雖不像麥子面那樣潔白,味道那樣純正,但也是一種獨特的享受。母親常用來包包子、貼餅子。在那個玉米面和麥子面尚不能糊住整個日子的年代,是紅薯面補充了空缺的部分,讓一年的光景變得不再殘缺。
春天,青黃不接。經過一個冬天的消耗,舊菜吃得差不多了,新菜還沒補上,怎么辦?農人們早有先見之明,在入冬前就做了充分準備。那時,農家除了紅薯多,大概就是水蘿卜多了。有時年景好,雨水足,弄回來的蘿卜像小山一樣。留下來點熬菜吃,剩下的大部分都統統礤成了蘿卜干。
陽氣上升。當大菜窖肚子日益干癟的時候,那些早已做好的儲備就派上了用場。這時,河里的冰塊一一消融。母親的預案開始啟動了,她將一大筐蘿卜干泡在水里。蜷縮、干渴了一個冬天的蘿卜干開始慢慢舒展,荒蕪了一個季節的夢開始復蘇。精神振作起來,面容光鮮起來,完全達到最佳的狀態時撈出,切成條,可以炒著吃。剁成末,可以包餃子吃,和鮮蘿卜是完全不一樣的味道。我想蘿卜片那么好吃,一定是在吸收了陽光的溫度后,在漫長的冬季里,內部微粒發生了不為人知的變化。那是一個奇妙的過程,一個神秘的世界,一切在暗處進行。它們的秩序被打破,然后交融、重建,以另一種方式固定下來。外顯在味道上,是那種筋道的、有彈性的、有嚼頭的口感。
和蘿卜相近的還有一種蔬菜叫蔓菁,比蘿卜個小,顏色有別,有些發紅。小時候,我們常去地里割草,餓了就偷著吃。削了皮,特別爽口。這種菜,很細,自然不能再削了。幾天前我碰到一個剛出身不久的小孩兒,母親非要把她身上的痣用激光點掉,醫生告訴她不能點,小孩的皮膚太嫩,一點就融化了。我想蔓菁也是,小小的個兒切來切去,對它傷害太大,整體晾曬,不失營養,而且很容易曬透。
如果說,紅薯面是白面和玉米面的救援,那么蔓菁就是南瓜條的替身。那時母親感到南瓜條金貴,總舍不得敞開吃,省下來送給城里的親戚,他們也稀罕。我們家做米粥的時候,就放些蔓菁疙瘩。一個冬天,蔓菁早已成了“塑膠”,整個身子緊皺在一起,硬得跟松塔一樣。這種疙瘩要經過長時間的熬煮才能化開,特別費柴。但熬出來的粥非常好吃,有一種水果清爽的味道。農家的日子就是這樣隨性和豐富多彩。
冬天,我們把所有能藏的東西都藏了起來,它讓我們藏神、藏精、藏陽,儲滿能量。像人一樣,大自然也在藏,萬物蕭疏,天空藏起了雷聲,鳴蟬藏起了叫聲,草木藏起了拔節聲。這是秋天落葉發出的指令,不能走得太快太急,走了一段后,要停下來歇一歇,然后重整行囊,再出發。
別輕易毀掉一條路
幾百年前,這里還曾是一片荒地。滿眼崇山峻嶺,峰巒疊嶂,只有狼啊、兔啊、狐啊,在這里出沒。那時根本沒有路,只有樹、石和雜草。風把季節都混在了一起,時光重重疊疊,淹沒了歲月的光鮮與清晰。
也不知過了多少年,我降臨到這里。房屋、水井、磨盤,甫一知事,映入眼簾的就是這樣一番景象。不過,長大后我總是站在這個村莊的制高點上,情不自禁地回望。這兒以前到底是什么樣子?肯定是一片荒蕪,甚至比想象得更加荒蕪。時光把無邊的寂寞風成了化石的模樣,虛妄和空無在吞噬。那時呈現的是一種最原始的狀態,沒什么可擾到這里——只有風和雨,白天和黑夜,來了之后又走,走了之后又來,一年又一年。
自從這里有了人,境況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們開始墾山開荒,修房建屋,鑿井耕田。建房需要樹木,石頭和糧食,于是這里便有了路——長長短短、粗粗細細的路。它們盤根錯節,像經絡一樣把村莊貫通起來。這不是束縛,而是一種解脫和放松。凡能索到的地方,都成了農人的目標,成了他們行腳的所在。像一個個無師自通的設計師,他們能根據各種地形和障礙,找到最安全的位置,找到最短的距離,能躲開山石,避開懸崖,行走在相對平緩的山路上。
一群羊來了,一群牛也來了,在山里,那是我們曾到達的最遠地方。我曾經跟姥爺到這里牧羊,那時羊不知不覺找到了“路”。被野草覆蓋的小徑隱隱約約,模模糊糊,若有若無。我一眼就能辨認出它們。不但我們能,羊也能。它們仿佛為了找到這條路,一路上還撒下一些羊糞蛋蛋,黑黑的、圓圓的,像藥丸一樣。那是一種特殊的氣息,暗示著有物種通過。每次,當我走到很遠的地方,一看到這些羊糞蛋,就感到特別親切和溫暖。說明我已經找到路了,沿著這方向,就能找到家,不會越走越遠,慌亂迷途。
地多的地方,路會寬一些,比偏遠的山上要寬得多,這是倒運的需要。玉米要擔回來,麥子要背回來,紅薯也要推回來。農人不知在這些路上走了多少遍,腳印疊加著腳印,汗水裹挾著汗水。匆匆的腳步把路踩得異常堅實,像農人的手繭一樣。那時我總是跟著父親從山里背糧,不知來來回回走了多少次。我們走一程,歇一程,路兩旁為我們準備了天然的石頭,像古道上的驛站。累了,實在走不動的時候,那石頭就成了我們歇腳的溫床,讓我們把背上的東西放下,坐一會兒,渾身的累就簌簌地往石頭上掉。記得一位農人說,什么時候最舒服?不是住豪華酒店,不是坐高檔轎車,而是背一身重物從遙遠的地方回來,卸下重負的一瞬間。我感到那位農人說得真叫絕,有什么能比卸下一身重負更舒服呢?
行遙遠的路就像唱一首歌。在平緩處,人們容易走,但高亢處,上大坡的時候,就沒有那么容易了,沒兩把刷子是很難唱上去的。那時我們往地里送糞,要上好幾個大陡坡。每到此時,就像音樂人提前醞釀一下,憋足勁,咬緊牙,用很大的力氣才能唱上去。我知道,這是一種最佳選擇。當初農人們修路時,一定是考慮了這些。如果從其它地方繞,肯定要遠得多,不如走這里合算。
有的地方非常狹窄,像變調。不過,農人們適應了這種難度,走得多了,就知道該怎樣轉換角度,讓裝滿糞的筐從這里經過。那時我擔糞時,搖搖晃晃的筐總是在兩塊石頭上碰來碰去。但父親不會,它能讓筐快挨到石頭時,趕快再折回來——這是一種悖論,一個人必須要面對狹窄,但又不能被狹窄卡住。在我家通往地塊的路上,平緩是很少的,大部分有很大難度,必須小心翼翼,用足夠的力氣,才能抵達。
幾百年的村莊,我只是其中一份子。不知有多少人丈量過,有給丈夫送飯的妻子,有給妻子采藥的丈夫,還有上山植樹的老人。他們恍恍惚惚,在路上投下虛虛晃晃的影子。雖然我記不清那些逝者的面容,但每當看到這些路,就會想起他們,尤其想起那些彎著腰,在路上挑糞者的身影。
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雖然挑糞很累,很苦,但這條路是繞不過去的。地不施肥不壯,就像人不吃飯一樣。過去,農人們即使走再遠的路,也要把糞挑到地里。土地的性質決定了糞必須參與,共同完成一項使命。有糞加盟的地是肥碩的、松散的、暄和的,像白面加入了發酵粉一樣微微膨脹。而不施糞的土地會板結、僵硬,沒有活性,即使后來加了化肥也不行。化肥是一種西藥,是短期效應,不像農家肥一樣從根本上加以滋養。可后來,一些村民外出打工后,不愿再走過去老人們的舊路,他們不再把種地當必須,不再把往地里送糞當選擇,而是買些化肥撒一撒,應付了事。地能知風雨、知寒雪,能感受到外界的一切變化。當來自糞里的微生物不再作用時,它們就開始有所察覺,變得萎靡不振。剛開始幾年,長出的莊稼還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因為那些地還透支著以前的老本,往后就不行了,地沒了活力,長出的糧食味道也大不如從前,不如以前那樣醇厚和濃郁,曾經的味道只能鎖在記憶中了。
那時,村莊是那么欣欣向榮。大豆、玉米、麥子、高粱,它們在每個時節都呈現出不同的氣象,讓人心里踏實,精神愉悅。每個人行走在田間都是歡快的,充滿期待的——期待著每一次拔節,開花,結實,期待著豐收季節的趕快到來。
但現在地里的莊稼越來越少了,土地感到的是被冷落和拋棄的絕望,它們發出了大聲疾呼,甚至張著干渴的嘴巴。雜草叢生,曾經的飽滿情緒被打破。
曾經這條山路上,都是去植樹的人。其中就有我的姥爺。他那時是隊長,也是帶頭人。一大片繁茂蔥綠的夢閃耀在他心里。哪兒該種楊樹,哪兒該種柳樹,哪兒該種桃樹,哪兒該種杏樹,他早就心中有數了。想著建房需要樹,吃水果需要樹,賣錢需要樹,防風固沙需要樹,姥爺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他帶領鄉親們,每天在這條路上風雨無阻——這是他認準的一條路,脫幾層皮也要走。最高的山坡上,他們迎著風,栽上槐樹,以防風固沙;再往下,栽上桃樹,招蜂引蝶;再往下,栽上楊樹,布施濃陰。蓬蓬的花椒樹栽在地邊上,不用占地;杏樹栽在山岡上,再貧瘠也無妨;梧桐樹栽在房前屋后,招鳳引凰。反正他們要把每一種樹都栽在合適的位置上,各得其所。那時整個山坡都呈現出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男女老幼齊上陣,把整座山都感動了。袒露心腸,敞開心扉,它們用心中的熱土與農人對話,呼啦啦地從樹窩中涌出來。農人們也把最熱忱的情緒交給泥土,扎進大地。此時,一場驚心動魄的律動就開始了。從暗處生發、吸著風、飲著露、沐著日月、披著星空,一年年,樹很快就從不起眼的小嘍啰,變成了讓人敬仰的大英雄。母親說,上世紀三年大饑荒,可憐的糧食根本不夠吃,是那些黑棗啊、柿子啊、杏皮啊,救了農人的命。我小時候,家里的條件還不是很好,基本靠賣花椒、核桃和柿子的收入。每到周末,夏天跑到山上吃杏子,秋天跑到深溝里吃桃子,再到深秋,爬上大樹摘柿子,吃得不亦樂乎時,母親總是告誡我們,這都是上一輩人鋪的路啊。
那時山上的藥材特別多,遠志、柴胡、地黃等。每到春天,那些藥材在山上不知不覺地發芽,然后隨風生長,在暗處開出耀眼的花兒來。那劇烈的陣痛,像對我們發出了揪心的呼喊,孕育一個冬天,該是降生的時候了。于是,我們沿著那條山路,直奔山上。那時的柴胡可真多啊!像商量好了一樣聚在那里,葉莖直愣愣地沖著天,根須深深地扎著地,精神煥發。看到這么多柴胡,我們幾乎忘了所有的累,揮舞著鎬頭在那里刨著。冥冥中,我們感到這些柴胡好像要急于完成一項使命,它們是那樣慈悲、和藹,非常默契地配合著我們,半點想待下去的愿望都沒有。那幾天,我們每天能刨一大袋子,中午也舍不得回家,吃點干糧,喝點泉水接著刨。晚上回家,我們滿載而歸——肩上、背上、腰里,整個身子都是藥的氣息。
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那時我們不是隱者,是為了生活。我們只知道采藥可以賣錢,可以為家里解憂。后來,我進入中藥鋪的時候,忽然明白自己也不凡起來。那么多藥屜里,說不上就有自己采過的藥在那里待過。史上藥,是誰采的?有多少人采過?神農氏?李時珍?一路走來,沒人知道,只知道他們一定隱在山中,云深不知處。后來我走進城市,幾十年后再回大山,發現那些藥材已沒那么多了,它們仿佛隱了起來,走很遠的路才能找到一棵。這時我才知道珍貴是需要呵護的,當人們不再理會它們的時候,它們也不愿為人做出努力。
被冷落的,還有那些樹上的果子。記得小時候,柿子長得特別多,尤其是深秋的時候,風吹葉落,樹上的柿子微微泛黃,把枝條壓得很低很低,仿佛它不使出最大力氣,就很難將柿子穩穩托起。那時整條山路都是擔柿子的人,兩大筐柿子在他們前后圓弧狀擺動,擔子被壓得顫巍巍的,像承載著柿子的枝條一樣。后來,摘柿人越來越少。他們感到摘柿還不如出去打工,干脆將柿子丟在樹上。大雁南飛,朔風凌厲,柿子等啊等,再也等不到摘柿子的人,它們的臉開始變得干枯,表面不再像以前那樣展脫,慢慢暗了下來。最后黑黢黢的,滿臉皺紋,讓人感到心痛和憐惜。
柿樹不再為人賣命了。一年年徒勞付出,讓它們心灰意冷,柿子開始越結越少,個頭也沒以前那么大,仿佛應付差事一樣。不但柿樹,還有杏樹、核桃樹、黑棗樹,也慢慢委頓下來,再不像以前那樣碩果壓枝,滿山飄香。看到這些,我想不管是大自然,還是人類,如果創造的價值不予充分利用,閑置一旁,以后還怎么能調動起創造者的積極性呢。
不知什么時候人們發現了鐵礦。尤其前些年,外地人借助各種關系,來這里瘋狂挖掘,把土都埋在了那條小路上。原來的那條路只剩下了些斷斷續續的片段,忽隱忽現,再不像以前那樣完整了。為了行走方便,那些不良挖掘者又開了一條新路,雖然很寬,但已不像原來那條路一樣和村莊搭配協調,甚至占了不少耕地,有一種被掠奪和侵襲之感。
現在,雖然國家已禁止了盜礦行為,但那條老路已很難再恢復了。我很懷念那條曾經的古路,懷念祖輩人走過的一條路。
別輕易毀掉一條路。
責任編輯 閻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