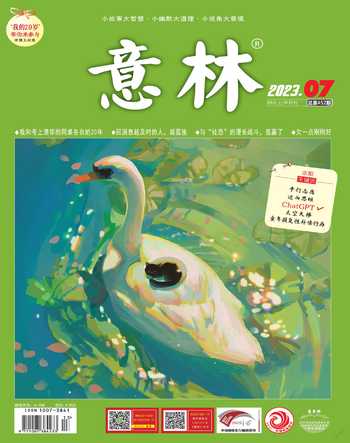復雜世界里,你要擁有過好這一生的四種能力
季羨林
在這復雜世界里,我們應該擁有過好這一生的四種核心能力:得自在、知孤獨、記初心、要豁達。
每個人都爭取一個完滿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內海外,一個百分百完滿的人生是沒有的。所以我說,不完滿才是人生。
在舊社會科舉時代,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要上進,只有科舉一途,你只需讀一讀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盡致地了解到科舉的情況。以周進和范進為代表的那一批舉人進士,其窘態難道還不能讓你膽戰心驚、啼笑皆非嗎?
現在我們運氣好,得生于新社會中。然而那一個考字,宛如如來佛的手掌,你別想逃脫得了。
幼兒園升小學,考;小學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學,考;大學畢業想當碩士,考;碩士想當博士,考。
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我們的人生還談什么完滿呢?
災難并不限于知識分子:人人有一本難念的經。所以我說不完滿才是人生。這是一個平凡的真理,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義,對己對人都有好處。對己,可以不煩不躁;對人,可以互相諒解。這會大大地有利于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
老友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我抬頭看到那大朵的牽牛花和多姿多彩的月季花,她們失去了自己的主人,朵朵都低眉斂目,一臉寂寞相,好像“濺淚”的樣子。
她們似乎認出了我,知道我是她們主人的老友,知道我是她們的認真入迷的欣賞者,知道我是她們的知己。她們在微風中搖曳,仿佛在向我點頭,向我傾訴心中郁積的寂寞。

現在才只是夏末秋初。即使是寂寞吧,牽牛和月季仍然能夠開花的。一旦秋風勁吹,落葉滿山,牽牛和月季還能開下去嗎?再過一些時候,冬天還會降臨人間的。到了那時候,牽牛們和月季們只能被壓在白皚皚的積雪下面的土里,做著春天的夢,連感到寂寞的機會都不會有了。
明年,春天總會重返大地的。春天總還是春天,她能讓萬物復蘇,讓萬物再充滿活力。但是,這小花園里的月季和牽牛會怎樣呢?
月季大概還能靠自己的力量長出芽來,也許還能開出幾朵小花。然而護花的主人已不在人間。誰為她們施肥澆水呢?等待她們的不僅僅是寂寞,而是枯萎和死亡。至于牽牛花,沒有主人播種,恐怕連幼芽也長不出來。她們將永遠被埋在地里了。
我一想到這里,就不禁悲從中來。眼前包圍著月季和牽牛的寂寞,也包圍了我。我不想再看到春天,我不想看到春天來時行將枯萎的月季,我不想看到連幼芽都冒不出來的牽牛。
我虔心默禱上蒼,讓這一塊小小的地方永遠保留夏末秋初的景象,就像現在這樣。
在這一條十分漫長的路上,我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路旁有深山大澤,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風;有山重水復,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絕處逢生。
我面前還有多少路呢?我說不出,也沒有仔細想過。馮友蘭先生說:“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歲,“茶”是一百零八歲。我沒有這樣的雄心壯志,我是“相期以米”。這算不算是立大志呢?我是沒有大志的人,我覺得這已經算是大志了。
陶淵明的一首詩,我很欣賞: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我現在就是抱著這種精神,昂然走上前去。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做一些對別人有益的事,決不想成為行尸走肉。我知道,未來的路也不會比過去的更筆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懼。我眼前還閃動著野百合和野薔薇的影子。
幼時讀唐詩,讀了“西塞山前白鷺飛”“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曾向往白鷺上青天的境界,只是沒有親眼看見過。一直到1951年訪問印度,曾在從加爾各答乘車到國際大學的路上,在一片濃綠的樹木和荷塘上面的天空中,才第一次看到白鷺上青天的情景,顧而樂之。
第二次見到白鷺,是在前幾年游廣東佛山的時候。在一片大湖的頗為遙遠的對岸上,綠樹成林,樹上都開著白色的大花朵。最初我真以為是花。然而不久卻發現,有的花朵竟然飛動起來,才知道不是花朵,而是白鳥。
我又顧而樂之。其實就在我入醫院前不久,我曾瞥見一只白鳥從遠處飛來,一頭扎進荷葉叢中,不知道在里面鼓搗了些什么,過了許久,又從另一個地方飛出荷葉叢,直上青天,轉瞬就消逝得無影無蹤了。我難道能不顧而樂之嗎?
現在我仍然枯坐在臨窗的書桌旁邊,時間是回家的第二天早上。我的身子確實沒有挪窩兒,但是思想活躍異常。我想到過去,想到眼前,又想到未來,甚至神馳萬里,想到了印度。
時序雖已是深秋,但是我的心中仍是春意盎然。我眼前所看到的,腦海里所想到的東西,無一不籠罩上一團玫瑰般的嫣紅,無一不閃出耀眼的光芒。
記得小時候常見到貼在大門上的一副對聯:“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現在朗潤園中的萬物,鳥獸蟲魚,花草樹木,無不自得其樂。連這里的天都似乎特別藍,水都似乎特別清。眼睛所到之處,無不令我心曠神怡;思想所到之處,無不令我逸興遄飛。
我真覺得,大自然特別可愛,生命特別可愛,人類特別可愛,一切有生無生之物特別可愛,祖國特別可愛,宇宙萬物無有不可愛者。歡喜充滿大千世界。
現在我十分清醒地意識到,我是帶著撿回來的新生回家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