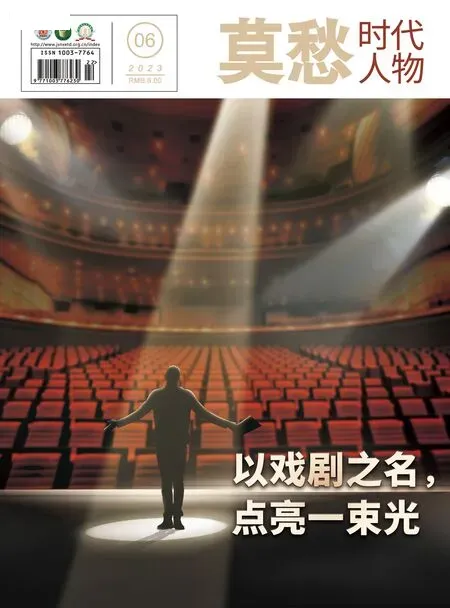花生原來不長在樹上
文仇士鵬
20 歲就加入中國作協的陳偉軍,一直有顆赤子之心。他出身貧寒,撿過豬糞、割過豬草、播種插秧、割稻曬谷,這些刻著鮮明鄉村印記的經歷既讓他保持了勤勉、質樸與節儉,也成了他筆下鮮活生動的寫作素材。他新近出版的兒童文學小說《少年奔跑在田間》便由此脫胎,如他在序言中所說:“當年的少年還在,少年與村莊的血脈依舊流淌。”
小說的情節并不復雜,顧曉蕓畢業后想要回到農村,一家人都不同意,其中就有主人公顧小森。從不想讓姐姐留下,到主動把姐姐留在農村,顧小森的想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標志著他從一個只知道學習的孩子,變成了一個懂事的小大人。顧小森的成長與蛻變便是小說的主線。
讓我驚喜的是,作者巧妙地找到了一個小切口——花生是埋在地里的。這是一個常識,但包括顧小森在內的很多人卻并不知道,這引起了他的興趣。他第一次獨自回鄉,是為了勸回姐姐,也是為了看看花生埋在地里的樣子。
縱觀整部小說,這句話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對于顧小森而言,他原以為自己像是長在樹上的花生,每學期評上三好學生就是生活的全部。而在農村,他依次完成姐姐布置的五個任務后,一步步地擺脫了“城里人”的標簽,完全融入農村的生態體系中。他成了埋在地里的花生,在鄉村的文化滋潤和村民的人性照耀下,他更全面地成長,除了學習之外,一無是處的空白都被填補、豐富。
對于以姐姐為代表的返鄉大學生而言,花生是他們建設家鄉、奉獻青春的象征。在小說中,呈現出一種輪回。奶奶在當知青時,從城市里帶著知識和技能去往農村,把貧瘠與荒蕪開墾成熱土;父親從農村里走出來,把生活的圓點挪到城市里;姐姐又從城市回到農村,和同學一起放棄舒適的生活,投身艱苦的環境中,開民宿,借助新時代的網絡技術等幫村民們的土特產找銷路,造福鄉里鄉親,讓村莊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花生長在樹上這種錯誤的認知像是一條裂痕,橫亙在城鄉文明之間。城市里的人過著不沾土腥味的生活,所接觸到的都是幾次加工后的農產品,見不到它們存在于自然中的樣子,也不愿意去遍布禽獸糞便的農村道路上行走,對農村避而遠之。漸漸地,他們的心中沒有了田野的鳥鳴與長風,眼中少了天真爛漫的光亮。這不僅讓童年缺少了五彩斑斕的一部分,也讓他們無法對鄉土形成深厚的感情。而這對于想要發展、想要擺脫貧困與落后,急需人才的農村無疑是致命的。
因此,這部以兒童為讀者的小說極具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只要心中有熱愛,不管是城市還是鄉村,都是青春的舞臺。”在孩子們最需要引導的時候,幫他們培養正確的人生觀、樹立遠大的理想,當他們長大成才后,或許就會有人愿意去偏遠地區支教,扎根基層,奔走在田間地頭,致力于鄉村振興。那注定是文學價值最好的實現。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小說是以五年級學生顧小森的視角展開,讓孩子們更能感同身受。此外,行文中融入大量富有童趣的內容,比如作者把吵鬧的公交車比作蜜蜂王朝,把滿滿當當的車子比作夾滿食材的超級漢堡,這些無疑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
顧小森最終獲得啟示:“人,不能只想著自己,還應該將目光放在我們身邊的一切。”現在,他知道了花生原來不長在樹上,而我們呢,會讓花生埋在地里,還是掛在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