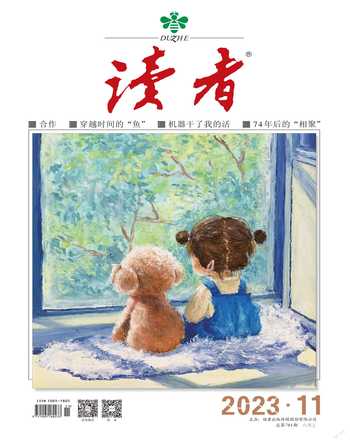穿越時間的 “魚”
李斐然

張彌曼在修理化石
世界的深夜
張彌曼覺得2018年太吵了。
這一年,熱鬧和光環一起涌到了這位82歲的古生物學家面前。3月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邀請她到法國參加典禮,授予她“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這一獎項每年只頒給全球5位女性。幾個月后,何梁何利基金為表彰她對科學的貢獻,頒給她最高獎“科學與技術成就獎”。人們管她叫“先生”,稱呼她“大家”。
人們像發現恐龍化石一樣,突然察覺到一位偉大的科學家的存在,發現了她在古生物學領域的杰出成就。盡管在過去60年中,她一直就在北京二環邊最熱鬧的一條街旁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人類研究所(簡稱“古脊椎所”),日復一日地默默工作。
她幾乎是全世界最了解古魚的中國專家。大部分古生物學家所研究的時間范疇在幾百萬年內,但張彌曼的研究范疇縱貫數億年,且在每個領域都有扎實嚴謹的發現,這在世界范圍內都是極為罕見的。
迄今為止,世界上已有許多古生物以她的名字命名,它們包括一種現已滅絕的古魚,一種在中國熱河發現的恐龍,還有已知最古老的一種今鳥型類的鳥……
在古脊椎所,時間以另一種尺度計算,不是去考慮一年365天,而是去思考地球已有的46億年。如果把這個時間跨度壓縮成人類紀年的一年,在這一年里,直到3月中旬,地球上才出現最早的生命跡象;到12月初,地球上才出現大規模沼澤地與大片森林;恐龍在12月中旬稱霸地球,可是好景不長,它們于12月26日滅亡。直到12月31日接近午夜時分,人類才登場。
對張彌曼來說,讓她畢生著迷的正是這個萬物演化的世界,這個既熱鬧又孤單的學科。在她面對化石的那一刻,房間里仿佛重現許多遙遠時代的生命。
第一條魚
在野外考察的時候,張彌曼很難讓人看出是一位院士。她永遠都自己拎包,自己搬石頭,“她會不計成本地去做一些外人看來很小的事情”。很多項目從頭至尾只有她一個人,每一步都是自己做,直到現在,很多標本還是她親自修復的,這會花費很多時間,但她不放心交給別人。
張彌曼研究的都是遙遠的歷史,沒有人親歷過現場,人們只能從偶然鎖在化石里的痕跡推測當時的狀況,所以,一切判斷都要特別小心——你可能是幾億年來,第一個認識這種生物的人,也可能會成為幾億年來,第一個毀了它的人。
以最謹慎的推測,在地球數十億年的演進中,魚類可能開啟了關鍵的一幕:脊椎動物誕生后的近1億年時間里,它們都只能生活在水里。直到3.7億年前,一群勇敢的魚終于決定離開熟悉的海洋,爬上陸地,開始新的生活。它們從此改名為“四足動物”,而其中一個遙遠分支就成為正在閱讀這段話的人類。
在古生物學家眼中,人類就是改版后的魚。直到現在,我們身上還保留著來自遙遠祖先的痕跡——我們從魚類祖先那里繼承了綿長曲折的喉部神經路徑,胎兒出生之前還有過鰓裂消失的階段,背部和腕關節的主要骨骼都是從水生生物進化而來的。所以,我們走路久了背疼,長時間打字手腕酸痛都情有可原,因為我們的魚類祖先平常可不干這些事情。
那么,第一條魚如何爬上陸地?離開完全熟悉的水的世界,魚類登陸后發生了什么?它們要如何呼吸、如何支撐自己的身體、如何活下來?從它們身上反推,當時陸地是什么樣子的?它們在演化中所經歷的起起落落,會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這些就是張彌曼所感興趣的終極命題。為了給這些命題一個盡可能準確的答案,張彌曼付出了太多的時間。剛開始工作的時候,為了搞明白在浙江發現的中生代魚化石的歸屬細節,她一到周末就帶著化石去挨個兒拜訪當時著名的魚類專家,向他們求教。
那時候寫論文全靠手寫,要一個字一個字地謄寫在方格稿紙上。論文動輒上萬字,大部分人的稿子會有些許修改,只有張彌曼的稿子,哪怕交來的只是底稿,也從頭到尾工工整整,即使這一頁最后一行有一個錯字,她也會把這一頁從頭再抄一遍。
張彌曼的學生說,在她身上,既有文氣,又有“匪氣”。她很謙遜,是大家閨秀,可是膽子也很大,敢跟人叫板。《自然》雜志對她的特寫里面,同行轉述了一則往事。那時候她作為學生代表,帶隊去哈薩克斯坦的危險區域考察,當時旅館拒絕接待這些中國人,她便拍著桌子,毫不退縮地跟前臺理論,要求入住。最后,她為團隊爭取到了應得的房間。
她上大學的時候,這門學科被視作“祖國的眼睛”。她被選派留蘇,通過魚類化石判斷地層,希望為國找油找礦。可等她學成回國,這個學科已經成了“祖國的花瓶”。
這成為考驗那一代科學家的一個核心命題——活在光圈之外的科學家的樂趣是什么?
事實證明,最迷人的還是那些原始命題——第一條魚的故事。“這門學科帶來的最大樂趣,無非就是由不知到知。”就這樣,她還在一次次奔赴野外,用地質錘敲擊著大地,尋找鎖在石頭里的魚,努力推動科學的進步。

張彌曼介紹她的研究工作
反對
1980年,張彌曼再次到瑞典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訪學。那時候,瑞典學派還處于極盛狀態,她的老師們都是瑞典學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早期脊椎動物研究的絕對權威。
特別是導師雅爾維克,正是因為他所發表的專著,“四足動物起源于總鰭魚類”這一論點才成了教科書上的公認觀點。他認為,3.5億年前,總鰭魚類是陸地上最高等的動物,它們長著內鼻孔,可以不用鰓就直接呼吸空氣,這是魚類從海洋登陸的一大先決條件,所以,很可能就是這種魚第一個從水中爬上陸地。
1982年3月31日,張彌曼博士論文答辯。這一天來旁聽的人比平時都要多,當時有很多著名的古魚類學家帶著自己的標本,從其他國家趕去斯德哥爾摩,見張彌曼。她的論文題目是《中國西南部云南省早泥盆世總鰭魚類楊氏魚的頭顱》,在論文中,她明確提出,540多張連續磨片的結果顯示,楊氏魚沒有內鼻孔。
這是古生物學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反對。魚類登陸呼吸需要內鼻孔,但屬于總鰭魚類的楊氏魚沒有內鼻孔,這直接動搖了總鰭魚類是陸地四足動物起源的傳統判定,改變了此后的教科書。張彌曼取得了博士學位,也為中國科學家贏得了世界聲譽。
30多年后,年輕的古生物學家朱敏和盧靜接手了張彌曼當年的研究。現在可以依靠CT掃描和同步輻射等新技術,在較短時間內精確復原古魚化石的腦顱。為了對照研究,盧靜用CT掃描楊氏魚化石,并將計算機重建出的模型和張彌曼30多年前手工做出來的模型進行了對比。令人驚愕的是,哪怕是最精細的地方,差別都微乎其微。
不僅如此,張彌曼所做的連續磨片,清晰細膩地復原出楊氏魚的腦顱、腦腔、腦腔血管,甚至神經通道的極其微小的細節,這是連目前最先進的CT方法和數字還原技術也無法獲得的準確信息,是再精密的機器也無法實現的極致還原。哪怕已經過去30多年,只要看一眼就能明白,為什么連絕對權威也不得不服氣。
21世紀的古生物學家
數十年里,張彌曼影響了許多“人類又進一步”的發現。在研究古生代魚類有所突破后,她又對中國中生代魚類、青藏高原新生代魚化石展開研究。在她的推動下,以30多歲的年輕人為主體的研究團隊開始研究遼西熱河生物群,使中國成為國際古生物研究的焦點。
2005年秋天,北美古脊椎動物學年會組織了“榮譽學術研討會”。在研討會上,曾任耶魯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費城科學院院長的湯姆森教授贊嘆:“40年前,一個來自中國的年輕女學者張彌曼,將云南泥盆紀魚化石標本帶到瑞典自然歷史博物館,給傳統的四足類起源理論鬧了個底朝天!”
張彌曼過70歲生日的時候,她的學生朱敏將一種新發現的魚獻給自己的導師。他給它取名為“晨曉彌曼魚”。他說,這條魚的科學地位很像他的這位老師。它是最原始的輻鰭魚,在演化中的地位很重要,位于進化樹的關鍵分叉點上,影響了后來無數的魚類。
事實上,張彌曼所帶來的關鍵節點不止一個。20世紀80年代,她任古脊椎所所長。張彌曼的同事苗德歲說,她是一個敢做敢當的領導。那時她促成的中加聯合恐龍考察,是當時國內罕見的大型國際科技合作項目。那么大的項目就是張彌曼在飛機上談成的。限于當年的通信條件,她既沒法向任何人請示,也沒有時間層層打報告申請,當場就同意了。那次科考發現了大量恐龍珍品標本,也培養了一批年輕的研究人員,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古脊椎動物學研究的發展。
2018年夏天,從不接受任何掛職頭銜的她,答應擔任化石點附近一所學校的榮譽主任,借當年的熱鬧帶來的一點影響,保護一段4億年前的歷史。她還不想停下來,便給自己起了一個筆名“尚能西”,因為她喜歡這個古老的寓意:“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
在給學生的贈書上,她題上了這樣的話:“自由比權利重要,知識比金錢永恒,平凡比盛名可貴,執著比聰明難得。共勉。彌曼。”
夜晚到來的時候,世界再度歸于安靜,房間里又只剩下她一個人了。不過,等化石里的秘密復活,熱鬧便又會回來,就像她的學生朱敏所記下的那樣,“深夜,她在顯微鏡下靜靜地觀察云南的古魚化石,4億年的時空穿梭,肉鰭魚在中國南方古海洋中暢游,同樣閃耀著逼人的美麗藍光,但不是在深海避難所中,而是在濱海,在海灣,因為它們是當時地球上最高等的動物”。張彌曼終其一生追尋的,就是這項遙望過去的迷人事業。
(蟲兒飛摘自東方出版社《她們和她們》一書,本刊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