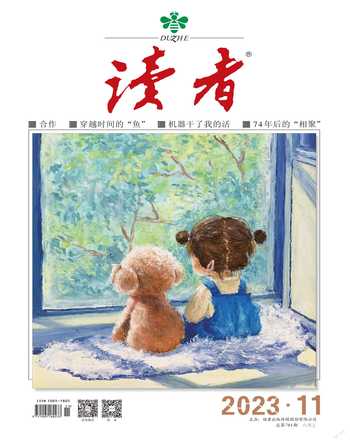世事如云煙,如何留得
劉荒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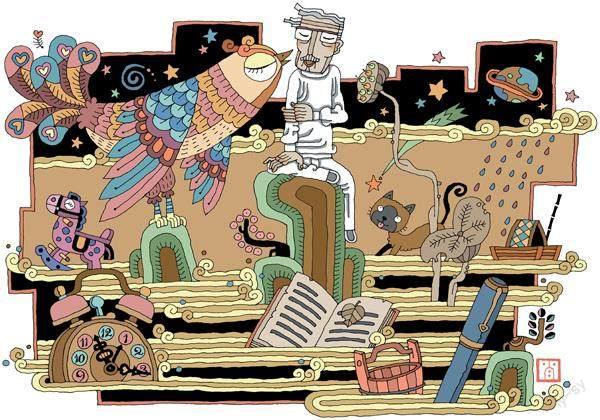
“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是李商隱的不朽詩句。聽雨有多種途徑:欲求響亮,宜鐵皮屋頂;欲求龐大,宜芭蕉葉;欲求細膩,宜堆積的落葉;欲求凄冷,自然要效蔣捷,困于江闊云低的客舟,西風里夾一聲雁唳。不過,沒有什么比得上繁盛過、綽約過的枯荷,更能在霜飛階前的秋陰黃昏,曲盡雨聲的意韻。
“留得”,無疑是關鍵詞。怎樣“留”,大有講究。塘中枯荷可以靠人的手下留情,也可以假手于風雨及節令;至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人所能做的,只是留住植被。
世事如云煙過眼,如何“留得”?且檢視一生中最要緊的幾樁事。
留得初戀嗎?最后閱讀火熱的情書的,是灶膛里的火苗。留得婚禮嗎?如果那個年代的照相機和菲林膠片的質量上乘,鏡框和家庭照相冊里還能僥幸存下婚紗照。如果當年的夾克還在,也許還能留得襁褓中兒女的奶香;如果火車站的月臺還在,也許還能留得父親從即將開行的港九直通車上跳下的姿態;如果人行道旁邊玫瑰叢下的泥土還在,也許還能留得陪兒女上學的影子;如果電腦硬盤有人的記性,也許留得我靈感驟至時敲鍵盤的吟哦。田塍旁的流水,留得我還鄉路上對著祖屋歡呼的倒影嗎?波羅的海的碧波,留得我與老友在郵輪上憑欄拍落日的動作嗎?家中起居室的地毯,留得外孫女騎在我肩膀上的笑聲嗎?
“留得”憑借的是記憶,鋼筆、鍵盤、鏡頭,不過是記憶的外化、固定和延長。
然而,記憶不是絕對聽話的奴仆,它的功能未必限于留聲機式、錄像機式、云端硬盤式原原本本的回放,它還會加入自作主張的篩選和修改。記憶與遺忘的合謀,使“留得”從單純的紀實變為現代主義的魔幻。進一步說,連當時馬上記下的日記,也可能部分地失去原汁原味。我還沒提到,多少人改寫過日記,將既成事實涂改得完全迎合他人的口味。
如此推論,“留得”莫非是一廂情愿?
是的,只有一次的人生,指向了無從復制。船過水無痕,每一條波紋都不同于另一條,漸次消遁,而后浪隨之。無論是刻意所為,還是自然發生,所有經歷都在記憶里分門別類地一一排列。當你反芻往事時,它們便被挑出。記憶也許聽話,哪壺開了提哪壺。你悲嘆人生易老,它饗以落花隨水流逝;你贊美愛情常新,它提交兩只緊緊牽著的長滿老年斑的手;你堅信人類的前途,它畫出滿天朝霞。記憶也有不聽話的時候,當你為“不負此生”而自鳴得意時,它便讓你看當年偷偷寫下的后悔事。
午夜夢回,你驚訝地悟出,這世間有無數的“留得”并不因你的意志而存滅,天地良心在悄悄地、冷峻地做證,誰也瞞不過,抹殺不了。“每個人的記憶都是自己的私人文學。”英國作家赫克斯科如是說。
96歲那年,王鼎鈞先生在《不一樣的雨聲》中說:“最后的呼吁,只有一個地球,留得地球聽雨聲。”
(葉輕舟摘自《解放日報》2023年4月6日,肖文津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