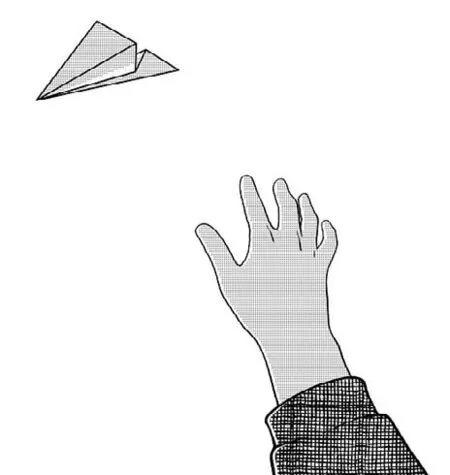只是吼聲
◎曉 月
1
這是個陌生的房間,和緩的鋼琴聲伴隨著山間溪水流淌,淡綠色的墻紙讓安梓軒的心安靜了下來。
“你好,小安。”
安梓軒睜大眼睛,看著面前的單霞阿姨。單霞阿姨是一位心理咨詢師,四十歲上下,剪著齊耳短發(fā),顯得很干練。盡管阿姨的聲音很溫柔,安梓軒還是身體僵硬,感到驚恐。阿姨的手輕輕劃過他的肩膀,笑著問:“這音樂讓你想到了什么顏色?什么樣的畫面?有沒有小動物?它們在做什么?”
安梓軒的大腦都是僵硬的,什么?顏色?音樂和顏色有什么關(guān)系?他茫然地盯著自己的腳。
“不用回答我。你聽這溪流,流過光滑的大石頭,與小黑魚擦肩而過,問候了不遠處的橘色小蘑菇。你還看見了什么?告訴自己,問問自己,美嗎?”
單霞阿姨的聲音把安梓軒帶進了山林,他們仿佛一起坐在一塊大石頭上,周圍氤氳的霧氣讓樹林更顯灰暗,溪流如一條發(fā)光的透明絲帶,沒有鮮明的顏色,溪水聲和鋼琴聲讓周圍顯得更安靜了。阿姨把一張大紙和一盒水彩筆放在他面前,輕聲說:“想到什么,可以把它們畫出來。”
安梓軒記得,那天從單霞阿姨的心靈工作室離開時,天已經(jīng)黑了,他沒想到自己竟在那兒待了三個小時。在這三個小時里,他一度忘了所有的吼叫,忘了自己是個讓人很不滿意的小孩,也忘了從前的世界。
那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你到哪兒去了?電話也不接,你想干什么?”空無一人的房間里,氣勢洶洶的吼聲如連珠炮般激烈掃射。
“還不滾回來?等我回家好好收拾你。”慘白的墻無辜地承受著這狂暴聲。如果墻能呼吸,它一定已經(jīng)不自覺地屏住了呼吸。
無人回應(yīng)。
房間西北角,從屋頂垂掛下的黑色監(jiān)控探頭顯得有些滑稽。黑色探頭是沒有靈魂的,它在替人發(fā)聲,它是八點三公里外那個人的傳聲筒而已。
“你還不回到書桌?你還沒玩夠嗎?已經(jīng)三十二分鐘了。你一走開我就知道,三十二分鐘了,我都給你記著,三十二分,一分鐘都沒少算,也沒多算。”監(jiān)控探頭那端的人把“三十二分鐘”重復(fù)了三遍,之后他說,“我可沒那么好忽悠,你是不是又想把半小時說成五分鐘?再不出來,你就等著瞧吧。”
安梓軒的身子一顫,小竊喜瞬間消失,心頭的烏云也蔓延到了臉上。
剛才他上衛(wèi)生間去了,當準備回到房間時,卻想起了那個可憎的探頭,他不由自主停下腳步,坐在了房門外的地板上。只是發(fā)呆,想著探頭對著無人的房間嘶吼的可笑,竟有點兒幽幽的快感。
他能瞧什么,瞧見自己被揍嗎?一個人被打的時候,怎么可能成為自己的幸災(zāi)樂禍的旁觀者?瞧?沒什么可瞧的。安梓軒捂著肚子,弓著身子,回到書桌前。
他望向監(jiān)控探頭,可憐巴巴地申辯:“我拉肚子了,剛才我肚子好痛。我沒去玩,一直在衛(wèi)生間拉肚子,真的。”
“哼,又想騙我?別啰唆了,老老實實開始寫作文吧。快點兒,別再沒事找事,拖拖拉拉的。”
“我肚子真的很痛。”此刻,安梓軒的肚子真的又痛了,他臉色煞白,有氣無力地說。
“還在騙我,你作文寫幾個字了?”爸爸完全不相信兒子的話,心里裝著的全是兒子的功課,他下意識地把兒子身體想象成了金剛不壞之身。
“我已經(jīng)寫了兩段。”安梓軒虛弱地回答。
“大點兒聲,別裝了!快點兒寫,等我中午回來檢查。如果寫完了,獎勵你玩半個小時電腦。要是沒寫完,估計你是皮癢了。”爸爸從鼻子里呼出一口氣,“哼,有了游戲,你肚子不痛了吧?”
“還是有點兒痛。我再休息一會兒就寫。”安梓軒把腦袋擱在書桌上。
爸爸的心突然抽動了一下,是不是真的生病?
不過這念頭一閃而過。他暗自思忖,這段時間憑空而來的“疫情假”,安梓軒都在家里,沒吃壞東西,沒受涼,怎么可能肚子疼?想到這里,他便繼續(xù)沖著監(jiān)控設(shè)備喊道:“你都休息半個多小時了,還不夠嗎?”
“再休息一小會兒,你下班前我肯定能寫完。”
一個聲音打破了安梓軒父子的時空:“安哥,我辦公室的電腦死機了,重啟也不行,你來幫忙看看?”安梓軒聽出那是爸爸的同事文文阿姨的聲音。
“好好,你先回去,我忙完就去你的辦公室。”安梓軒爸爸不耐煩地向來人揮了揮手。
如果沒有人來打斷安梓軒父子的對話,他們可以反反復(fù)復(fù)繞上幾十甚至上百遍。
安梓軒家的常態(tài)是,爸爸為兒子功課等事喋喋不休地撒氣,兒子向父親可憐地求饒,媽媽終于忍不住時過來勸勸,最后兒子順從了,以兒子心不甘情不愿地應(yīng)付完功課告終。之后,生活才重歸平靜。
安梓軒家平靜的時光并不多。
2
文文阿姨的皮鞋聲遠了。
“爸爸,你去忙吧,你下班時一定能看到我寫好的作文。”安梓軒感覺到肚子里的抽動,疼痛加劇,又站了起來,彎著腰說,“我要去衛(wèi)生間了,很快就回來。”
“臭小子,花樣這么多。快去快回,我做完事情,還會過來看你寫作文的。”爸爸關(guān)掉了手機的監(jiān)視界面。
躲進衛(wèi)生間,坐在馬桶上,安梓軒肚子里的疼痛漸漸被排出,他的心又一次被安撫了。這一刻,他大腦一片空白,忘了爸爸,忘了作業(yè),也忘了自己。
這兩年,安梓軒似乎學(xué)會了表演,肚子疼、腳疼、頭暈、反胃……他對這些詞信手拈來,仿佛病痛是聽話的智能機器人,可以隨叫隨到。可演著演著,這些病痛就成真了,先是有點兒疼,后來越來越疼……麻煩也隨之而來了,病痛隨叫隨到,卻不能揮之即去。
安梓軒媽媽是牙科醫(yī)生,不借助驗血等檢測手段,她很難確定兒子身體的真實狀況。對于兒子說身體疼痛,她的半信半疑寫在眼神里。帶兒子上醫(yī)院檢查,沒查出身體器官異常。
安梓軒爸爸放心了。于是,每次安梓軒說疼,他就成了人工測謊儀,測試的結(jié)果永遠都只有一個:“安梓軒,你在撒謊。”安梓軒爸爸不信自己不愛聽的語言。
偏偏那么巧,安梓軒的話大多是爸爸不愛聽的。安梓軒說同學(xué)的事,爸爸沒興趣聽;說課上喜歡的知識,爸爸沒耐心聽;說成績的事,爸爸只在乎數(shù)字,卻又極不滿意那些數(shù)字。
安梓軒媽媽太忙了,除了在醫(yī)院上班,她還多點執(zhí)業(yè)。多點執(zhí)業(yè)的意思就是,她從醫(yī)院下班后,又輪流到兩個診所加班,適當增加個人收入。在安梓軒家,媽媽待在家里的時間遠遠少于爸爸的,媽媽的收入也遠遠高于爸爸。
爸爸常說,媽媽很辛苦,媽媽的每一分鐘都能變成金子,所以,孩子們都要乖乖懂事,不要讓媽媽再多操心家里的小事兒。
“我都修完電腦了,你還躲在衛(wèi)生間嗎?趕快出來,你究竟要騙我到什么時候?”爸爸的聲音再次清晰地傳到耳畔,安梓軒打了個激靈,肚子又疼了起來,似乎有千萬只蠕蟲在他的肚子里恣意狂歡。當疼痛被無視,實話被說成謊言,肚子就會更痛了。
作為報社的電腦設(shè)備技術(shù)員,安梓軒爸爸上班很閑。疫情期間的停課,讓他心神不寧,孩子交給老師和把孩子放在家里,心里的感受是大不同的。兒子停課在家自學(xué)的時候,他不得不時時盯著監(jiān)控探頭看。他到單位上班,人在曹營心在家。
“我真的很痛。”安梓軒再次回到房間時,弓著身子直奔床鋪,屁股沾床就仰面躺下緊閉雙眼,無力地呼出長長的一口氣。
“你還裝樣?”爸爸生氣地吼道,“剛才你不是答應(yīng)我,上完廁所就寫作文嗎?”
“別那么兇對孩子說話,安梓軒大了,你得尊重孩子,耐心一點兒,有話好好說。”同事文文阿姨的音量不大,安梓軒還是聽到了。以前,安梓軒常跟爸爸去單位,遇到爸爸訓(xùn)斥他時,文文阿姨也會及時出現(xiàn),救下安梓軒,帶安梓軒去她的辦公室寫作業(yè)。
“你不了解他,這孩子天生不自覺。你忙你的去吧。”安梓軒爸爸不僅聽不進文文阿姨的話,還下了逐客令。他把文文推出去后,反鎖了辦公室的門。
“怎樣呀?還裝不?”
安梓軒沒有半點兒力氣回應(yīng)了,用手捂著肚子,蜷縮著身體,
“喊多了狼來了,當狼真的來了,就沒人會救你。”安梓軒爸爸繼續(xù)吼道。
安梓軒已經(jīng)昏睡過去了。
看到孩子一動不動沒了任何動靜,安梓軒爸爸慌了。
他第一時間給安梓軒媽媽打了電話:“孩子好像暈倒了,我馬上從單位回去,送他去醫(yī)院。”
“是不是睡著了?”安梓軒媽媽聲音顫抖,不安地問。
“不是,我們好好說著話,他突然就沒了反應(yīng)。我先回去,你也趕回來吧。”安梓軒爸爸掛了電話,火急火燎地往家里趕。
安梓軒爸媽幾乎同時到家。他們先是使勁搖晃安梓軒的身體,見喚不醒他后,爸爸在媽媽的幫助下背上兒子,把他送進了醫(yī)院。
3
一番檢查中,安梓軒漸漸醒過來了。“我,怎么了?”見到急切湊到跟前的爸媽,安梓軒仿佛在夢里。
“你生病了,醫(yī)生做了初步檢查,沒什么大問題,很快就會好的。”媽媽拉著安梓軒的手說。
“我怎么病了?”安梓軒有氣無力地問。
“誰知道呢?你這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病了?”爸爸沒好氣地說。
“對不起。”安梓軒說著,眼淚流了出來。
“是媽媽對不起你,平時對你關(guān)心太少了。寶貝,你要快快好起來哦。”媽媽抹去眼角的淚水,內(nèi)心充滿愧疚,后悔自己陪伴兒子太少了。
“你回去吧,我在這里陪兒子,醫(yī)生說檢查兩天,如果沒事,就可以出院了。”爸爸像個盡心盡責(zé)的機器人,催促太太回家。
媽媽在安梓軒床邊坐下,語氣堅定地說:“不,我來陪兒子,你回家吧。”
初步檢查后,醫(yī)生暫時沒發(fā)現(xiàn)什么指標異常,說再持續(xù)觀察。
安梓軒還沒醒來前,爸爸陪在病房,媽媽去了醫(yī)生辦公室。
聊的時候,醫(yī)生提到,這些年因為心理原因引發(fā)身體疾病的情況很常見,“軀體化障礙”這個詞,一下子刻到了安梓軒媽媽的心頭。醫(yī)生絮絮叨叨地講起處在家庭高壓陰影下的孩子們生病的故事,安梓軒媽媽的心惴惴不安。
安梓軒媽媽回到病房,悄聲對爸爸說道:“醫(yī)生說,孩子可能是心病。”
“瞎說,沒病裝病。”安梓軒爸爸低聲嚷道。
安梓軒媽媽皺起了眉頭:“打住!我是醫(yī)生,心病也是病,這些年得抑郁癥的孩子可是不少。”
“吃得好,穿得好,只要他好好學(xué)習(xí)就行。這病他會得嗎?”爸爸嘟囔著。
“如果不是身體上的問題,就是心理上的問題。”安梓軒媽媽神情凝重地說,“今晚,我想和孩子待在一起,你讓我好好想想。”
“可是……”
“別可是了,這也是當媽媽的應(yīng)該做的。你快回去,好好地睡一覺,我可能隨時需要你。”安梓軒媽媽勉強擠出一絲笑容。
第一次獨自待在家里,安梓軒爸爸的心里空落落的。
他走進兒子的房間,坐在他的床沿上,視線正好是書桌那兒。
一幅畫面出現(xiàn)在他眼前,書桌前坐著兒子,旁邊站著的是他。他依稀看見自己拍打兒子的腦袋喊:“又走神了,半天也沒寫兩行字。”兒子委屈地流下眼淚,卻讓他更加惱火,“哭哭啼啼的,哪像男孩子?!讓你專心寫作業(yè),有那么難嗎?”“我寫,我馬上就寫。”孩子邊抽泣邊拿起筆,眼淚滴落在筆上,也滴落在作業(yè)紙上。想到這些畫面,安梓軒爸爸眉頭緊鎖。
但是,想到自己上班的那點兒微薄的工資,他更堅定了自己的想法。今天不好好督促安梓軒學(xué)習(xí),未來他可能連我都不如。這時代競爭壓力越來越大,沒有身體的疾病,就是意志不堅定,得訓(xùn)練。他暗自跟自己說:“寧可現(xiàn)在被孩子恨,也還是不能放松對他的要求。”
4
爸爸離開病房后,安梓軒舒了口氣。
媽媽摸摸他的額頭問:“哪里還難受嗎?醫(yī)生說,明天還要做些檢查。”
“我不難受了,媽媽。你上班怎么辦?”安梓軒擔憂地問。
“媽媽請假了,專心陪你。”媽媽沖兒子眨了眨眼睛。
“這樣呀?可以嗎?”安梓軒怯怯地問,“那你明天要上班嗎?”
“也不去了,我陪你。”媽媽一向覺得自己的工作耽誤不得,今天卻被觸動了,“我參加工作這么多年來,除了生你的時候請過產(chǎn)假,其他什么假都沒請過。我應(yīng)該好好陪陪親愛的兒子了。”媽媽的話里夾著鼻音。
那天電話里,聽說兒子失去了知覺,她嚇壞了。雖然她努力說服自己,兒子是睡著了,但眼淚卻止不住地往下落,她多么害怕失去兒子啊。這么多年來,自己忙于工作,當老公嚴厲訓(xùn)斥兒子時,她覺得一切都是那么理所當然,從未認真想過,這一切是不是合適?
從前,她幾乎是缺席了安梓軒的成長。孩子上學(xué)放學(xué),是丈夫接送;孩子邀請同學(xué)過生日,是丈夫張羅;孩子參加游泳訓(xùn)練,是丈夫陪同。此時此刻,她感到深深的自責(zé)。她不明白,自己怎么會支持丈夫粗暴的教育方式,那么多冷嘲熱諷,那么多嚴厲的呵斥。想著想著,她又一次垂淚……轉(zhuǎn)過臉,避開兒子,然后,她輕輕地撫著兒子的手,溫柔地說:“你多睡一會兒吧,醫(yī)生說你可能是太累了。兒子,你不用學(xué)得太吃力,媽媽只是希望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樂樂。”
“謝謝媽媽。”媽媽的陪伴,讓安梓軒心安了。
病房淡藍色的墻漆,還有媽媽溫和的話語,讓他感到放松。許是真的累了,許是病了的自我暗示讓他犯困,他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住院的這些天,安梓軒都睡得特別踏實。
可以出院了。爸爸來接安梓軒和媽媽。
安梓軒一見到爸爸,身體就打了個寒戰(zhàn)。
爸爸麻利地收拾他們的行李,有條不紊地裝好箱:“我給你們煮了松茸雞湯、白灼九節(jié)蝦,還有兒子最愛吃的椒鹽豬蹄,你們都好好補補身子。”
“你爸真能干,是不是?”媽媽站起身,拉著兒子的手,示意他感謝爸爸。媽媽快樂地說道,“我們回家。”
“嗯。”安梓軒的心又開始打鼓,手心直冒冷汗。
“好好學(xué)著,兒子,以后長大了,你也要學(xué)會照顧女生的。”爸爸把拉桿箱遞給兒子,“你來推箱子。”
“兒子才剛出院,你別馬上讓他干活,醫(yī)生說了,還得好好休息。我來推箱子!”媽媽接過行李箱。
“男孩子沒那么虛弱,箱子也不重。你都照顧兒子三天了,也要好好休息。”爸爸體貼地對媽媽說。
雖然安梓軒并沒覺得自己很虛弱,可爸爸的要求,還是讓他渾身不自在。
“兒子,你要不要有推箱子的機會?”爸爸又一次問他。
“你怎么回事兒?”媽媽突然有些生氣,“兒子還是病人呢。”
爸爸笑嘻嘻地說:“兒子是男子漢嘛,沒那么嬌氣。不過,你說的也有道理,你們都需要好好休養(yǎng)。來吧,我推拉桿箱。”
回到家后,安梓軒媽媽恢復(fù)了工作,但她辭掉了多點執(zhí)業(yè)的診所工作,把更多的業(yè)余時間都給了安梓軒。
那段日子,安梓軒很開心,寫作業(yè)很快,還多次得到老師表揚。
5
多年前,安梓軒爸媽在城郊買了棟別墅。
最近,他們打算動工裝修了。他們帶設(shè)計師看別墅時,也會帶上安梓軒。安梓軒不喜歡待在空房子里,他聽不懂那些裝修術(shù)語。爸媽千交代萬交代不能亂跑,不能下水玩之后,同意他坐在別墅前發(fā)呆。別墅前的玉樟溪,緩緩流淌,在山的映襯之下像個溫婉含笑的水精靈。安梓軒是個坐得住的孩子,他靜靜地看著玉樟溪發(fā)呆,偶爾向溪里投個石子兒,看著一圈圈漣漪蕩開來,像對他悄悄耳語什么。
裝修需要不少錢,媽媽又漸漸回到了往日的忙碌,爸爸再次全權(quán)承擔起照料家庭和督促兒子學(xué)習(xí)的重任,生活又恢復(fù)到了安梓軒住院前的樣子。
半年后,安梓軒又開始頻繁地頭暈和肚子疼。
他自暴自棄地想著,我活著有什么用呢?媽媽會掙錢,爸爸會照顧家庭,而我只會給爸媽添麻煩。如果這世界沒有我,媽媽也不用那么累,爸爸也不用生氣。也許沒有了我,世界一定會更好的。
當這種想法無法遏制地鉆進安梓軒腦子里之后,它就賴著不走了,直到媽媽把他送到單霞阿姨的心靈工作室。
那一天,他們聊著山山水水的美,也分享了他們在同一首音樂里感受到的不同畫面和故事。不知不覺中,安梓軒心頭的烏云被驅(qū)散了。
當他逐漸認識到爸爸媽媽不完美,也并不永遠正確的那一刻,所有像石頭一樣壓在胸口的“不聽話、不乖”之類的“評語”,都化成了云霧,飄遠了,散去了。
回家后的安梓軒,仿佛變了個人似的。他會對正大聲吼叫的爸爸說:“爸爸,你別生氣……今天的云朵,真好看。”
他還會主動地問媽媽:“媽媽,我可以為你做些什么嗎?”
有一天,媽媽問安梓軒:“兒子,你怎么越來越乖了?你不怕爸爸吼你了?”
安梓軒聳聳肩膀,說:“吼聲只是吼聲,爸爸心頭有壓力,他不開心,我為什么要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