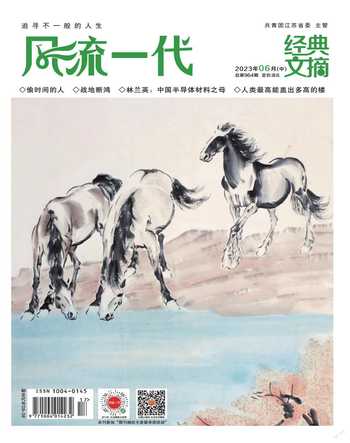荔枝味道
江揚
味道,除了嗅覺、味覺,還有視覺、聽覺和觸覺,都有一種記憶或者畫面。
當粗糙的灰黑色樹皮上,綠著光澤的樹葉布滿嫩枝時,一粒粒細小如豆的黃色花蕾,不顯眼地像一把把傘聚集排列。以數量取勝的荔枝花,在每一條枝上開得成團成簇,給人一種特別熱鬧的感覺。
荔枝的味道,由春天始。空氣里氤氳著花香的氣息,它不濃烈,深深地吸一口,大腦的海馬體瞬間激活,荔枝的情感喚起也由此展開。這種味道是對蜜蜂最大的嗅覺沖擊,尋著香味“嗡嗡嗡”地飛來飛去,忙著在花上辛勤采蜜授粉。
芒種后,不同品種的荔枝陸續散發出果實的香味。它獨特的味道,來自黃色的花蕾,來自溫潤的土地,來自和煦的陽光。走進恍如一串串紅燈籠掛滿樹上的荔枝林,不由讓人停下腳步,循著時間的線索,探聽古老荔枝樹下的歷史回響。
遙想南越王趙佗將中原農耕技術帶到蠻荒的嶺南,荔枝就有了“食其華實為荔枝仙人”的民間流傳。這位史上最長壽的大王為“拍馬屁”,把荔枝北運到漢都長安進貢漢武帝。《西京雜記》中描述漢武帝對于荔枝的喜愛遠遠超過其他的貢品,在上林苑建起世界最早有文字記載的溫室“扶荔宮”,遠從嶺南移植荔枝樹來栽培。不過,史書記載荔枝樹只開過一朵花而沒有結果。
唐朝太監高力士為取悅唐玄宗,讓寵妃楊玉環吃到新鮮的荔枝,每年竟派出快馬,日夜兼程從家鄉嶺南“置騎傳送”。穿州過府,很多官差、驛馬因此累死在半道上。杜牧有感在《過華清宮》里寫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白居易《荔枝圖序》中描寫“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的荔枝味道,總能直擊人們的敏感味蕾,讓無數文人墨客、帝王美人“競折腰”。
一聲聲“知了、知了”的蟬鳴從草尖掠過荔枝林,婉轉成一串串肆意歡叫。這么小的黑色精靈,竟有超音頻的震顫,那響徹一個夏天的歌吟,把我的思緒帶到小學四年級那年,也是記憶中第一次吃荔枝。
我和妹妹乘車去看在山上養雞場勞動的媽媽。正是荔枝成熟的時候,從高處望去,漫山遍野的紅色果實掩映在綠樹間。林中壓彎了樹枝的累累荔枝,伸手便能摘到,我高興地叫妹妹:“看呀,好多荔枝!”得知我們來,媽媽一早就去果農家購買剛剛采摘的新鮮荔枝。當地人說日出之前采摘的荔枝最好吃,摘的時候還要帶上綠色枝葉。
六月的天氣格外悶熱,媽媽把荔枝攤開在床下的地板上,那時沒有冰箱。媽媽說,你倆慢慢吃,我去雞場干活。
她前腳邁出門,我和妹妹就不約而同地趴在地板上看床底,哇!滿滿一地都是荔枝,通紅誘人,我倆席地而坐吃起來。剝開外殼厚實的果皮,如同白玉的果肉晶瑩剔透。咬下一口,除了甜,還有鮮,那似蜜一般的香味,吃了有種沖擊性的愉悅感。我覺得荔枝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沒有之一。
平日,家里也有水果。不過面對這么美味這么多的荔枝,我和妹妹忍不住一顆接著一顆地吃,盡情吃掉了床下大約一半的荔枝。
媽媽回來看到滿地都是荔枝皮、荔枝核時,幾乎呆住了。嚇得我倆連忙說蘇東坡“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距離我們吃掉的數字差得還遠呢。 媽媽一臉哭笑不得的表情。
小時候不理解東坡先生喜歡荔枝的心境,長大后才明白,來自遙遠古代的荔枝,不但具有荔枝所應該有的優秀品質——清新中透出某種溫潤的美好,而且也像蘇東坡對嶺南的情感一樣,更容易得到人們的鐘愛。
記得粵劇藝術家紅線女用花腔女高音唱《賣荔枝》時,把最后“賣荔枝”三個字無限延伸,由強至弱,欲斷還連,兀地翻起一個高腔滑音,隨即戛然而止,將嶺南人對荔枝的那份自豪、那份贊賞,盡情表現在一腔一板之中,至今余音裊裊,韻味猶存。
多年后,我來到陽光格外充足的美國加州,水蜜桃、櫻桃、草莓、西瓜、哈密瓜、香瓜等水果,一個比一個甜,唯獨少了荔枝。有一天,意外發現灣區的華人超市有售荔枝,在誘惑我口腹之欲的同時,也帶來了遙遠的嶺南信息。盡管看上去外皮的鮮紅已漸褪色,價錢賣得也不便宜,仍然非常搶手。買的人除了嘗鮮,還為了要消解那一份相思。我毫不遲疑地買了好幾磅。
到家后便迫不及待剝開荔枝皮,一泡水先滾了出來。經過萬里運輸急速冷凍的荔枝,到達加州后的味道已經不盡人意。其實,古人早就認識到,這種水果不能離開枝葉,在西漢司馬相如的《上林賦》中就把荔枝寫作“離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荔枝圖序》更詳細提到荔枝:“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味道,要有物質基礎為前提。加州的氣候和土壤,也許就不具備欣賞新鮮荔枝的條件。
急凍荔枝給人的手感、顏色以及那果肉的模樣,似乎都讓荔枝的形象變得模糊。然而,荔枝的味道,那種又甜又香的味道,卻始終在心里很清晰,清晰如昨,直到今天。
(王傳生摘自2022年7月16日《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