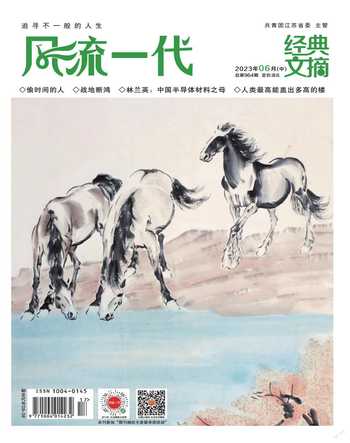媽媽說的話
張頌文
①
六歲的夏日。
小孩子都像貓,喜歡找一個盒子把自己裝起來。我鉆進一個放棉被用的大木頭箱子,把自己裹在軟軟的被子里,關上箱子,狹小的空間成為完全屬于我的童話秘境。我在里面演繹無窮的想象力,幻想自己是一個勇闖魔獸世界的英勇男孩。
啪嗒一聲,箱子的搭扣扣上了,我立刻從假想英雄淪為困獸。神奇秘境因為沒有了光而變成恐怖黑暗的監獄,我發瘋地用腳踹用手推,眼前還是一片黑暗。媽媽推門進來稍停幾秒就再次出門,我沒來得及反應。不知不覺,箱子縫隙里透過來的光線也全都暗下來,天黑了,媽媽總也不來,我哭到呼吸困難。
昏睡中,眼皮突然感受到強烈的光,媽媽打開箱子把我抱了出來:“走,我們去看老奶奶。”
媽媽是小鎮上有名的“馮醫生”。她喜歡回訪病人,經常會帶著我走很遠的路去病人家里,有時還要走夜路。
媽媽牽著我的手,沿著一條水渠慢慢走。水是從山上引下來的,冰涼,清澈,甘甜,一種名叫花手絹的小魚在水里游啊游的,五顏六色的尾巴搖搖擺擺,煞是好看。水緩緩地流,我們慢慢地走。走累了我們就停下來坐一會兒,以手做瓢舀水喝。
②
那天去的是一個老奶奶家里。她住在一個舊舊的陰暗小平房里,小院只用一個竹籬笆圍著。門都不用敲,一推就開。
老奶奶躺在床上,很努力地想爬起來。媽媽坐在床邊握著她的手說:“阿媽你怎么樣?身體什么感覺?”“沒力氣,渾身沒力。”“但是你臉色好多了。”
小屋里點著一盞很暗的煤油燈,我幾乎看不清老奶奶的臉。老奶奶咧開缺牙的嘴笑了:“真的嗎?”
“對啊!你現在只是缺一種維生素。有了它就會很快好起來。”
老奶奶不笑了:“沒有錢買藥。”
媽媽拍拍她的手背說:“不用買!只要你每天曬半小時太陽,你身體里就有這種維生素了,你的病就好了!”“真的?”“真的!”
過一個星期,我跟我媽又去看她。那是另一個黃昏,夕陽正在落下。
遠遠地看見老奶奶坐在門口的藤椅上,睡著了。
媽媽輕輕拍了拍她的手,叫“阿媽”。
老奶奶睜開眼睛開心地說:“哎,馮醫生,我現在感覺好多了。曬太陽這個方法太好了,曬完以后我真的不疼了。”媽媽說:“你要堅持曬太陽啊。只要你每天曬,很快就會好了。”
回去的路上,我覺得媽媽不開心。
“媽媽,那個奶奶的病是不是好了?”
“她還有一個月。”
媽媽說她得的是絕癥。
我說:“你不是說曬太陽能好嗎?”
“沒有多大幫助,只是讓她覺得有一些希望。一個人最怕沒有盼頭,你只要給她希望,就好。”
那個慈祥的老奶奶總是給我吃特別好吃的櫻桃,我很喜歡她。我哭了很久,一路走一路掉眼淚。不過是半個月,老奶奶還沒撐到我媽說的一個月,就去世了。我相信,她走的時候,心里安詳而有希望。
③
高一的一天,爸爸來宿舍找我,說了一堆好好學習、多照顧自己之類的片湯話。然后頹然又艱難地說:“你媽確診了,是癌癥。”
爸爸是個軍人,雷厲風行,話不多,總是很威嚴。他從不低頭服輸,這么大的事,他一定是覺察到過征兆,獨自扛了很久,實在不知道怎么辦了。我不記得具體的對話內容,只記得當時他眼角的淚。
這一天起,我少年的心陷入悲涼。陪床的日子有一年多。那段漫長的日子里,媽媽日復一日地躺在病床上,無力而面色蒼黃,沉重的呼吸一開始讓人膽戰心驚,后來變成司空見慣。瑣碎的事情一天一天格式化,醫生護士都變得很熟。
仿佛一切都不會變化,好像媽媽整個后半生都會這樣躺下去。誰都知道那一天終將會來,卻又都盼望不要到來。等待的時間很長,于是感覺那一天似乎真的不會來。唯一每天讓我們慶幸的是媽媽還在。我對生活的期望簡單地降低到極點,只要她不呻吟,我就覺得很幸福。
某個課堂上,我突然心神不寧,像是心里炸開一顆雷,想到了媽媽,以為是心靈感應的征兆,請了假奔出教室騎上自行車一路狂奔去醫院。半路上下了一場雨,更以為這是天意,想到媽媽可能出事,不禁悲從中來。
偏偏車鏈子也意外地斷了,我淋著雨,推著自行車,一路號啕著,每邁出一步,腳下都甩出一大坨爛泥,一步一滑,幾次都差點跌倒,一路上內心充滿絕望。擦了眼淚進到病房,媽媽一如往常正在熟睡。媽媽醒來后心疼地說:“以后上課時間不要來看我,不要擔心。”
這樣的虛驚又發生過幾次。再后來,生離死別的概念根本就不在我腦海里了。我想做一個孝子,盡心陪護癌癥晚期的媽媽,事實上乏味的陪伴讓人抓狂,越來越深地加重我的孤獨感和絕望。
媽媽已經到了要打杜冷丁止痛的程度。每當她虛弱地說:“文仔,我疼。”我就習慣性地說:“打針吧,一會兒就好了。” 我止不住地想:這樣無聊的日子真是煩透了,什么時候才能結束?媽媽做過醫生,對自己的病情很了解,大家的安慰和避重就輕并不能真正讓她高興。她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
④
媽媽離開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大人眼里的爛仔。那以后長達十多年,我一聽到別人提起媽媽就會止不住痛哭,我總覺得內心愧疚,沒有在她最需要的時候給予最好的陪伴,沒有在該珍惜的歲月里給予足夠的回報,沒有在來得及的時光里讓她得到安慰。
我讀了無數本心理學書籍,把自己分析得底朝天,終于有一天,規勸別人節哀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應該為這么多年的愧疚作一個了結。當年的我沒有能力給予,沒有能力付出我想要的分量,我只是順其自然地過一個正常男孩想要揮霍的時光,我應該給予媽媽的不是愧疚,而是感謝和懷念。
媽媽對我的期望,并非成為大人物,而是活得明白和開心。當我明白了這一點,終于可以平靜地真正接受媽媽的離開,在靈魂深處,終于釋懷。小時候媽媽給我講過很多事情,當時并不都懂。長大的歲月里,每當我有困惑,就在心里回放媽媽說過的一切。
越長大越覺得,所有的問題,在媽媽的聲音和故事里都有答案。她用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方式告訴我:文仔,一切都會有辦法,只要你清楚你的目的,只要你找到方式。你記得怎樣迅速記住一個手機號碼嗎?像是腦子里有個錄音機,迅速記下那串數字,再在腦子里回放,一遍不夠就回放兩遍,兩遍不夠就回放三遍。
⑤
這世界就是這個樣子,你不知道哪顆種子長出的樹最好,只有悉心對待每一顆,就算有的永遠爛在地里,你終究會收獲一片樹林。老天當然有瞎眼的時候,下一場雪,又蓋上一層霜,但只要你熬得過去,當春天來的時候,雪會化成水,滋養你的土地。
媽媽也不知道究竟哪句話會對我產生影響,她只是傾盡所能,用成年人的方式提前教我長大。媽媽讓我明白,人不能認命,如果你覺得到此為止,你這輩子只能有一種模式。而拼命尋找方法的人,人生的道路,有組合模式。
冥冥中似有指引,我走過泥濘,做了酒店經理,做了導游,讀了電影學院,做了演員,又做了表演老師,換過太多頻道,轉過無數個彎。我一次次在迷茫和艱難時對自己說:再想想,一定還有辦法。
去年到老家的禪寺里祭拜媽媽。下午的佛堂,靜得仿佛時間停止。幾千個格子里,住著幾千個靈魂,牽系著幾千個家庭的懷念和悲傷。我看著媽媽的照片,默默在心里給她講我這一年的事情,好像又回到當年她給我講她所見所聞的場景。
我無法不思念,但我已不悲傷。我知道,只要我記得媽媽說的話,她就一直都在。
(姚梅芬摘自《視野》2023年第5期,西米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