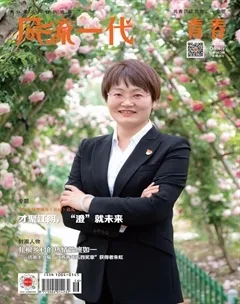沒有“身份”的實習生誰來保護?
共享文檔表格里,羅列著某APP幾百條帖子。王麗(化名)依次點擊進入,寫下不同評論:“支持、感動!”“太可惡!”不到半個小時,她就點評了20多條。
自3月開學以來,這是大三學生王麗每天要做的“功課”。作為一家互聯網企業的遠程運營實習生,她需要把這項工作干滿4個月,才能獲得實習證明。
教育部的數據顯示,今年,全國高校畢業生預計達到1158萬人,同比增加82萬人。“現在畢業生幾乎人人手握三四段實習經歷,沒有相關經歷很難找到工作。”王麗說。
在實習證明背后,實習生勞動權益保護的話題值得關注。
倒貼實習管理費,什么也沒學到
如今正讀研一的向家(化名),說起大二時在某傳媒企業的實習經歷,不由感嘆道:“既倒貼費用又沒學到東西。”
向家本科讀的是廣告學專業,對電視節目制作很感興趣。2020年6月,他看到某綜藝節目組的一則招聘公告,通過面試,他成為這個綜藝節目組的實習編導。
到節目組前,向家就吃了一個“下馬威”。工作人員告訴他,想順利到這里實習,他要聯系屬地派出所開無犯罪記錄證明,還需要交500元一個月的“實習管理費”。
“培養一個實習生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你的工作不熟練,會給大家造成麻煩,拖慢工作進度。”正當向家詢問“實習管理費”是否合法合規時,與他一起辦理實習手續的同伴已欣然接受,并稱“特別優秀的人才能免去這筆費用,我們要交500元,是因為我們不夠優秀”。
想著機會難得,向家只能交了這筆費用,但接下來的實習體驗讓他并不愉快。在節目組,誰都能使喚他干活。向家負責該節目的新媒體宣發,員工一股腦兒把活兒交給他,也不進行指導,只交待他產出文案、視頻。
向家還負責節目現場的后勤保障工作,他經常下午到錄制現場,忙碌到第二天一早。更讓他郁悶的是,“他們員工的活兒都給我干了,還時時暗示我‘不夠優秀’。”
4個月后,向家結束了這段實習,拿到了實習證明,卻感受不到獲得感。
君輝律師事務所律師何金宇表示,2019年發布的《教育部關于加強和規范普通本科高校實習管理工作的意見》中規定,高校和實習企業不得違規向學生收取費用,不得扣押學生財物和證件;要保障頂崗實習學生獲得合理報酬的權益,勞動報酬原則上不低于相同崗位試用期工資標準的80%。“我國民法典、勞動法中都沒有實習管理費的相關規定,因此不能征收任何實習費用。”何金宇說。
向家稱,目前,這家企業已取消收取實習管理費的做法。
有的實習生情況好一點。
王明(化名)在一家互聯網公司招聘內容運營崗位上實習了4個月。由于他發帖的內容有趣,為此獲得了200元的購物卡作為“工資”,還有一些禮品。但直到離職,他都沒有與該企業簽訂任何形式的實習合同,他也搞不清楚與這家公司是何種勞動關系。實習證明上標注的是他參與的是遠程實習。
雖然這段經歷沒有為王明增加有意義的工作經驗,但一紙實習證明幫他獲得了后續不少面試機會,他說:“總比要倒貼費用還學不到東西的實習強。”
有的沒人理,有的受侵害
今年夏天即將大學畢業的李曉(化名)為了增加簡歷的分量,3月初特意找了一家軟件公司實習,在從事測試工作的部門工作。“雖然沒有加班費,但為了多學點東西,我也跟著一起加班,可一個月過去了,根本沒人帶我。”李曉說。
公開資料顯示,我國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學生進入用工單位實習。然而,大部分實習生尚未脫離校園,無法簽訂勞動合同,從法律意義上說,實習生并不能與受勞動法保護的勞動者身份直接掛鉤。因此,實習實訓違規收費、實習期間學生受到傷害、學生合法權益保障不力等問題時有發生。
陳涵(化名)是四川某職業學院一名建筑工程技術專業的學生,基于學校畢業實習的要求到A公司實習,A公司以勞務派遣的方式將他派至福建B公司,之后B公司又將他派往總承包單位C公司某高速隧道工地從事測繪工作。
陳涵工作時意外受傷,經司法鑒定構成二級傷殘。近段時間,陳涵受傷賠償案迎來終審判決,法院認定醫療費、護理費、殘疾賠償金等損失合計232.63萬元,A公司、B公司分別承擔30%的過錯責任,學校承擔20%的過錯責任,陳涵本人、C公司分別承擔10%的過錯責任。
“在這起案件中,相關公司存在不少侵犯實習生權益的行為,比如以‘技術咨詢費’‘場地介紹費’賺取收益的形式對陳涵實施‘勞務派遣’,上崗前未對陳涵進行安全防護知識及崗位操作規程教育培訓,施工現場安全防護措施不足等。”該案代理律師、廣東合拓律師事務所律師吳夢凱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還有更嚴重的。
此前,湖南衡陽某學院一名女學生在網絡上發布求救信稱,其2021年6月進入校企合作單位實習,后被企業領導性侵并懷孕。之后,校方發布情況說明:學校關注到2022屆畢業生在網上發布的求救信后,第一時間與該畢業生取得聯系。后來,當地公安機關對此案立案偵查。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范圍表示,實習單位對實習生權益的侵害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勞動報酬權,尤其是職業院校的定崗實習生,他們的工資報酬通常低于市場水平;二是休息權,他們常常會被要求長時間工作;三是職業安全衛生權,有些實習單位的工作條件較差,沒有對實習生進行足夠的培訓和保護,使得他們可能遭受職業傷害。
法律是維護權益的堅強后盾
每年求職畢業季,都會有反映大學生求職、升學困境的“熱詞”出現。在當前激烈的人才競爭環境下,學生們所面臨的實習、就業等壓力不容小覷。
為幫扶大學生實習、就業,國家、地方各部門均推出不同的措施,而在相關部門中,共青團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針對在校大學生實習,共青團中央推出了大學生實習“揚帆計劃”,組織他們參與政務實習、企業實習、職場體驗活動等各級各類實習活動。
自2019年起,大學生實習“揚帆計劃”在全國范圍內鋪開,各級團組織累計組織150多萬名大學生參與各級各類政務實習、企業實習,57萬余名大學生參與職場體驗活動。
而在社會上選擇實習單位和崗位,大學生們需要擦亮眼睛。
按照常理,有付出就應有回報,但現行勞動法未賦予實習生勞動者的身份,使得一些勞務中介機構和實習單位趁機鉆法律空子,出現向實習生違規收取各種費用、克扣實習津貼、安排實習生超長時間工作、不提供必要的勞動安全保障等不法行為。如何有效保障實習生合法權益,避免他們成為不法勞務中介機構斂財的工具和實習單位的廉價勞動力,是一道必須待解的現實命題。
值得肯定的是,近年來,司法機關對此進行了積極探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導案例中,已有認定就業型實習生可以與實習單位構成勞動關系的個案。
“目前很多省份都頒布了實習生職業傷害保障方面的地方性立法,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部委也聯合印發了管理辦法,但還欠缺一部全國范圍內適用的高位階立法,通過法律的強制力切實保障實習生的權益。”中國政法大學社會法研究所所長婁宇認為,現有規范性文件對于保障機制和維權機制的設計比較簡單,可操作性不強,再加上宣傳力度不夠,相關群體的維權意識欠缺。
“不能把‘不知者無罪’作為實習單位違法的免責事由。”何金宇呼吁,要進一步向用人單位等普及實習生權益保障的相關法律法規;同時有關部門應加強監管,明確對實習單位違規的處罰措施。實習生也要學會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資料來源:中國青年報、法治日報、北京青年報、共青團中央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