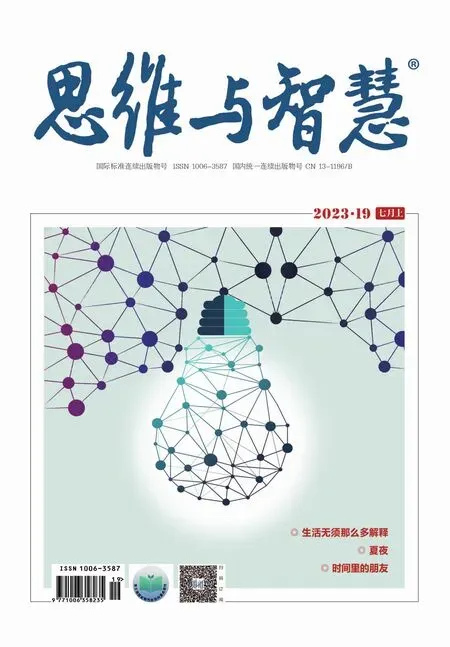踩泥
◎ 張亞凌

每年夏天我都會去河灘踩泥,倘使某一年沒有成行,接下來的秋天與冬日,必是渾渾噩噩,渾身不舒坦,沒有精氣神,像被抽了筋剔了骨。
踩泥在我,是養護童年里的美好,以免在歲月的流逝中因童年褪色而迷失自己。
踩泥首選河灘邊。
起初是光光的硬硬的一塊地,赤腳,高高低低地踩起來,能聽到赤腳與光地因久未見面響亮的寒暄聲。慢慢地,泥點開始迸濺,當然少不了親近上衣,一片一片,泥花怒放。赤腳者已年過四十,卻歡喜如孩童。赤腳與光地的話兒越說越多,越說越深,越深的話題聲音越小,就像嘴巴湊在耳邊竊竊私語。
聲音越來越小,小至消失,腳下那塊地成了貨真價實的泥,軟軟和和的泥,腳拔出又落下,是沒了聲音,卻有了騰云駕霧之妙感。
后來啊,越踩越厚實,泥漫過腳背,漫過腳腕,漫向小腿,直到膝蓋。對,到膝蓋處就恰到好處,人就穩穩地“栽”在了泥里,不倒翁般,左右晃著也倒不了。
泥至膝蓋,就得挪窩了。
到了膝蓋再想拔腿出來就得有人幫忙,自個兒只會越折騰越糟糕,絕對無法脫身,有種身陷沼澤的絕望。幫忙的那個人得像踩泥者一樣,有顆未泯的童心,或者,對泥土有深入骨髓的熱愛。而不是撇著嘴,滿臉嫌棄地小心地拉著踩泥者,生怕將自己弄臟。
要想盡情盡興地踩泥,一定要找好同伴。得找能真正陪你酣暢淋漓的人,否則會大煞風景。常常是意猶未盡,重新找塊灘邊光光的硬硬的地兒,開始新一輪踩泥,反反復復,酣暢淋漓,樂此不疲,興盡才不得不歸。
聽家在河邊的朋友說,他們才不會如此用蠻力的,隨時想,隨時玩,就像拉著寵物樓下遛一圈。作為遠離河岸的旱鴨子,驅車往返百余里,踩一次恨不得將河岸扯起來塞車里帶回去。
如果真的總是漲水近不了河邊,就只能在雨后,到偏遠的郊區(城里不是柏油路就是水泥路),瞅著四下無人,脫掉鞋襪,在泥土路上撒歡一回。小小地過個癮,抖落掉不喜歡的厭惡的,讓自己清爽起來。
鐘情于踩泥源于童年。
五十年前,農村,土院落。雨后,院子里蓄了水,常常赤腳在水里撒歡。我的母親是教師,規矩多。她不喜歡我在水里瘋玩,還讓我“笑不露齒行不動裙”“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一開口就拿條條框框往我身上硬套。有時面對母親,我竟會覺得自己身上每一個部件都沒長對地方,我無法成為她期待中的好女孩。
好在,我有姥姥。
姥姥說,要那么多講究干啥,小孩就要有小孩樣。放開了,才能長開。
有姥姥這個大靠山,我的童年幾乎是全方位散養。我呢,就在姥姥的寵溺下隨心所欲,各種折騰各種嘗試各種受傷,反倒愈挫愈勇,以至于成了膽大得能捅破天的假小子。后來歷盡磨難依然滿臉燦爛昂首挺立,或許真得感謝兒時的散養。
美好的童年,是一個人可以攜帶一生享用不盡的大禮包,而每年踩泥,則是我重返童年的神奇隧道。童年,是我向上成長的龐大根系,我能繼續不偏不斜端端正正地行走就得益于她的滋養。
終其一生,我都是從鄉下泥土地里走出的孩子,我得記得時時回望自己的來路才能看清去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