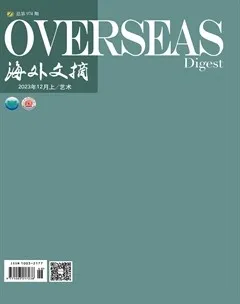明清才女季嫻:生平與作品的文藝透視
近些年來,明清女性的文學批評活動愈發引人關注,季嫻作為研究明清女性文學研究繞不開的人物,我們有必要對關于她的研究進行回顧。本文對季嫻的研究從其生平與家族背景、作品形式與體例、作品內容與風格三個方面進行概述研究,力圖厘清季嫻研究的成就與不足。
季嫻,字靜姎,明清揚州府人。著有詩文集 《學古余論》《學禪諢語》等多部,編選《閨秀集》兩卷。晚明以來,江南地區掀起一股為女性選編出版詩詞集的熱潮,至沈宜修《伊人思》出現第一部女子為閨秀才媛輯撰的作品集。此外,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季嫻《閨秀集》、梁小玉《古今女史》以及王端淑《名媛詩緯》等都影響廣泛。其中,陳啟明將季嫻《閨秀集》稱為“第一部女性論詩之選”,稱贊季嫻“作為女性選家第一次以自覺的批評意識主動參與到主流詩潮中”[1],可見《閨秀集》的標志性意義。
1 生平與家族背景研究
季嫻出身名門,自幼在良好的家庭環境和文化氛圍中熏陶成長,多數文獻在提及季嫻時總是忽略其生平經歷甚至出生年月。根據季嫻丈夫李長昂為季嫻編撰《雨泉龕文集》序言中的信息:“及戊子霖兒幸叨秋鑒,偕天中北上。以十六歲兒離膝下,內子之感也何似![2]”可以推測出1648年戊子時,季嫻的兒子李子霖時年為16歲,可知季嫻在1632年生下兒子李為霖,由此可以大致推測出季嫻的出生日期。
其次,筆者將季嫻的生平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出嫁前、婚姻前期和婚姻后期。第一階段出嫁前,多數文章關注的是關于季嫻幼時受教育的描述以及與父親出游的經歷。陳啟明《第一部女性論詩之選:季嫻<閨秀集>》提到:“予幼非穎慧……而舅氏宗伯公藏書架滿……因得肆覽焉。”季嫻的個性與才情在具有濃厚文化氛圍的家庭環境中自由發展,年歲稍大后又隨父親宦游,飽覽齊魯冀豫等地風物,這對季嫻文化品性的造就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第二階段中,季嫻完成了其重要作品的收錄與輯成。王向東、許霽在《秀擅閨中,風高林下——明末清初揚州才女季嫻傳論》中指出,與宰相李春芳家族結親,標志著她人生中一個嶄新而重要的階段就此開啟。婚姻前期,季嫻與丈夫同心同德,丈夫也支持她的創作。王翼飛在《清代女性文學批評研究》中提及,《閨秀集》的編纂并非季嫻獨立完成,背后有著丈夫李長昂的大力支持與協助。李長昂不僅慷慨地為妻子提供豐富的藏書資源,還積極鼓勵并激發她進行書籍的編撰工作。“子既羨閨閣之多才,……易不為諸才媛謀可傳哉?[3]”正是得益于丈夫李長昂的不斷鼓勵與實質性的支持,《閨秀集》才能夠順利刊印并廣泛流傳。同時,王向東指出,《雨泉龕合刻》的出版發行,與李長昂的助力有著更為直接且密切的關系。在《雨泉龕合刻》中,李維章序謂“(嫻)數年來所著益多,予因匯已刻未刻嚴汰之,共此篇,以質之作者”[4]。作為旁觀者的李清,在為此書所作的序文中寫道:“今以雨泉龕詩刊,則予叔維章志也。”可見,李長昂對季嫻的支持力度之大。在第三階段中,季嫻的婚姻經歷了婚變。順治十四年,李長昂私藏姬妾,使得二人離心離德,季嫻回應:“‘原欲為汝置一人,今既有此,何不攜歸?維章堅不肯從”。由此季嫻的愛情期待與生活理想遭受了重創,其創作風格也轉向傳道論禪。
此外,在家族背景的研究中,王向東的論文《明清昭陽李氏家族文化文學研究》、許霽的論文《清代延令季氏家族文學研究》中均有對季嫻的提及,但不是以季嫻為重點,其中前者探究延令季氏家族的血脈傳承與歷代變遷;后者在“明清昭陽李氏家族的女詩人考述”一節中,對季嫻的生平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考述。
總之,在對季嫻的生平與家族背景的研究中,大多數是對季嫻《閨秀集》和《雨泉龕合刻》的序言中的只言片語的引用和解釋,對季嫻的生平未加系統化梳理。而對季嫻生平的考察,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季嫻文風形成的時代因素、人生經歷影響與其文風轉變的原因,進一步挖掘其久浸佛道的思想內涵。
2 作品形式與體例研究
季嫻在文學上的兩大貢獻包括:一是整理并出版了《閨秀集》,二是創作并發行了《雨泉龕合刻》。
《閨秀集》共分上下兩卷,其中每一體中按照以類編排的原則編排。陳啟明在《第一部女性論詩之選:季嫻<閨秀集>》中指出《閨秀集》編排的兩大特色,一是以詩體為經緯,“《四庫存目叢書》影印《閨秀集》2卷附詩余1卷,……上卷選錄詩歌體裁有樂府四言古詩五言古詩七言古詩,……清鈔本卷首依次為季嫻自序選例與選里氏目次,共選錄明代閨秀75家,詩360首,詞27首。”具體來說,該集按照詩歌體裁分類編排,內容分布如下:第一卷含樂府36首,四言古詩3首,五言古詩30首,七言古詩28首,及五言排律12首;第二卷則包含五言律詩75首,七言律詩44首,五言絕句45首,六言絕句3首,和七言絕句84首;第三卷收錄詩余作品27首。陳啟明指出,這種編排方式延續了前人的分類傳統,以詩體為經緯來編排內容,將人們對女性詩歌創作的焦點由人引向了詩作本身,對作品進行真正審美意義上的鑒賞。二是采用夾批和詩后簡短評論的方式,對女性創作的詩歌進行賞析與評價,不同于其他女性詩歌選集的多編選而少評點,《閨秀集》收詩360首,點評之作就超過了250首,這些評論大多融入詩句間的夾注和詩篇結尾的簡短點評中,“如此詳細的圈點評贊是此集與其他女性選集最大的不同”。王翼飛也在《清代女性文學批評研究》中指出這一點,“沒有刻意說明女作家的身份德行,只是對所選詩作進行了純文本的鑒賞性分析,這是整個中國文學批評都鮮有的。”這一點也是《閨秀集》能在眾多女性詩詞選本中顯赫出眾的關鍵因素。吳琳在《清初女性詩歌嬗變研究》中指出了《四庫總目》中關于是集“皆近體也”描述的錯誤,并闡述了季嫻《閨秀集》體例的影響,“康熙時期女史范端昂編《奩詩泐補》《奩泐續補》,即依此書體例,多錄季嫻評語。”此外,陳啟明在《清代女性詩歌總集研究》中將季嫻的《閨秀集》與沈宜修的《伊人思》對比指出:“《閨秀集》的選源顯然更為豐富,……而很有可能是直接從這些入選詩人的詩集本身獲取詩源。”
在關于《雨泉龕合刻》的形式與體例的研究中,僅有兩篇文章涉及。王向東、許霽的《秀擅閨中,風高林下——明末清初揚州才女季嫻傳論》中指出季嫻將文章分為兩類,“釋氏所為”的“醒世之文”和“儒者所為”的“名世之文”,其中《雨泉龕合刻》文集一卷中的八篇都為“醒世之文”。許霽在《清代延令季氏家族文學研究》中指出《雨泉龕合刻》包含八卷,其中文集一卷,詩集七卷,作者將目錄搜集摘錄附在文中以供參考。
總之,在關于季嫻作品形式與體例的研究中,多數學者的目光關注于《閨秀集》的編排體例上,一是以詩為經緯的編排體例,唯詩品論之,是真正對詩的審美鑒賞;二是夾批和短評的形式,該選集特有的詩學批評視角先行引導讀者,與其他女性詩歌選集形成鮮明對比。關于《雨泉龕合刻》的形式與體例的研究,僅停留在初步分類與詩文篇目的輯錄,這一方面有所欠缺。
3 作品內容與風格研究
在關于季嫻作品內容與風格研究中,多數人的關注在于其《閨秀集》。陳啟明在《第一部女性論詩之選:季嫻<閨秀集>》中明確指出季嫻“崇尚復古”的選心,他指出首先在詩文的題材和內容上季嫻尤其欣賞閨秀“復古”之作,以徐媛、許景樊為例刻意體認古詩典范的作品。再次,季嫻在詩文的評點中,非常看重詩歌在“格律聲調、語詞篇章等詩學本體層面上的規范性和唯美性”,這種強調與她秉持的復古詩學觀念緊密相連。加拿大學者方秀潔(Grace S. Fong)在其專著《她自己就是作家:中國封建帝制晚期背景下的性別、能動性和寫作》(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6]中對季嫻的《閨秀集》進行了分析,她對《閨秀集》的序言與選例進行解讀,指出男性文人對女性詩歌評判標準的松懈是女性詩歌質量低下的原因。其次,在其夾批中方秀潔用具體的例子來闡述,季嫻的批評是真正的“實用”批評,包括對詩歌作品的風格和形式方面的具體的、有益的評論。她認為季嫻的編輯實踐確實體現了她的文學價值觀與“自由”價值觀之間的張力,以及她的倫理取向,這對季嫻最初的編輯目的——自娛以及給女兒李妍提供閱讀模板而言是合理的。
關于《雨泉龕合刻》作品內容與風格研究,僅王向東、許霽的《秀擅閨中,風高林下——明末清初揚州才女季嫻傳論》中有所涉及。二人總結出季嫻所作詩集“凄美”的特點。晚年生活的孤寂、哀傷,深刻影響人的心境,然而,季嫻又細膩多情,把情感當作內心的慰藉和精神的解脫途徑。此外,郁步生在《明代揚州府作家研究》中找到季嫻的五首詩并加以分析,指出季嫻“淡而有味、韻味無窮的藝術風格”[7]。
總之,關于季嫻作品內容與風格的研究,在《閨秀集》中,學者往往關注季嫻選擇的詩作中的鮮明的女性特色,即強調“綺、婉、秀”的特點[8];其次,她挑選的詩歌注重格律、音韻及文辭結構的規范美,彰顯了向古典致敬的“復古”風格。在《雨泉龕合刻》中,更多關注其卷一文集中佛理、禪理的闡釋,剩余七卷中詩集“凄美”的特點。然而,由于研究文本的缺乏,導致對這兩部作品還有待于從更多的角度去開拓挖掘。
4 結語
回顧近些年來對季嫻的研究,大體是從其生平與家族背景、作品形式與體例、作品內容與風格三個方面來展開研究,其中第一個方面的研究多為談論其家族時涉及對季嫻的探討,另外兩方面的作品也主要關注其《閨秀集》和《雨泉龕合刻》,并多數以前者為主。關于季嫻的研究文獻中直接論述的不及十篇,一些重要著作如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合山究《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9]、曼素恩《綴珍錄:18世紀及其前后的中國婦女》[10]等都未見或少見關于季嫻的研究。可見的第一部對季嫻進行較為詳細的論述的文獻是加拿大學者方秀潔(Grace S. Fong)2008年的專著《她自己就是作家:中國封建帝制晚期背景下的性別、能動性和寫作》。在分析中,方秀潔以《閨秀集》為例,強調女性評論者如季嫻,更重視突出“性情”與“性靈”,相比男性評論者,在選編時通常首先考慮符合婦德的內容,其次才是藝術審美價值。目前,學者們對季嫻的研究已經有了基本的輪廓,但值得深入探索的領域還有很多,如季嫻的出游、家庭變故對其創作風格的影響、季嫻的佛禪思想探究、《雨泉龕合刻》體例分析等,都是今后值得研究的課題。■
引用
[1] 陳啟明.第一部女性論詩之選:季嫻《閨秀集》[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6(2):100-107.
[2] 黃強.李漁研究[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308-309.
[3] 王翼飛.清代女性文學批評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14: 60-61.
[4] 王向東,許霽.秀擅閨中,風高林下——明末清初揚州才女季嫻傳論[J].揚州大學學報,2011(6):74-79.
[5] 吳琳.清初女性詩歌嬗變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13:8-10.
[6] Grace S. Fong,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8.
[7] 郁步生.明代揚州府作家研究[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 2010:147-148.
[8] 尹玲玲.論《閨秀集初編》的女性編選視角[J].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17(1):48-51.
[9]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0] 曼素恩.綴珍錄——18世紀及其前后的中國婦女[M].蘇州: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
作者簡介:趙子亨(2000—),男,山西臨汾人,碩士,就讀于濟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