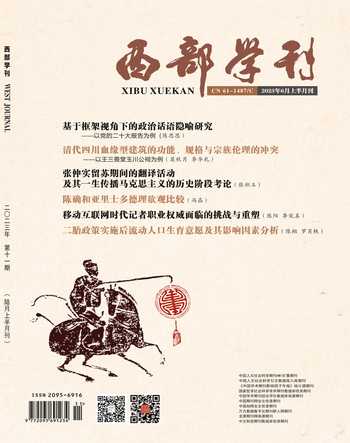中國共產黨對農村土地政策的實踐探索與經驗啟示
摘要:自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充分重視土地對于革命、建設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意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土地政策進行了調整,先后經歷了土地社會公有、耕地農有、減租減息、土地集體所有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系列變革,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進程中不斷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土地制度。這一系列的實踐探索,凸顯著土地政策改革始終堅持黨的正確領導、堅持立足人民立場和對社會基本矛盾適時調整的價值旨歸,從中啟示我們在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中進一步探索馬克思土地產權理論中國化的實現路徑、鞏固馬克思合作化理論的實踐成果,并用匹配土地政策助力社會協調發展。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價值旨歸;經驗啟示
中圖分類號:F32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3)11-0030-05
糧食安全是事關國家穩定發展和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土地權利制度是土地政策的核心,是經濟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基礎,決定著國家的基本制度和治理體系。在探索實現土地公有的實踐中,我黨的土地政策先后經歷了土地社會公有、耕地農有、土地集體所有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及建立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三權分置”(即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等階段,促進了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歷史進程。本文以二十大精神為指導,從推動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背景出發,分析我黨成立以來土地政策改革的一般歷史性規律,以期給實踐提供參考。
一、我黨農村土地政策的歷史沿革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1921—1927年):土地社會公有
1920年11月,上海共產黨組織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宣言》提出:“將生產工具——機器工廠、原料、土地、交通機關等——收歸社會共有,社會共用。”[1]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浙江嘉興召開,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明確規定了“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歸社會公有”的政策目標,這是黨的農村土地政策的最初觀點,體現著黨的農村土地政策鮮明的階級特點。
(二)土地革命時期(1927—1937年):耕地農有
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在探索和實踐中,中國共產黨逐步深入認識我國革命的性質,提出耕地農有政策。1927年11月28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明確提出“一切私有土地完全歸組成蘇維埃國家的勞動平民所公有”[2]。1928年6月召開的中共六大對土地問題的立場是“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耕地歸農民”[3]。1926年8月瞿秋白在《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中提出中國國民革命的意義是解放農民,明確提出“耕地農有”[4]主張。1928年12月湘贛邊區蘇維埃政府頒布《井岡山土地法》,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制定的第一個土地法,提出“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1929年4月,《興國縣土地法》將《井岡山土地法》中的“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興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所有,分給無田地及少田地的農民耕種使用”[5]。1929年,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實行以鄉為單位,抽多補少,自耕農的土地不沒收的政策。我黨通過一系列政策保障農民對耕地的所有權,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升了農民的革命熱情,在開展土地革命的地區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群眾基礎。
(三)全面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年):減租減息
全面抗戰時期,一切工作圍繞抗日政治路線展開,為盡快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日作戰,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若被采納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可以實行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四項保證。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正式確立減租減息政策。1942年1月2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詳細研究各抗日根據地減租減息經驗的基礎上,通過了《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制定了抗日時期土地政策的三項基本原則。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的指示,在華北及陜甘寧邊區的解放區和東北解放區,普遍開展了反奸清算和減租減息運動[6]。
(四)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年):耕者有其田
解放戰爭時期,為實現團結全國人民、打敗國民黨反動派,建設新中國的政治任務,我黨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提出實行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7]的口號。1945年在黨的七大《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指出“首先在全國范圍內實現減租減息,然后采取適當的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8]。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決定將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轉變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9]。1947年《中國土地法大綱》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0],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確立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五)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1949—1978年):土地集體所有制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有步驟地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11]。1950年6月30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明確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該所有制實行后,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以調動,更大程度地提高了生產效率。但是由于生產資料的局限性以及資金等問題,導致生產只能在零碎化的土地上進行,難以實現更大的突破和進展。1953年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期間,先后成立了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逐步實現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中國農村土地所有權實現了由農民個體私有制到集體所有制的變革。
(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8—2012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貫穿這一時期土地政策的主線。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對包產到戶政策改革給予強有力支持,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表示“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十五年以上”[12],對土地承包期做了年限規定,進一步確保了土地的穩定性;同年11月,再次提出“土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不變,在承包期內,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13],充分保障了農民土地承包權的穩定性,減輕了農民的后顧之憂。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經營制度”。2002年8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保護農村土地承包權流轉,土地可以以多種形式進入市場,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進行規模經營,提高農產品質量和產量,促進生產方式進步。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農村土地制度,農戶在承包期內可依法、自愿、有償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完善流轉辦法,逐步發展適度規模經營。
(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2012年至今):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
為了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增強土地政策與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的匹配程度,我國從落實土地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出發,提出“在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基礎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允許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向金融機構抵押融資”[14],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前提下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流轉的框架。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土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并指出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彰顯出“三權分置”制度的政策目標和實施意義。2019年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的意見》這一文件中,提出“土地承包期再延長三十年,使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從第一輪承包開始保持穩定長達七十五年”[15],與穩定農戶承包權政策具有內在統一性。2020年施行的《土地管理法》(第三次修訂)確立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基本制度。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破除了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在市場上流通的阻礙,使得土地利用得到更大的空間,不僅對增加農民收入、推動共同富裕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大大促進了鄉村振興。
二、我黨土地政策改革的價值旨歸
我黨的土地政策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之上,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逐步探索、形成、完善和發展起來的,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其中所體現出來的黨的領導、群眾創造和生產關系調整是我黨土地政策改革的價值旨歸。
(一)始終堅持黨的正確領導
黨的正確領導使農村土地政策的制定、貫徹和變革始終服務于黨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心任務[16],始終堅持黨的領導確保改革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確保人民在改革中獲得最大權益。
一是與時俱進促改革。沒有黨的正確領導,就沒有正確的農村土地政策。“土地社會公有”“耕地農有”“土地集體所有制”等是我黨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變的基礎上,根據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實際和黨的中心任務進行土地政策改革的成果。每到一個關鍵節點,黨都能夠掌控全局,做出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決策部署。在民族大義面前,中國共產黨主動提出從“耕地農有”轉為“減租減息”政策,最大限度地團結了可以團結的力量,最終實現抗日戰爭的勝利[17]。改革開放后,黨對包產到戶的行為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出臺五個“一號文件”為包產到戶保駕護航。根據國家政治路線和政治目標以及當前土地政策實施效果及時進行評估、調整和改革,使得我國土地政策在實施的過程中能夠適應社會變遷,保障糧食安全和人民權益。
二是開拓創新促生產。無論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都充分體現了黨對農村土地政策的重大創新,在黨領導下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戶紛紛響應,農民生產積極性明顯提高,通過統分結合的經營體制,使得我國土地政策既體現社會主義性質又能夠充分激發市場活力;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破除了城鄉二元體制的壁壘,活躍了城鄉生產要素,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同等入市,保障了農村群體的權益,促進了社會的公平,有效釋放了農村的生產力;由“三權分置”衍生出來的農業社會服務和專業組織、生產要素交易市場等幫助構建新的農業農村產業格局,是對新發展理念的充分貫徹,破解了農村發展的難題。
(二)堅持立足人民立場
一是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中共一大明確提出“消滅資本家私有制”,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消滅封建地主對農民群眾的剝削,探索適合我國實際和維護人民利益的農民個人所有制的土地政策。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減租減息”土地政策,在緩解國內矛盾的同時,團結一切抗日力量,贏得了抗戰的勝利。充分認識到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在農民無法自主實現土地更大收益時,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三權分置”制度,盤活農村土地,幫助農民最大限度獲得土地財產權,允許農民在承包權范圍內最大限度的自主處置權,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富裕。
二是尊重人民群眾的意愿。恩格斯在《德法農民問題》中指出:“我們根本不能設想用強制的方法去剝奪小農……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馬克思也指出,不能通過“宣布廢除繼承權或廢除農民所有權”來實現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由此在我國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付諸實踐的過程中,充分貫徹其農業合作化的原則和方針;在進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采取自愿互利的原則,充分尊重農民群眾意愿;在土地流轉過程中,也根據農民意愿進行有償流轉。
三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有了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的沖鋒在前,才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積極效應。也正是黨對人民首創精神的認可和支持,才使該項制度得以充分貫徹實施。
(三)調整社會基本矛盾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在實踐中,需要不斷地調整,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在土地農民所有制關系基礎上形成的零碎化經營模式,限制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經過黨和國家的不斷探索、調整,對農村土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形成了一定意義上的合作經營,匯集了更多的生產資料,促進了生產。正是在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不斷調整、對當前政治格局發展情況的清醒認知下,黨通過變革土地政策,緩解了人地矛盾,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
三、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土地政策變革的啟示
(一)探索馬克思土地產權理論中國化實現路徑
馬克思土地產權理論包括土地產權權能理論、土地產權結合與分離理論、土地產權商品化及配置市場化理論、地租理論四個部分,是推動土地產權明晰和要素市場化的重要理論基礎[18]。黨的二十大著眼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提出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破除妨礙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制度壁壘,促進發展要素更多下鄉的新要求。
第一,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土地產權理論。立足國際國內雙循環發展格局,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在推動要素組織內部流動的過程中,推動跨區域生產和要素流動。第二,尋求地租多種實現形式。現代意義上的地租不再是指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更多表明的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所屬關系,推動農民實現財產權的多樣實踐。第三,形成完善的法規制度保障,在推動農民土地承包權退出補償機制、要素流動市場準入原則等方面,現實的法規還存在不足和空缺,需要發揮黨和國家的引領作用,實現政策和法規的一致。
(二)鞏固馬克思合作化理論實踐成果
在馬克思、恩格斯農業合作化理論的指導下,我國形成了土地國有化對推動形成社會主義的重要性認識,形成了對農業進行規模化經營利弊認知和自愿、示范與社會幫助的農業合作化的原則與方針,新階段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需要鞏固其實踐成果。
第一,鞏固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該體制是對效率與公平進行平衡的重要手段,不僅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保障了農民權益,同時還展現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優越性。第二,鞏固適度規模經營成果。黨的十九大、二十大明確提出要推進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鞏固現有土地流轉、出租、轉讓形成的規模經營行為,并施以法律保障,實現維護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第三,促進產業化經營,實現經濟組織多元化。在城鄉要素流動和規模經營的基礎上,形成人才、產業的集聚效應,發展鄉村特色產業,發展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三)以匹配的土地政策助力社會協調發展
以前農業的功能被局限于產品、市場、要素和外匯等經濟功能,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應該注意到土地政策引發農業變革帶來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態文明和社會多方面的轉變。
第一,“藏糧于地,藏糧于技”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掌握發展主動。“洪范八政,食為政首”①“民以食為天”等人們耳熟能詳的話語,充分證明了糧食安全的重要性,我們要以匹配的土地政策助力社會穩定,增強糧食安全保障,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抵御國際市場沖擊。第二,國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載體。土地具有涵養水資源,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作用,制定土地政策需要注意增加土地可利用幅度和土地質量,充分發揮土地在水土保持、氣候調節中的作用。第三,農村蘊含著巨大的消費市場。充分發揮農村特有的地域優勢,發展特色產業,開發潛在價值,促進當地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四、結語
黨的土地政策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時期,為了適應生產力發展和實現相應政治目標,需要不斷對其進行調整。我們要始終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正確看待黨的土地政策發展史中的階段性、臨時性、過渡性政策,分清歷史主流和支流,避免以偏概全,避免對土地政策的錯誤認知。充分認識到黨的土地政策是我國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國家的經濟、文化、生態有著密切聯系,應該給予高度的重視,適時進行調整。
當前,在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要加強對馬克思土地相關理論的學習,深入探索更多的組織實現形式,形成配套法律制度和價值觀念,實現要素交易市場常態化、合法化、標準化,在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中實現黨的土地政策的最大價值。
注釋:
①洪范八政:出自《尚書·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參考文獻:
[1]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增訂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664.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延安時期黨的重要領導人著作選編: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524.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3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382-383.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184.
[6]顏杰峰.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的歷史回顧及其啟示[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2(2):99-109.
[7]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8.
[8]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6.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3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246.
[10]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6.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6:425.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159.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709.
[15]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的意見[N].人民日報,2019-11-27(1).
[16]易振龍.中國共產黨農村土地政策的百年發展歷程及其經驗啟示[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3):31-40.
[17]曲福田,馬賢磊,郭貫成.從政治秩序、經濟發展到國家治理:百年土地政策的制度邏輯和基本經驗[J].管理世界,2021(12):1-15.
[18]劉敏.馬克思土地產權理論與我國農地制度改革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5.
作者簡介:洪鷺敏(2000—),女,漢族,江西撫州人,單位為南寧師范大學,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責任編輯:馮小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