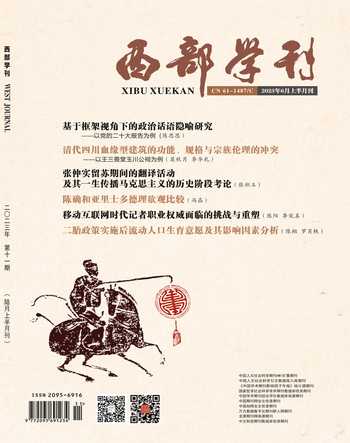“天人合一”視域下的消費主義與生態危機
陳宗杰 史育華
摘要:當代的消費主義從本質上講依然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從屬于資本邏輯,鼓勵人們在消費中實現自身的價值,它的基本信條就是只有消費才能實現人生意義,這樣的人生意義在實現的過程中,會讓人們近乎于貪婪地追求物質財富,其后果必然帶來整個生態系統的全面崩潰。我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人們走向以修身為本的“內向型超越”,讓人們知道物質方面的超越是有極限的,對內在人格與人生的德行、境界與智慧的重視應甚于對身外之物的數量增長和質量精美的重視,只有實現這樣的轉變,人類社會才有可能實現可持續性發展。
關鍵詞:“天人合一”;消費主義;生態危機;內向型超越
中圖分類號:B82-053;B82-05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3)11-0052-04
消費主義產生于十九世紀后半期,于二十世紀初盛行于西歐,后伴隨著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傳播,成為一種新的生活理念與生活方式。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提高,消費主義在我國的影響日益擴大,并繁衍出了多種消費方式。這種消費理念與生態文明所倡導的消費觀念格格不入,會加劇生態危機,不利于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因此,提倡我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緩解消費主義所內生的焦慮,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成為當前一項極為重要而迫切的任務。
一、資本邏輯——消費主義思潮的意識形態根源
消費主義從來不是一個單獨的概念或者浪潮,更與個人的自律精神無關,其本質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強大變種,是資本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更是一種全新的、扭曲的宗教,通過拜物的形式許諾下一切美好,讓人只能看得見貨幣的關系,而看不到人的本質,并通過這種方式去壓制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因此,從這個角度上看,脫離資本和資本主義這個背景后,僅僅討論消費主義的內涵、危害以及解決方案是毫無意義的。消費主義的關鍵點從來都不是商品和消費本身,它是從屬于“資本邏輯”的意識形態,是資本不留余力進行自我增殖的必然產物,就如同福斯特所指出的那樣:“消費主義的價值傾向是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客觀邏輯相一致的,消費主義適應了資本增殖的需要,也是資本增殖的一種主動的文化策略。”[1]它的外在雖然表現為一種特定的文化現象,但究其本質而言卻是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
與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和新儒學等高度概括、理論化的社會思潮不同,消費主義沒有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沒有理論代言人,是一種感性化的意識形態。它以大眾文化產品為載體,不斷為民眾制造虛假的需求,并通過大眾傳媒進行宣傳,將消費演繹成為每個人都要追求的目標,簡而言之,就是鼓勵人們在不斷消費中實現自身價值, 用消費水平的高低標識自身價值的實現程度。究其本質,不過是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需求而已。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專門論述過資本家想方設法地制造消費者的需求從而攫取利潤的丑惡行徑:“工業的宦官迎合他人的最下流的念頭,充當他和他的需要之間的牽線人,激起他的病態的欲望,默默盯著他的每一個弱點,然后要求對這種殷勤服務付酬金。”[2]252-253
此外,浸淫著消費主義文化的大眾文化將社會大眾裹挾進娛樂的漩渦,在人為制造的“消費場所”——購物廣場、娛樂會所、高級餐廳里,被標準化、程序化的流水線生產剝奪了自主性、自由和快樂的工人們,在這些場所宣泄著工作中的各種制度對人性所造成的壓抑,在消費中踐行著自主選擇權。之所以社會大眾會被剝奪自主性就在于消費主義的背景是工業文明,它追求標準化,必然會對工人的個性進行壓制,但由壓制個性引起的異化感會在消費過程中被消費產生的虛假滿足感所消解,在這樣的虛假滿足感中重新恢復了作為資本增殖的必然要素——勞動者的肉體狀態和精神狀態,從而使人們可以投入到下一輪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人們不再關注資產階級統治社會的方式,也不再關注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平等,忽視了同階級人民真正的需求。但就算在消費中,社會大眾的需求是時時刻刻被偽造的。物品的相對豐富也僅僅是相對而言,就像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所指出的:事實上“財富和產品的大量出現是不會取得海平面一樣的平衡的”[3]。資產階級利用廣告、公共關系和市場營銷,甚至利用整個泛文化行業對消費主義起到“潤滑劑”作用,通過廣告來制造焦慮,塑造出人們所必需的消費對象。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2]180這種意識形態的虛假性、隱蔽性的關鍵就在于夸大了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共謀、共享。
消費主義將實際社會關系中的地位不平等以及階級的對立,通過“自由”“自主”的消費觀簡單地概括為金錢之間的差異,試圖彌合階級的對立。因此,消費主義是更加意識形態化的意識形態,它標志著資產階級對廣大勞動者的剝削,從赤裸裸的單向灌輸轉向了更為隱蔽且充滿誘惑性的剝削方式。所以說消費主義從本質上講仍然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雖然將自身包裝成普適性但仍然從屬于資本邏輯。
二、生態危機——消費主義盛行的必然結果
從起因來看,生態危機是人為引發的還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學術界有著諸多觀點。但無論怎么說,生態危機的加劇與人類不合理的生產生活有著高度的相關性。作為西方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思潮之一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就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消費模式是當今社會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根源。其代表人物魯道夫·巴羅明指出,“環境破壞既是由資本主義積累的全球動力驅動的,也是由消費主義驅動的。”[4]
在分析消費主義與生態危機的關系前,首先要辨析消費和消費主義之間的區別。一般的消費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活動之一,適度的消費對經濟的發展起重要的推動作用,對于社會的發展和國家的繁榮富強產生積極的影響。但消費主義這樣的異化消費是一種過度的消費,這樣的生活模式掩蓋了人的基本物質需求和人生意義之間的界限,激勵人們以永不知足的方式追求物質上的滿足,這種典型的“外向型超越”的生活方式,是在現代工業社會中長期居于統治地位的主流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認為自然資源是無止境的,人的物質需求也是無止境的,人類只有不斷地征服自然、擴大消費,才能不斷刺激經濟增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人生的整個意義只能在創造、占有和消費物質財富中得到體現,這樣的價值觀自然而然地把一切的價值都歸納為金錢的價值,把一切的社會進步都歸納為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這樣主流的價值觀會對全球的生態環境和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因為這種“外向型超越”的生活方式的極限就是整個生態系統的承載力,人類生態足跡的過沖必然會導致自然資源的不斷下降,當人類溢出的廢棄物突破地球吸收廢棄物和污染物能力的時候,也就達到了增長的極限,最終生態系統將不可避免地崩潰。因此,在現代社會中消費主義的盛行所帶來的不僅僅是消費的異化,人生意義同樣會被異化,人不知在哪里該滿足,在哪里該不知足,毫無節制地追逐物質上的滿足、經濟的增長以及科技的進步,最終的結果必然會導致生態系統趨于崩潰,人類的生存之基也將不復存在。
消費主義盛行所帶來的結果必然是一種激進的發展主義。所謂激進發展主義指的是發展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相信經濟發展是社會進步與政治發展的先決條件,乃至貧富差距、生態破壞的問題,依然可以通過發展本身來解決,篤信這個方向且否定所有舊有的經驗的做法,就可以稱之為激進的發展主義,這種激進的發展主義同樣也是“科技萬能論”的一種體現。在這種發展模式下,自然界不再是維持人生存的無機身體,而是淪為了被人類任意索取的對象,就如同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邏輯下)自然界才不過是人的對象,不過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認為是自為的力量;而對自然界的獨立規律的理論認識本身不過表現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從于人的需要。”[5]其實,文明與自然之間永遠存在著一種張力,但是人類在消費欲望的刺激下打破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從本質上來說,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面臨的最基本的關系,絕對不能站在自然以外去看待人類的社會,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的產物,準確而言是自然壓迫的產物。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人類歷史無論如何不能僅僅理解成人類本身的歷史,只能被看作自然歷史中比較有自覺性的部分。”從這個角度上看,消費主義思潮所帶來的這種激進的發展主義異化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破壞了人類存在的根基,不利于實現人類的永續發展。因此,要想實現人類的永續發展,緩解當下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人類必須破除消費主義的虛妄,要知道在哪里應該滿足,在哪里應該不知足。
總的來說,消費主義的盛行所帶來的就是人類對物質方面過于貪婪的追逐,一方面,消費主義會讓人類迅速達到生態系統的承載力極限;另一方面,消費主義的盛行會讓人們篤信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必然在發展中能夠得到解決,這樣的一種激進的發展主義早已被生態學、復雜性理論以及耗散結構論所證實,這樣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人類必須超越消費主義,追求真正有意義的生活,從而讓消費真正地服務于需求。
三、“天人合一”——以“修身為本”的內向型超越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思想核心與精神實質。它首先指出了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其次表明人類生生不息,則天、希天、求天、同天的主義和進取精神;第三,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世界觀、價值觀的思維模式的全面性和自新性。錢穆先生認為,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是整個中華傳統文化思想的歸宿,季羨林先生認同錢穆先生對“天人合一”思想重要性的評價,認為它意義深遠,是中華文明對人類社會的偉大貢獻。但就“天”與“人”的內涵,兩位先生的觀念并不相同。錢穆先生認為“天”所指的是天命,而“人”所指的是人生;季羨林先生則認為“天”所指的是自然界,而“人”所指的是人類本身,“天人合一”思想所表達的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在生態環境日益嚴峻的當下,只有這種東方思維才能拯救人類。其實兩位先生的看法都是正確的,兩種觀點是可以互補的,只是側重點不同,季羨林先生側重的是自然觀,錢穆先生側重的則是人生觀。“天人合”一思想擁有著豐富的內涵,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其最基本的含義,換而言之這是其本意,而其他的含義則是由此演變而來。也就是說,“天”的本意就是指的物質之天或者說是自然之天,遠古時代雖然這個“天”有著神學的色彩,但歸根到底是借助“祥瑞”或者“災禍”等自然現象來表達對人類的警告。因此,從“天人合一”思想含義演變的角度看,這兩種觀點是有內在聯系的。通過這兩位先生的觀點,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天人合一”思想對于人生觀的構建,以及在正確認識自然中所起到的價值導向作用。
在當代社會,受到消費主義思潮的影響,有的人無法正確地認知人生的價值導向,最關鍵的是不知向什么地方追求無限。人是一種追求無限的有限存在者,追求無限從某種方面而言就是人生的意義,但是,以何種方式追求無限,追求什么樣的無限,決定著一個人是智慧的還是愚蠢的。一方面,“外向型超越”的價值觀有著本身不可超越的極限,也就是生態系統的承載極限;另一方面,從個人的角度上看,人對物質財富的剛需顯然是有限的,每個人可以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有限度的。因此,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消費主義泛濫所蘊藏的巨大風險。當一個人全身心地擁抱消費主義,甚至可以說是物質主義的時候,他所看到的必然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千般不是,縱使中華傳統文化有些不足之處,但更多的是值得我們肯定和學習的,比如以修身為本的“內向型超越”的生活方式不會導致生態系統的崩潰。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縱然有千般好處,但是有一點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這種消費主義的“外向型超越”的生活方式必然會造成生態系統的破壞,導致人類文明滑向毀滅的深淵。
為了擺脫整個人類文明被毀滅的命運,就要徹底批判“科技萬能論”的謬誤以及依附其上的“消費主義”的虛妄。我們必須拒斥消費主義,并將“資本邏輯”置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制約之下,實現以東方文化的綜合思維模式濟西方的分析思維模式之窮。首先要學習東方人的哲學思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徹底改惡向善,徹底改弦更張。只有這樣,人類才能繼續幸福地生存下去。”[6]歸根結底,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續的,人類必須摒棄消費主義,改變“外向型超越”的生活方式,以“天人合一”思想為指引,構建“內向型超越”的生活方式。唯有當“內向型超越”平抑“外向型超越”時,整個人類文明才是可持續的。
闡發“天人合一”思想,實現對消費主義的祛魅,是一項“闡舊邦以輔新命”的偉大事業,同樣需要我們深層次地去把握“天人合一”思想和“內向型超越”的內涵以及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天人合一”從表面上看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但其不僅僅體現在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更體現的是人如何規范自己的行為,使自己的行為邏輯更加符合天道的運行規律,這是一個不斷歸正自己行為與內心的過程。人在天地之間猶如魚在水中,人既不可能超越于自然之上,也不可能游離于自然之外,人類的一切行動都必須尊重自然法則。“內向型超越”的價值導向則使人們對自我改善的重視應甚于對改造外部世界的重視,對內在人格與人生的德行、境界與智慧的重視應甚于對身外之物的數量增長和質量精美的重視。
四、結語
我們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消費主義僅僅是人生意義的一種而已,這樣的價值觀只能在“資本邏輯”中得到辯護,脫離了“資本邏輯”的話語體系,消費主義的荒謬性就會體現得淋漓盡致。總之,消費主義帶來的“外向型超越”的價值觀毋庸置疑是危險的,全球性生態危機以及生態學理論都表明了這一點,以這種價值觀為導向甚至會造成整個人類文明的毀滅。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的歷史本身是自然和自覺的歷史統一,人并不能改變自然,只能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合理地改造自然。因此,人們必須在尊重自然、認識自然的基礎上合理地對自然進行索取。“天人合一”思想就是這樣的生活方式在哲學層面的凝練與表達,這種生活方式以“天人合一”思想為指引,注重以修身為本的“內向型超越”,將物質財富當作自身生存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全部的人生意義。將精神境界或者說非物質財富的創造當作自己的價值取向,只有這樣,人類社會才能真正地可持久。同樣,借鑒“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加強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實現美麗中國的目標。參考文獻:
[1]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M].耿建新,宋興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2.
[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55.
[4]特德·本頓.生態馬克思主義[M].曹榮湘,李繼龍,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6.
[5]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3.
[6]季羨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56.
作者簡介:陳宗杰(1995—),男,漢族,河北邢臺人,單位為河北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史育華(1978—),男,漢族,河北灤南人,博士,河北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理論。
(責任編輯:王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