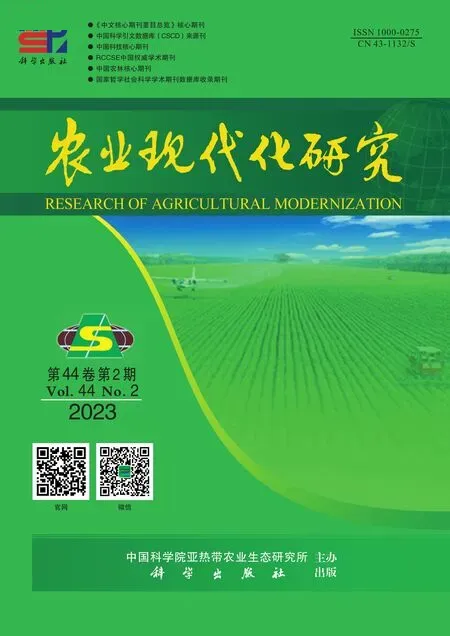“非糧化”種植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一個宏觀比較視角的分析
宋碧青,龍開勝
(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
糧食安全是關乎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問題[1]。隨著城鎮化推進不斷占用耕地,氣候變化加劇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對保障糧食安全敲響警鐘。國家在政策層面對確保糧食安全給予了高度重視,多次強調“合理保障農民種糧收益”,“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但在政策高壓的背景下現實卻是耕地“非糧化”問題依然突出[2]。廣義上而言,“非糧化”指耕地未種植糧食作物的行為,如種植經濟作物、耕地撂荒、挖塘養魚等,狹義上指在耕地上種植經濟作物的行為[3],實質為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的調整。關于“非糧化”的測度學者們傾向使用非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即“非糧化”程度衡量[4-5]。基于《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測算顯示,2016—2019 年全國“非糧化”程度分別為28.58%、29.06%、29.45%和30.05%,“非糧化”呈上升態勢,長期“非糧化”將對國家糧食安全產生危害。如何切實提升種糧農民收益,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是構建糧食安全長效機制的重要抓手,具有現實意義。
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是學界關注的熱點話題。已有學者通過構建糧食生產與收入協調性指數發現:“糧食產量—農民收入”協調性逐年下降,糧食增產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不斷降低[6-8],保障糧食安全與增加農民收入似乎是一個兩難選擇。為破解這一困局,我國出臺了多項糧食補貼政策,但在推動糧食生產進而實現農民增收上仍有較大提升空間[9-10]。而經濟作物種植能夠顯著提高家庭經營性收入,對農民的生計活動調整起到積極作用,并進一步對其他結構性收入產生正向影響[11-12]。現有觀點普遍認為經濟利益驅動是耕地“非糧化”的根本誘因[13],“非糧化”的經營方式能夠獲得更高的農業產出效益[14-15]。據《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摘要》數據顯示,2015—2019 年期間,三種糧食(稻谷、小麥、玉米)年平均凈利潤為-568.20 元/hm2,棉花與兩種油料(花生、油菜籽)的年平均凈利潤分別為-9 001.65 元/hm2和-523.35 元/hm2,種植經濟作物并非必然帶來可觀收益,這一數據與現有觀點相出入。究其原因,現有研究多著眼于單一的收入維度,而農民的種植規模會對不同類型收入產生影響,單從某一收入維度去評論農民增收與否有失偏頗。此外,當前關于農作物種植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研究多為定性分析,缺乏實證檢視,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收入的具體作用效果尚待進一步論證。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從農民收入結構視角出發,以2000—2019 年我國31 省(區、市)(不包括港澳臺)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和農民收入為考察對象,揭示并比較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收入的具體作用效果。此外,依據糧食主產區和非糧食主產區進行區域劃分,考察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收入影響的區域異質性。研究結果將對從宏觀層面審視“非糧化”問題,提高農民收入提供經驗參考。
1 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影響農民收入的理論分析
農作物種植規模是影響農民收入的重要因素。按收入來源將農民收入劃分為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四類,其中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存在直接影響。農民工資性收入變化主要源于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因素[16],但種植規模可能影響到農民勞動時間配置,故對工資性收入也存在一定影響。農民通過顯化土地資產價值而獲得財產性收入[17],與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關聯不大。因此,本文重點關注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的作用。
1.1 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與農民經營性收入
近年來農資價格、勞動力價格、土地流轉租金等不斷上漲,農業生產投入成本增加,擠占利潤空間。但與此同時,農業機械化程度不斷加深、農業社會化服務趨于完善,農業機械化對勞動力要素起到替代作用,可以降低人工投入成本,使得農業生產取得規模經濟效益[18-19]。且隨著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傳統農業理論中機械化需要相應的耕地規模作為配套的限制逐漸被打破[19-20],機械化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越來越普遍。在農業勞動力剛性約束持續增強背景下,糧食作物相較于經濟作物更易于進行機械化作業[21],獲得規模報酬。基于以上分析,糧食作物種植易于與機械化生產相匹配,獲得規模經濟效益;經濟作物的農業機械化配套程度雖弱于糧食作物,但一般而言其單位面積收益更高,故擴大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經營性收入增長均起到正向促進作用。
1.2 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與農民工資性收入
農民將其勞動時間在從事農業生產和非農業生產間進行分配,在不考慮其他要素配置時,擴大種植規模意味著更多的農業勞動時間投入,這會降低工資性收入份額。但隨著我國土地流轉速度不斷加快,通過農地流轉釋放大量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加之農業機械化的大量普及對勞動力要素起到替代作用,進一步促進勞動力非農轉移,農民逐漸由以往單純從事農業生產演變為兼業經營形式,獲得工資性收入[22-23]。因此在當前的要素配置現實情境下,擴大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有助于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
1.3 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與農民轉移性收入
農民轉移性收入主要來源于一系列農業補貼等政府財政轉移支付。自2004 年起,國家陸續出臺糧食生產的價格支持和補貼政策,包括四項補貼、政策性農業保險、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政策等多項措施,其中四項補貼包括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資綜合補貼。雖然糧食直補的補貼形式在各地有所差異,但總體上與糧食播種面積相掛鉤,即糧食作物種植面積越多獲得的糧食直補越多。農作物良種補貼的種植范圍涵蓋主要糧食品種和棉花、油料等經濟作物,補貼標準依據種植面積折算。農機購置補貼則是對購置農機用于農業生產的農民進行經濟補償。農資綜合補貼的發放對象主要為種糧農民,根據農資市場價格走勢和農業生產形勢,進行動態調整補償。因此,不論是增加糧食作物或是經濟作物種植規模,都可促進農民轉移性收入增長。
2 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為盡可能確保數據完整性,本研究采用我國31個省(區、市)(不包括港澳臺)2000—2019 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其中,農民各類收入、糧食作物播種面積、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鄉村人口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農業機械總動力、農作物成災面積和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農民受教育年限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數和就業人員總數數據來源于各省(區、市)歷年統計年鑒,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地區生產總值指數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地方財政農林水務支出數據中2000—2006 年數據來源于《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2007—2019 年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個別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均值法等方法補齊。
2.2 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本文被解釋變量是農民收入,用農村居民收入來反映,具體包括農民總收入、農民經營性收入、農民工資性收入和農民轉移性收入。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收入統計口徑變更,從《中國農村統計年鑒》獲取的農村居民收入數據中,2000—2013 年統計口徑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013—2019 年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借鑒王麗納和李玉山[24]的研究,由于兩者統計口徑差異較小,2014—2019 年的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此外,為消除通貨膨脹影響,采用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調整,以2000 年為基期進行價格平減。
2)解釋變量。本文以糧食和經濟作物年播種面積反映農民的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其中經濟作物播種面積根據農作物總播種面積扣除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獲得。
3)控制變量。基于已有研究[25-28],本文引入農業機械總動力、勞動力轉移、自然災害、農民受教育程度、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支農水平作為控制變量。其中,各省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將各種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計算平均數得出,各省份人均GDP 和人均農林水務支出同樣以2000 年為基期進行折算。上述各變量含義及描述性統計詳見表1。

表1 變量含義及描述性統計Table 1 Variable def 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2.3 計量模型設定
根據前述理論分析,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考察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收入的具體作用效果,一方面可避免遺漏省際層面的不可觀測變量而引發的內生性問題,另一方面可控制不隨時間變化的不可觀測因素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回歸模型如下:
式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Yit表示省份i在t年的農民收入情況,細分為農民總收入、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Xit為核心解釋變量,包括糧食作物種植規模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Zit表示控制變量,di為省份固定效應,νt為年份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考慮到采用取自然對數的方法能夠降低潛在異方差干擾,對部分離差較大的連續變量取自然對數,將農民四類收入、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農業機械總動力、自然災害、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支農水平變量作自然對數處理。
需要說明的是,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結構也可能對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產生影響,已有學者關注到這一影響路徑,如李婭婭和趙小風[29]、何蒲明[30]、高曉燕和杜寒玉[31]等,這種雙向影響關系會導致模型估計產生內生性問題。為提高估計結果的可靠性,參考已有文獻引入滯后項以處理內生性問題的方法[32-33],本研究選取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的一階滯后項、二階滯后項作為相應的工具變量,采用面板工具變量法估計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并對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進行檢驗。
3 結果與分析
3.1 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與農民收入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與農民收入存在相關關系。2000 年我國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約為10 846萬hm2,2000—2003 年經歷短暫下滑后呈現穩步上升趨勢,2016 年達到11 923 萬hm2,而后逐年下降,2019 年全國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為11 606 萬hm2。經濟作物播種面積在2004 年經歷短暫下滑,而后從2009 年開始呈現較緩慢的上升趨勢。經濟作物播種面積由2000 年的4 784 萬hm2增加至2019 年的4 986 萬hm2(圖1)。
同一時期,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2000年人均2 389 元上升至2019 年的16 021 元。農村居民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均整體呈上升趨勢,其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分別由2000 年的人均1 513 元和人均744 元增加至2019 年的人均5 762 元和人均6 584 元,2015 年工資性收入首次超過經營性收入,成為農村居民收入的第一大來源。轉移性收入由2000 年人均84 元躍升至2019 年人均3 298 元(圖1)。由于農民不同類型收入的變動趨勢有所差異,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與不同類型收入變化的關系存在異質性,下面將詳細計算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與農民收入的數量關系。
3.2 工具變量有效性分析
本研究數據為全國31 省(區、市)(不包括港澳臺)20 年的面板數據,參照Bai[34]的研究,由于數據的樣本截面數多于時間點數,屬于短面板,不需要進行單位根檢驗。在引入工具變量后,需要判斷工具變量的有效性。理論上而言,由于農民當期的種植決策可能依賴于往期的種植選擇,所以引入的工具變量糧食及經濟作物種植規模的一階滯后項、二階滯后項與當期種植規模在理論上具有顯著相關性。雖然種植規模的當期值與干擾項可能存在相關性,但其滯后項卻不會與當期干擾項相關。為證明所選取工具變量的有效性,本文分別進行工具變量不可識別檢驗(LM 檢驗)、弱工具變量檢驗(F檢驗)以及過度識別檢驗(Hansen 檢驗)。結果顯示,不管是全國層面或者分地區層面,均通過工具變量不可識別檢驗,Kleibergen-Paap rk LM 統計量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即強烈拒絕工具變量識別不足的原假設;均通過弱工具變量檢驗,即拒絕是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Kleibergen-Paap rk WaldF統計值大于Stock-Yogo 檢驗10%水平上的臨界值19.93;基本通過了過度識別檢驗,即總體接受工具變量外生的原假設。上述檢驗結果證實所選擇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
3.3 全國層面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分析
從表2、表3 的回歸結果可知,全國層面上,種植糧食作物能夠顯著增加農民總收入和轉移性收入,顯著性水平均為1%。糧食作物種植規模每擴大1%,農民總收入增加0.065%,轉移性收入增加1.011%。農民轉移性收入增加與近年來不斷投入的糧食補貼以及相關的農業補貼有關,國家為穩固糧食生產對種糧農民給予包括農業支持保護補貼、糧食生產者補貼等多項轉移支付。而與糧食種植最直接相關的經營性收入回歸結果卻不顯著,其系數符號為負值。說明從整體上看,種植糧食作物并未帶來可觀的農業收益,農民總收入增加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轉移性收入彌補了經營性收入損失。

表2 糧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收入影響的檢驗結果Table 2 Impacts of grain crop planting scale on farmers’ income

表3 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收入影響的檢驗結果Table 3 Impacts of cash crop planting scale on farmers’ income
全國層面的回歸結果表明種植經濟作物對農民總收入、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產生顯著正向影響。經濟作物種植規模每擴大1%,農民總收入增加0.054%,經營性收入增加0.064%,工資性收入增加0.196%。種植經濟作物能顯著增加農民經營性收入是由于經濟作物往往有著更高的單位面積收益,這也是“非糧化”屢禁難止的根源。種植經濟作物對農民工資性收入具有促增作用,可能的解釋是與近年來不斷推進的土地流轉有關,一部分農民將土地流轉給其他經營主體,自身從事非農業生產或者兼業經營,同時土地規模化經營利于開展農業機械化服務,促進勞動力非農轉移,增加工資性收入。此外,通過對比回歸系數可知,擴大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均能促進農民總收入增加,且兩者的促增程度相似,這意味著落實防止耕地“非糧化”相關政策,矯正農民非糧種植行為是可行的,并不會對農民總收入增加帶來不利影響。
控制變量方面,增加農業機械總動力投入能夠顯著提高農民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顯著性水平均為1%。這表明機械化的使用能夠帶來作物種植的規模經濟效益,且能夠對勞動力要素起到替代作用,促進勞動力轉移,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勞動力轉移對農民經營性收入具有正向影響,顯著性水平均為10%。這一結果說明農民經營性收入隨著勞動力轉移程度加深而上升,間接表明存在農業機械化和勞動力轉移的要素替代關系,農業生產取得規模經濟效應,表現為經營性收入的增長。其余控制變量回歸系數均符合理論預期,在此不做過多描述。
3.4 分區域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分析
為進一步考察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收入影響的區域異質性,本研究按照糧食主產區(包括黑龍江、河南、山東、四川、江蘇、河北、吉林、安徽、湖南、湖北、內蒙古、江西和遼寧)和非糧食主產區進行區域劃分,具體的回歸結果如表4 和表5 所示。

表4 分區域糧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收入影響的檢驗結果Table 4 Impacts of grain crop planting scale on farmers’ income in diff erent areas

表5 分區域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收入影響的檢驗結果Table 5 Impacts of cash crop planting scale on farmers’ income in diff erent areas
不同于全國層面的回歸結果,糧食主產區內糧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增加起到顯著的正向作用,顯著性水平均為1%。糧食作物種植規模每擴大1%。農民經營性收入增加0.277%,工資性收入增加0.624%。而非糧食主產區內擴大糧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經營性收入未有顯著影響。這一結果與李紅莉等[28]研究結論相呼應:糧食主產區的設立對農民經營性收入有著顯著的促增效應,糧食主產區內土地規模化程度較高,土地集中連片,易于獲得規模經濟。主產區內種植經濟作物對農民結構性收入未有顯著影響。需要注意的是,在糧食主產區內不論種植糧食作物或經濟作物,對農民總收入的影響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還需出臺相關政策助力農民增收。
在非糧食主產區,擴大糧食作物種植規模能夠顯著增加農民總收入和轉移性收入,顯著性水平均為1%,農民總收入增加源于農業補貼等轉移性收入增長。增加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對農民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和總收入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顯著性水平均為1%。2000 年糧食主產區的“非糧化”程度為29.42%,2019 年降低至22.41%,而非糧食主產區“非糧化”程度由2000 年的32.51%上升至2019 年的43.93%,非糧食主產區“非糧化”程度存在蔓延趨勢。且對比非主產區農民各類型收入的回歸結果可知,糧食或經濟作物種植規模雖對農民不同類型收入存在異質性作用,但均能促進農民總收入的增加。后續應在非糧食主產區有序開展“非糧化”整治活動,如對經濟作物清理騰退、耕地復墾等,擴大糧食作物種植規模,遏制耕地“非糧化”增量。
4 結論與政策啟示
4.1 結論
本文從理論層面闡述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收入的具體影響機制,采用中國31 個省(區、市)(不包括港澳臺)2000—2019 年的面板數據,探討了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收入的具體影響,并基于糧食主產區和非主產區進行區域異質性分析。考慮到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借助面板工具變量法開展實證分析,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全國層面上,擴大糧食或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總收入增加均起到正向促進作用,這表明種植糧食作物也“有利可圖”,農民種糧與增收可以兼得。且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總收入增加的作用力相似,這意味著當前防止耕地“非糧化”的政策安排是切實可行的,并不會對農民增收帶來不利影響。
2)從收入結構看,全國層面上,糧食作物種植有利于農民轉移性收入增長,但并未帶來農業收益的提升,農民總收入增加一定程度上源于農業補貼等轉移性收入彌補了經營性收入損失。經濟作物種植有助于農民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增長。
3)區域異質性分析表明,糧食主產區內,種植糧食作物對農民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增加存在顯著正向作用,種植經濟作物對主產區內農民各類收入未有顯著影響。在非糧食主產區,擴大糧食作物種植規模能夠顯著增加農民轉移性收入和總收入,擴大經濟作物種植規模對農民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和總收入具有顯著正向作用。說明糧食主產區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取得了較好的農業經濟效益,但對總收入的促增效果并不顯著,因此還需出臺相關政策助力主產區內農民增收。同時結果表明在非糧食主產區內開展“非糧化”整治不會對農民收入帶來不利影響。
4.2 政策啟示
1)推動實施差異化的“非糧化”整治措施。對于“非糧化”問題的整改不可冒進、一刀切,以免損害農民的合理利益。在保障糧食供應基礎上兼顧當前居民膳食結構轉變趨勢,合理規劃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種植區域,實施差異化的耕地“非糧化”整治措施:對于破壞耕地耕作層的行為,應嚴令禁止并恢復原狀;對于一些特色農產品產區,應因地制宜劃定經濟作物生產范圍;位于糧食主產區的優質耕地要確保糧食種植面積不減少,嚴控違法改變耕地用途行為。
2)優化糧食補貼規則,提高糧食產品附加值。優化現有的農業補貼政策,提高糧食生產補貼的瞄準性,設置分梯度、差異化的補貼規則,確保“誰種糧,誰受益”,降低農民糧食種植的投入成本。推動糧食產業綠色高質量發展,提高糧食產品附加值,通過市場交易機制使優質的糧食產品獲得優價,助力農民經營性收入增長。
3)有序落實非糧食主產區的糧食生產責任。當前需嚴控非糧食主產區“非糧化”蔓延趨勢,有效落實“非糧化”整治措施。科學制定非糧食主產區內各省份糧食種植規模底線,有序引導各類經營主體開展糧食生產活動,并對其落實績效進行監督考核。進一步探索糧食主產區與非糧食主產區的利益補償機制,謀劃好全國糧食生產一盤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