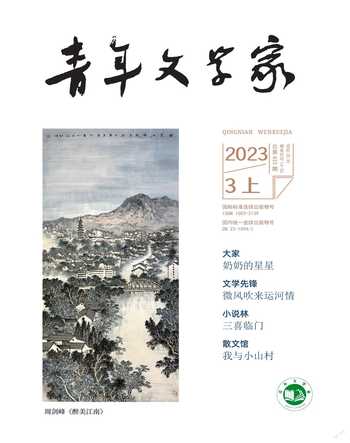尋江面上的時空
雷茜杰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似水流年,世人心中,時間與流水有著奇妙的共性,默默無聞、至柔至善,卻又足以承載萬物,而空間就像是江河里的船舶,小舟里發生著令今人追憶不已的舊事,重復著,重復著……
那一個個時間點,在江濤與萬古不變的風里,順流而下。舟楫搖搖,清風徐徐,倘若有岸上的人發現了它們,就會驚異地發現,那是一個個曾經,一個個時空。
山杏還艷,桐花萬里,春景當時。卸去讀書與考試的目的,我重拾當年的書本,本著要懷思那段時光,打開了書本,是蘇東坡的詞《定風波》。上面密密麻麻記滿了當時老師說的感想與重點,“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喃喃中,我閉上了眼睛。原本被緊閉的窗戶阻擋在室外的雨聲,漸漸空靈、遼遠,似從天邊傳來。我的眼睛適應了黑暗,又隱隱約約中透著一股綠意,耳畔雨滴拍打的聲音也漸漸清晰,空氣中是泥土和新雨的味道,清冽中帶著竹質的敦厚。我是誰?或者說,現在的我是誰?
沙湖道上的行人匆匆忙忙,怨聲載道,這場雨來得猝不及防。嘈雜聲中,有一人走得很慢很慢。他穿著草鞋,卻步履堅定,和那些手忙腳亂的行人格格不入。他頭發灰白,卻身姿如竹,手持竹杖,布衣被大雨淋濕,但他甚至還帶著解脫、自由的笑意,這使我永遠無法將“狼狽”一詞用在他的身上。直覺告訴我,他是蘇子瞻,一定是。我追上他,“蘇學士!”他腳步一頓,回頭看我。我這才注意到,我仿佛融入了此情此景,我變成了一個徹徹底底古代面貌的人。
“烏臺一事……”我踟躕開口,他卻了然。我亦步亦趨跟在他的身后,時不時用袖子拂去臉上的雨珠,他側目與我交談:“你看,下雨不見得一定是那么不好的,為什么不轉念一下呢?”頓了頓,見道路崎嶇,他將竹杖換了只手,嘆息一聲,聲音在暴雨中不甚清晰,像是囈語:“人生也沒有什么不好的,失落過去后,竹杖也好,騎馬也罷,此時此景,竹杖難道不比騎馬輕松嗎?都是自己的選擇罷了。”
沙湖道將盡,竹葉婆娑,他駐足回望,雨霧中不見其容貌,忙忙碌碌的人在人間,他亦在人間。晴天是他的人生,下雨也是他的人生,蕭瑟處往往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功課。“不必為我惋惜,我走過的人生都是我的,我時常提醒自己,生命里,我喜歡的和不喜歡的都是自己生命里最珍貴的部分,與自己和解,才會釋然。”他說。
雨漸小,林間霧氣氤氳。先生抬頭,我這才看見,一直忽視的天空已經是云破天光降,身邊傳來吟唱的聲音。蘇先生腳步輕快,竹杖輕提,向前走去……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在我的人生里,他是一個從紙上走到現實里的人,抑或連紙頁的平面都遮擋不住的存在于人世間的人。我靜靜佇立在沙湖道間。我無法動了,無法提步上前,我與他的遇見隨著《定風波》一詞的結束而結束了。我見到了誰?他是心中的我,還是當年的蘇軾,還是《定風波》中的蘇子瞻呢……
彼時,明空如洗,云消雨霽。人生有涯,人終將逝去。生命也會是歷史上的一瞬定格,存在于歷代史官的筆記里,存在于百姓口口相傳的故事里。生命當真逝去了嗎?或許吧,但我始終相信,思想無涯。或許,我們的生命無法如長江之無窮,但是今人依舊可以以精神游弋千古。當有那么一刻,兩個思想可以同頻共振,我們或許可以通過那尚有余溫的文字見到他,重回那個時空,去實現瞬間的交集。
何曾得見,屈子投江,“長太息以掩涕兮”之時,悲憤的長嘯;何曾得見,陶潛歸去,“采菊東籬下”時,是否對南山懷有一絲渴望;何曾得見,太白捉月,吟嘯間是否還在喃喃“大鵬一日同風起”的理想;何曾得見,稼軒“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的夢想;何曾得見,楊慎一壺濁酒的笑談……
悠悠長風,萬古不絕,生命已然沉寂,思想依舊泛起波瀾。作為現世的今人,是否能駕一葉之扁舟,尋江面上的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