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樹
誰最中國
曾經看《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書里的奇跡蘋果受自然養育長大,切一半,放置兩個月居然還不會腐敗,禁不住就想嘗一口這原生長大的蘋果。
書里的木村阿公,一生只為做成一件事,便是致力于種出不打農藥的蘋果樹,堅持了9年終于守候到蘋果花開。有人說全憑阿公的堅持和追求,才讓這自然山林里的樹長大開花結果,讓這無農藥參與成長的樹,結出了不會腐敗的蘋果。但木村說,這不是我的努力,而是樹的努力。
樹的努力,這句話在我心中激蕩很久。
是啊,在無人的山野里,樹在自然山林里,深情地埋伏于大地,向土地里扎根,積蓄著力量去高擎天空,最終也能染盡一片山林。
木村將自然的土壤還給了蘋果樹,“蘋果樹每次掉葉子都會長出新葉子,一次次地掉葉子,一次又一次地長出新葉子。即使生了病,仍然要活下去”。這傻氣的話語里藏著樹木本真的模樣。在書中,讀到他每每失敗后重新栽種,總會為他的堅持而淚目,但回頭想想,又何嘗不是為樹的努力感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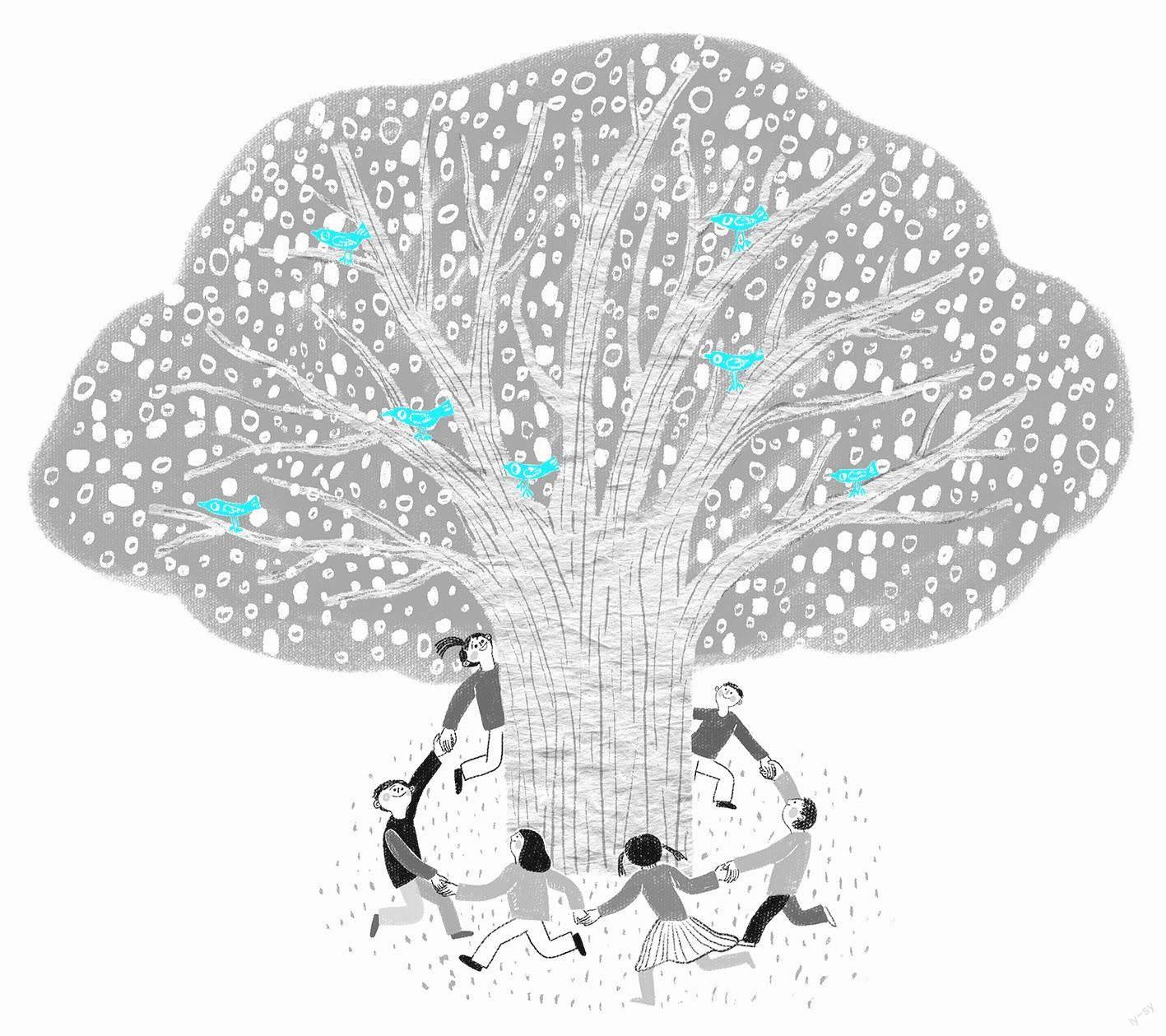
不由得想起一部日本紀錄片《人生果實》,男女主人公修一和英子是一對夫妻,選擇深居于日本高藏寺新城一隅的林間書屋,在這里他們栽植了上百種樹木蔬果。這些樹結下的果實在年復一年的醞釀里,成為四季里的三餐。他們在這深林之間,侍弄園子,照顧花木蔬果,周圍圍繞著各種各樣的樹木,待秋天結果。英子形容這種日子,每天都是小陽春,安安穩穩的愜意。
任其自然而然長大,風吹葉落,落葉堆肥,滋養大地,樹木新生,生活就在其間一點點被豐滿。
古時,大多文人墨客會在自家小院種下一棵樹,作為近時陪伴和身處遠方的寄托,成為一份心安依存的憑借。
白居易“手栽兩松樹,聊以當嘉賓”,他在尚平實、通俗的生活里,于出任揚州處的院里,手植兩棵松樹,將其作為寂寥日常的一份安慰,也是一份堅實牢靠的陪伴。而兩棵松樹也越來越像他,不懼風雨,在地從容。一如白居易堅定地走著新樂府運動的改革之路。
歐陽修離開揚州轉任潁州,當送劉原甫出任揚州時,不禁想起曾任揚州知府的時光,寫下“手種堂前垂柳,別來幾度春風”。堂前的手植楊柳,見證過自己作為“文章太守”的快意日常,久久難忘。一棵垂柳留下來的是歐陽修的恣意人生,在揚州扎根生長,將他的瀟灑駐足。
還有寫《種柳戲題》的柳宗元,于柳州種下了一棵柳樹,與樹一同化作往事。“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種柳戲題》中他一改往日嚴肅的姿態,變得柔軟可戲。手植柳樹化作相思追念他處,在此地所留存的故事,作佳話供世人笑談,足以聊慰人生。
我們總是說植樹和樹人,養樹即養人,一棵樹是映照,是陪伴,是一個人的心安之所,是一個家族綿延不絕的見證。
感知到樹的力量的人,總想走進去被其環抱在懷,是擁抱安心,亦是擁抱自我。或許我們本就是一體,神話傳說里盤古的毛發化身為樹木花草,說不定樹里面還殘留著上古時期盤古的生靈。人如樹,樹如人,獨立且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