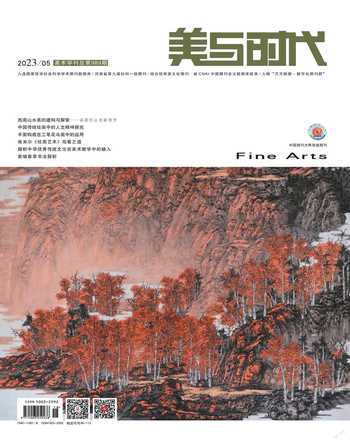米芾《春山瑞松圖》藝術風格賞析
摘 要:關于《春山瑞松圖》的品鑒,以作者米芾生平活動和特性為起點,結合作品的畫技、構圖和意境進行多角度賞析,進而提出該畫畫技具備米氏落點法特色,多用米點皴畫法,色彩巧妙,富含生機,構圖層次豐富,意境彰顯個人順自然合乎“道”的追求,呈現平淡純粹的精神境界。
關鍵詞:米芾;《春山瑞松圖》;畫技;意境
米芾是我國著名書法家、畫家以及書法鑒賞家。相比于其書法作品成就斐然,繪畫作品雖未廣為傳播,卻深刻展現著其個人特性和精神追求。本文以《春山瑞松圖》為主要對象,根據圖中詳細內容、畫法技巧、構圖思考等,并結合作者生平經歷中對平淡的崇尚而分析意境,進行全面賞析。
一、米芾的生平及創作背景
米芾初名黻,字元章,號鹿門居士、襄陽漫士、海岳外史、溪堂居士、無礙居士,湖北襄陽人,祖籍太原,北宋書法家、畫家、書畫理論家。宋徽宗召為書畫學博士,曾官拜禮部員外郎。米芾一生無心于政治作為,而沉醉書畫。其生于皇祐三年(1051年),從小與書法為伴,年僅十歲便可碑刻。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隨其母前往京都汴梁,并于兩年后獲賜校字郎一職。元豐五年(1082年)去往黃州拜訪蘇軾,開始推崇魏晉書法。其常常“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觀其《自敘帖》大概可知其用功頗深。或許正是源于對書法繪畫的深刻喜愛,其成就斐然,成為我國著名書法家、鑒賞家、畫家。大觀元年(1107年),米芾任職淮陽軍知州,卒于任上,享年五十七歲。
縱觀米芾一生,三點尤為突出。首先,米芾好潔成癮。《南宮舍人米公墓志》記載,其“性好潔,置水其傍,數颒而不帨。未嘗與人同器服”。此外,米芾常常要清洗巾帽,哪怕是稍有灰塵,也是洗過才可佩戴。并且每同客人告別后,也需洗滌坐榻,方覺舒適。而其性格方面的脫俗也從其幼時可看出,其打扮奇異,行為與人不同,被稱為“米癲”。后世傳稱米芾有嚴重的潔癖、書畫癖、石癖等。正因如此,米芾憑借迥異的風格,在書法繪畫領域中,敢于持批判態度,向前人作品提出疑問。盡管在同時代有人認為米芾帶有狂傲不羈的不良特征,但正是米芾對自身書法繪畫技藝的投入和自得,對各作品具備的獨特自身感知特性,使得其個人作品渾然天成,自成一派,嚴謹細致又不乏灑脫奔放。在我國書法史上,米芾與蘇軾、黃庭堅、蔡襄并稱“宋四家”。
其次,米芾精通古玩鑒賞,一旦碰見古玩書畫便愛不釋手,并十分渴求獲取。此處可于其兒子米友仁的描述中看出:“所藏晉唐真跡,無日不展于幾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并且每當夜晚降臨,米芾便將這些晉唐真跡們收于小盒中,放置枕邊,方可安眠。此外,米芾的《畫史》也對我國繪畫歷史發展有重大影響。米芾在其中著重表達了對徐熙水墨花鳥的欣賞、對黃筌等人的貶低,以及對吳道子等人繪畫技巧的贊揚和其繪畫作品意蘊缺失的嘆息。由此不難看出,米芾鑒賞書法繪畫的一個明顯標準便是意境。
最后,米芾最為吸引后人的便是其書法繪畫作品,并且相較于繪畫,其書法作品受到普遍歡迎。董其昌評價米芾書法“宋朝第一”,并認為其有著高于蘇軾的水準。同樣,蘇軾自身也贊揚米芾書法超凡脫俗,堪比“鐘王”。黃庭堅感嘆米芾書法“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在米芾作品之中,其行書和草書最為人喜愛,諸如《珊瑚帖》《蜀素帖》《紫金研帖》等作品皆為傳世之瑰寶。盡管米芾繪畫作品不如其書法流芳百世,但仍然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其與兒子米友仁開創的“米氏山水”,多使用水墨點染方式進行勾勒,為我國水墨山水畫之新風——“云山墨戲”。
二、《春山瑞松圖》詳情內容
《春山瑞松圖》現今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紙本設色,縱35厘米,橫44厘米。水墨畫山崗上,隱約六棵松樹,三顯三隱,枝葉穿梭,近處松下有小亭獨立,亭內無人亦無擺設。亭前云霧翻涌,瀕臨山崖,空白無痕。遠方高山聳立,點翠綴綠。造型秀雅柔和,清峻安寧。意境開闊平和,蘊含生機。畫卷左下角處有“米芾”二字款,乃后人加。詩塘處有宋高宗題字,并有“御覽之寶”和“太上皇帝之寶”二璽。此外,鑒藏璽印有“御書房鑒藏寶”、五璽全、“嘉慶御覽之寶”等共六個。收傳印記有“興霞殿寶”“玉堂柯氏九思私印”“殿寶”“黃琳”等共四個。由于此畫作者未題年款,故無法判定其創作年限。此外,關于《春山瑞松圖》作者是否為米芾,現仍存在爭議。在《故宮書畫錄》卷五和《石渠寶笈》中,皆認定此畫為宋人所作。而后《故宮書畫圖錄》(一)又將其作者改為米芾,并認為通過詩塘的題詩可見得為宋高宗之前的畫作,而米芾之前絕不可能有人可臻此意境。
單看米芾個人的山水風格,首先不能逃離董源對其的影響。董源作為南派山水畫開創者,其畫作在自身沉淀后多表現為平靜深遠,皴法似麻袋皮面。以《夏景山口待渡圖》為例,其多處使用苔點,山勢重疊,植被細密,水天一色,顏色較為淡然。米芾給予了極高評價:“平淡天真,唐無此品。”正是因此,米芾畫作也充滿著對純真平淡的向往。此外,結合米芾所處地理環境,從襄陽到謫居鎮江,深受江南繚繞煙雨的影響,又秉持著自身獨具一格的個性,形成了一種全新的山水畫技巧,即濕筆聚積著多層次水墨點而成山,此也被后人稱為“米點皴”。米芾的兒子米友仁也繼承此技法,此類山水畫在畫史上被稱作“米點山水”。
三、《春山瑞松圖》評鑒
(一)以米點皴畫法為特色
《春山瑞松圖》中下方、遠處的山石以及繚繞的云霧均使用米點皴畫法。概看《春山瑞松圖》似描繪云霧攢動下的深山春景,畫中浮云充溢山谷,青山挺立云端,近處松樹參差下小亭空蕩開闊。此幅《春山瑞松圖》相較于下方的松木和遠山,反而將中心位置留給波動的云霧,這也正彰顯了米芾所強調的天真和追逐的平淡。
重重山峰使用渲染手法疊加青綠,山體部位順勢使用米芾特有的米點皴呈現厚重感,山頂微粉突出春日生機,像是晨光熹微映襯,又宛如春花爛漫,增添柔和感,令人身心喜悅,感到希望。前景松林樹木筆法精致細膩,嚴密錯落,用雙勾描繪松樹本體。以濕潤淡墨凸顯云霧松木,將傳統使用線條勾勒山水、云霧樹木的技法拋去,繼承王維首創的潑墨畫法,并將董源的點子皴與米芾自身所處江南云雨自然景象相結合,貫穿自身書法繪畫個性技巧,創造出以米點皴為主的,描繪云煙變化卻又不顯小氣的意境圖景,將畫中樹影搖曳、云霧波瀾壯闊、青山清淡堅挺的南方春季生趣盎然描繪得淋漓盡致。
(二)構圖三段呈現豐富層次
從構圖細看,遠景為三組層疊的青山,左處最小,中間最高,右邊較厚,形成對比,顏色從下深到中間偏綠,至山頂呈現粉色,表現出米芾創造的多種顏色薄涂而后疊加覆蓋的畫法,此配色也促成了后元代畫家對綠色、粉色的追逐。同時,此重巒疊嶂的山峰似也具備象征意義,掩蓋于云海之上,呈現沉靜開明之景。畫面中景為純澈云海,不顯筆鋒舒張卷動,卻使人們感悟到云起霧涌之間合乎“道”的大清明,近乎“誠”的洗滌,褪去世俗下人性沾染的惡習,神清氣爽怡然自得。他的點染畫技也渲染出光斑效果,層次分明。近景為幾棵稀疏松樹,盤虬搖曳,接近畫軸底部,亭子用簡約幾筆勾勒清晰。盡管松木半隱半顯,仍可以看出云霧遮蓋下的松樹與遠方同樣遮擋的山峰技法差異較大,使得畫卷形式多樣,內容豐富。
(三)以云霧為主的內容巧思
米芾在《畫史》中談論道:“鑒閱佛像故事圖,尤以勸誡為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尤是煙云霧景為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由此可以見得,在山水畫當中,米芾更為注重的乃是煙云霧色之變化與營造的恢宏之氣勢。此外,此番評價以及展開的敘述也對于山水畫取代人物畫而重構畫史有著一定的影響。依據此重看《春山瑞松圖》云霧的表現,當是掙脫山水之美而騰駕于其樂旨趣之上的心性展示,是一種對江南春日山水欣賞沉淀后的感悟凸顯。云霧流動自當不以任何意志為干擾和轉移,隨性自在實為最合乎自然變化之法則的。云霧所展現的這份恣意、不為世俗牽扯的態度,構成了感情與理性的交流,并使得二者彼此互為表里去展開協調,進而順應自然,回歸質樸本真。此實現了從零至一而歸于零的另類圓滿,也是個人情感意志與社會自然交互的結果,而這又以在萬事萬物之上的法則為歸宿,最終形成了遺世而獨立、寂靜卻自得其樂的云霧之美。
(四)意境平淡,合乎于“道”
紙本設色以精致細膩見長,米芾的《春山瑞松圖》水墨變化頗有趣味,畫卷盡管嚴密,內容卻并非厚實滿當,著重于表達作者感情和志趣。米芾關于繪畫的態度,在《畫史》中已然體現。其認為高超的畫技、惟妙惟肖的描繪固然十分重要,也是繪畫基礎,但總體卻不可一概而論,更應當關注的應是意境的呈現。其個人欣賞的是不受到世俗羈絆而可以感性為主、自由自在地表達自然的繪畫作品,并且米芾認為這遠比繪畫的技藝等外在的東西更為重要。例如米芾對王維畫作的贊賞和繼承,盡管王維文人畫在當時還未受到大范圍關注和推崇,但王維畫中的風格、意態流露以及詩畫相互交融的特點,都與米芾的追求有所重疊。
結合其書法作品和生平整體來看,米芾的繪畫美學重點表現在其對平淡的追崇和對高古意趣的向往。米芾受其父親“親儒嗜學”的影響,走上了不同于其武將世家的道路,但個人仍是不喜科舉,加上舉止怪異,奇裝異服,與常人交往偶爾受阻,對儒學更是嗤之以鼻,其思想和興趣從而轉向道家,提出了“庖丁解牛刀,無厚入有間。以此交世故,了不見后患”。這一方面表達了米芾對道家經典的涉及和掌握,另一方面也宣示了他個人的處事態度,像庖丁解牛般深刻了解牛的身體構造,直接處理最為薄弱的地方,而用之于待人接物也需在復雜厚重的社會關系體系制度中,采取順自然而合乎事物本身的相應措施、行為方式。加上米芾對魏晉文化的偏愛,其思想似乎也受到玄學的影響。由此來評析《春山瑞松圖》意境,筆者認為拋去宋高宗題詩部分,該畫重點并不在山峰的秀麗優美,也非松樹的多姿細膩抑或亭子的簡單小巧,而是中間云霧的壯闊。從前景向遠景細看,云霧呈現出由暗至明到純粹的白的轉變。米芾此番構圖和描繪,使人聚焦該圖攜以天地浩然正氣之洗禮,蕩滌宇宙間萬事萬物的紛雜,從而達到心靈的純澈和平和,此種世間之大道法則凌駕于個人之上,便形成了順從自然的德。云霧不需像山巒般久久佇立,伴隨萬古長空,也無須如松柏與小亭般經受著陽光沐浴或風雨洗禮的交替而更改。云的形成只是剎那,云的變化也在于一夕,此番順應自然的不同形態轉化,而本體卻未發生偏移,直至形成如同光的白色淡然,不僅是作者個人實踐的昭顯,也是其對宇宙真理的探索結果,更是此畫流傳于后人的巨大文化和精神價值,也映照了高宗所題的“越千萬年,以慰吾心”。
四、《春山瑞松圖》對當代個人思考的意義
以《春山瑞松圖》為參考,米芾的繪畫作品展示了個人的人生哲學。如同其在執筆《畫史》時,開門見山地指出:“五王之功業,尋為女子笑。”其認為仕途并非完全由自身努力爭取或毀滅而去變好或變壞,更多是取決于官運,字畫才是文人才子們最應當投入時間和精力的事情。這種創見突破當時世俗,對當時文人界也有著極大沖擊。這種符合“道”的順勢而為觀念,結合該圖內容思考,應立足于對山、松、云、亭等細節技藝的精煉,只有具備畫工的畫技才能進行描述和表現。在此之上無需添加過多世俗的干涉,任山、松、云自由生長,自在舒展,此看似普通的闡述,實則正是順應天道自然的無為,意蘊便自生自為地流露出來。
將《春山瑞松圖》作為藝術作品看待,首先便是藝術對人的自我思考意識的要求。畫卷乃是由自身產生并且對自身提出疑問:自身究竟是什么和一切是什么。宇宙間的萬事萬物在畫中對照著,如山峰、松樹、人造亭子等都是直接生成的,或者說是單次的,而創作者依托心靈去復現它的本身。因為山巒、松林等首先是作為自然存在物而呈現的,至于認識、觀照和思考都需要人的心靈運用。畫卷同樣可以是推動我們認識自己心靈的媒介,也是與古人溝通交流的媒介。畫的意義便是讓我們打破熟悉的環境,跳出舒適區,以畫為參照,觀照自身,思索自身。《春山瑞松圖》當中,山與松便是對現實的體現,相對的,云霧與春日淡粉生機則是作者內在的表達。倘若以《春山瑞松圖》為研究對象,應當先從經驗出發,即從現象去看待畫技的細膩和繪畫功底的表露;其次從理念出發,即本質內容中云霧帶給人們直擊心靈深處的觀感和春日微小的喜悅;最后是將經驗觀點與理念觀點相統一,實質上,該圖無論是松木山巒,還是云霧淺顯轉變,抑或小亭獨立,都是缺一不可的,它們所共同營造的才是最為真實質樸的“道”。
參考文獻:
[1]米芾.米芾集[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
[2]米芾.畫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8.
[3]趙若婷.米氏山水的風格形成與繼承關系探析[J].美術文獻,2022(5):49-51.
[4]李浩然.米芾藝術筆記的敘事空間與空間意涵[J].中國美術研究,2022(1):116-125.
[5]李東岳.米芾觀念中的李成繪畫風格:以《讀碑窠石圖》為例[J].美術觀察,2022(11):62-63.
[6]呂文亭.米芾“真趣”論及其對平淡的崇尚[J].青少年書法,2022(22):47-49.
作者簡介:
白奕琳,中國計量大學人文與外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哲學、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