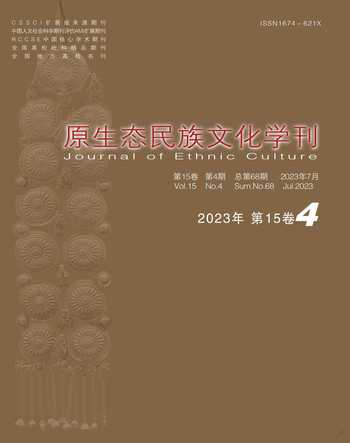清水江流域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管慶鵬 潘梅



摘 要:清水江流域的考古是貴州考古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就田野考古的深度和出土實物資料的研究來看,清水江流域的考古整體上處于方興未艾的階段。其文化遺存的特征主要受到來自湖南地區的影響,并保持著自身的獨特性。清水江流域的考古促進了貴州考古學的發展,為建立和完善貴州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以及高廟文化的傳播范圍提供了實物證據。
關鍵詞:清水江流域;考古史;高廟文化
中圖分類號:C9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 - 621X(2023)04 - 0106 - 09
在中國考古史研究中,區域考古史的興起備受學界的關注。雖然研究者的學術興趣和研究風格有所不同,但都關注考古發掘的歷程與實物資料的研究。近年以來,研究者在區域考古史方面有不少新的進展,但仍有很多值得探討的空間。既有的考古史研究成果關照到宏觀的敘述,卻忽視了微觀的闡釋;注重整體性,但忽視了區域的差異性。因此,區域考古史的研究無疑有助于加深我們對考古史的認識。基于前人的研究,文章從考古史的視角,就清水江流域內的古遺址、墓葬的調查與發掘進行梳理,并探討考古材料所反映的相關問題。需要說明的是,文章研究時間從民國時期開始,止于2020年,但涉及具體出土遺存討論時,則使用考古學年代。懇切希望方家給予指正。
一、田野考古發掘前古物的發現
清水江位于貴州省東南部,其源始于都勻境內,流經都勻市、麻江縣、凱里市、臺江縣、劍河縣、錦屏縣、天柱縣等政區,入湖南省境內稱沅江。民國時期,清水江流域發現“雷公山殘碑”引起了金石學家的關注。1956年修建黔桂鐵路時,貴州省博物館在麻江縣谷峒墳山腳清理了首批明代土坑墓,標志著清水江流域考古的開始1。自此之后,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在清水江流域發掘十余處早期文化遺存,以及不同時期的墓葬27座,為構建貴州考古文化發展脈絡提供實物資料。
關于考古史研究的范圍,閻文儒認為:“不僅限于舊日的金石學,也不限于近百年來的發掘報告,歷代對物質文化遺存的認識和重視、搜索和保護,也都應列入考古學史的范圍以內。”1就清水江流域而言,考古史的范圍主要包括金石學與物質文化遺存。隨著近代考古學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和早期考古活動的展開,使得宋代以來的“金石學最終匯入考古學中,成為近代科學考古學的一部分”2。在1949年之前的中國考古史中,安陽擁有特殊的地位。而安陽考古之外,吳金鼎等人在云南省蒼洱境內的調查與發掘成了中國考古學上一個全新的嘗試3。可見,近代考古學已經影響到西南地區。另外,1943年貴州省安龍縣名勝古跡保管會組織挖掘“三王子”墓4,則是近代田野考古實證主義傳播到貴州具體的案例。
民國時期,清水江流域的古物引起了金石學家的關注。民國《貴州通志》記載:
雷公山殘刻一 存
雷公山殘刻二 存
按以上二石皆出雷公山,發現之時頗不同。其一,在民國四五年間。其二則民國三十年,字體并難識,未能遽斷時代,然絕非元以后物,故附于此5。
方志編纂者稱民國時期共發現兩塊雷公山殘刻,時間分別在民國四五年間(1915 - 1916年)和民國三十年(1941年),殘刻以石質為載體,字體難以釋讀,絕非元代以后之物。后世研究者認為,殘刻是碑銘殘片,故稱“雷公山殘碑”6。
關于殘刻二的發現有著相對豐富的情境信息。1941年羅友梅奉命到雷公山考察物產,在雷公坪的荒土中意外發現殘刻二,并對殘刻字體進行了探究。羅友梅云:
民國三十年奉命赴雷公山考查物產,于十一月出發,經□(鎮)山臺拱至雞講(現改西江),由雞講至雷公山約二十余華里,攀藤附葛,盡二日之力而達雷公坪。坪位于雷公山之頂,咸同間為苗匪盤踞,建有房屋百余棟,可容數千人居住,并筑有諸葛臺,聞係發號施令之地,后經數載征伐,始告平息。今則荒煙蔓草,破瓦頹垣,所謂諸葛臺,不過黃土一壞而已。在荒土中得殘碑一塊,字體奇異,不類漢字,亦非苗文,而筆法蒼勁,近于漢魏,遂命工揚取以供研討云7。
雷公坪位于雷公山頂,咸同年間為張秀眉等占據,正南面遺留有“點將臺”,是否為咸同年間所建尚無定論8。關于殘刻,羅氏認為是殘碑,且“字體奇異,不類漢字,亦非苗文,而筆法蒼勁,近于漢魏”。雷公山殘刻字體奇異,至今仍不能斷代和識別。兩年后,楊西橫在“孔明碑”的拓片上亦提到雷公坪的“石碑遺址”9,但未探究其年代以及內容。新中國成立后,雷公山殘刻被文物收藏者捐贈貴州省博物館,上殘刻5個字,如圖1所示10。雷公山殘刻因缺乏紀年和可比對的字體,在斷代方面未能達成共識。但雷公山殘刻的發現,表明清水江流域的古物進入研究者的視野,為今后清水江流域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奠定了基礎。
二、方興未艾:考古發掘的歷程及其原因
麻江縣谷峒墳山腳土坑墓的清理,標志著清水江流域考古的開端。1956年修建黔桂鐵路時,在麻江縣谷峒火車站遇外挖出一面銅鼓(圖2)。隨后貴州省博物館籌備處立即派陳默溪、熊水富等前往發掘,清理豎穴土坑墓7座(M1—M7),出土銅手鐲、鐵匕首和珠飾等隨葬品。經對器物的觀察,初步判定墓葬年代為明代1。麻江縣谷峒出土的銅鼓形制獨特,研究者稱為“麻江型”銅鼓,因而在銅鼓研究中具有標尺性的作用。
1970年代以來,地方文物部門在清水江流域零星發現一批文物,逐漸改變黔東無古可考的現狀。1972年錦屏縣水泥廠在敦寨北麓采礦時,意外發現石斧1件2。4年后,黎平縣文物部門在和平村發現漢至南宋時期的古代銅錢,共38種74式3。1980年黎平縣德鳳鎮在基建過程中發現發騰蛟墓碑,并出土墓志。次年4月,黎平縣洪州區發現元代銀器26件。1982年,天柱縣高釀村民潘澤宗挖出“青龍刀”一把,刀面鑄文“嘉慶二年造”4。1989年,在錦屏縣三江鎮平金村發現一批青銅器,共8件,包括劍3件,矛1件,鏃1件,鉞2件,鋤1件。熊水富說:“在原出土青銅器的河床內,又出土了一批西漢時期的鐵斧、刀等,還有一柄典型的戰國青銅劍,亮江上游隱江地點也發現了青銅器。”5后期調查證實該地區確實存在大量的青銅器。1992年凱里市村民挖掘屋基時,發現4座明清時期的墓葬,出土銅器、珠飾和的貨幣等器物。1993年修建凱里市民族賓館周圍的道路時,發現2座石室墓,并在墓室北端壁外發現陶罐2件。同年3月,在凱里市金井村意外發現1座石棺墓,出土陶器、瓷片。是年6月,天柱縣白市發現一批新石器時期的石器6。以上器物和墓葬的發現,為我們認識清水江流域的文化提供了線索。值得注意的是,清水江流域內首次發現青銅器的出土以及新石器時期的遺物,逐漸改變了人們對黔東南考古的認知。
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入,清水江流域的考古迎來了新的機遇。2004年為配合清水江流域水電站的建設,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大規模對托口、白市、掛治等水電站周邊文物進行系統的調查,“共發現14處遺址,上百處橋梁、碑刻、民居建筑”7。2009至2011年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學考古系發掘了天柱縣辭兵洲、盤塘、溪口、坡腳、鸕鶿、月山背以及錦屏縣坪鎮陽溪、潘寨、培芽等遺址。其中溪口遺址位于天柱縣江東鄉,發掘面積約240平方米,文化堆積分為商周、宋元和明清三個時期,且以商周時期遺存為主。商周時期遺跡有“房址10座、灰坑8個、灰溝1條、窯址2個、墓葬3座、活動面4個”1。遺物包括石器、陶器和銅器等。據碳十四測年,該遺址的第⑧、⑦層的年代在公元前1770 - 公元前820年之間,即商代早中期到西周中晚期。另外,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還發掘了江東溪口窯址,出土了大量的瓷器,以青釉為主,黑釉、醬釉次之2。瓦罐灘窯址位于天柱遠口鎮,發掘面積232.5平方米,清理灰坑14個、灰坑3條、龍窯1座,出土完整或可復原的瓷器3100余件,以及大量窯具。窯址年代為元代,“是貴州經科學發掘的第一座窯址,出土瓷器種類之廣、數量之多,在本省境內首屈一指”3。可見,這次發掘的遺內容豐富,類型多樣。
2018年以后,清水江流域的考古呈現由下游向上游地區轉移的趨勢。如圖3所示,清水江上游發掘的遺址有里皋和鐮刀灣遺址。其中里皋遺址分布在清水江支流重安江西岸臺地上,地層堆積達9層,包括商周、明清等時期的文化遺存,出土典型器有花邊口沿器、小平底罐,陶器飾有繩紋、方格紋等。鐮刀灣遺址因簡報未公布,具體情況不詳。可見,清水江流域的考古發展不平衡的現狀有所改變。事實上,這種改變仍是受上游地區水電站建設的影響。
清水江流域的考古發展與現代自然科學技術的進步密不可分。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田野發掘方面,采用地層學,全站儀、篩選、浮選法等考古學技術與方法,確保了發掘工作更具有科學性。溪口遺址測年數據的公布,標志著清水江流域考古斷代工作有新的突破,為同時期遺址斷代提供了標尺的作用。另外,從清水江流域考的考古人員來看,除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外,還有四川大學和中山大學等考古人員的加入,使得清水江流域考古調查、發掘等工作更為專業。可見,以上考古技術與方法的運用以及考古人數的增長,反映清水江流域考古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清水江流域的考古雖取得可喜的成果,但發展較緩慢。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三方面值得重視。首先,清水江流域人類遺存量的田野調查深度阻礙了考古的發展。清水江流域長期處于邊地,文獻闕載,導致了人們對其歷史遺存缺乏整體性的認知。1989年錦屏縣三江鎮平金村發現首批青銅器,引起了考古學者的關注。盡管如此,當時人們并不清楚清水江流域人類遺存的數量。直到2004年以后,為配合清水江流域水電站的建設,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大規模對托口、白市、掛治等水電站周邊的文物進行田野考古調查,其調查結果打破了人們對清水江流域人類歷史的認知。由于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田野考古調查主要集中在河流階地,且呈現出線性分布的特點,因此河流階地之外的人類遺存仍不清楚。其次,清水江流域的考古朝邊緣化發展。貴州境內人類遺存的分布不均衡,就史前遺址而言,集中分布在烏江流域。盡管其它流域略有分布,但遺址數量、文化內涵豐富程度等方面都趕不上烏江流域。因此,烏江流域長期主導著貴州考古學的發展方向1。隨著貴州基建的深入,各流域的考古雖在線性方面有了延伸,點層面有了積累,但仍然無法改變貴州考古發展不平衡的現狀。而這種現狀的存在,促使清水江流域的考古朝著邊緣化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清水江流域考古的發展完全是基建推動的產物,這種依賴基建推動發展起來的流域考古又將受到該流域經濟發展的限制,一旦基礎建設項目結束,又將回歸緩慢或暫停發展的狀態。最后,國家文物政策的推行也影響著清水江流域考古的發展。清水江流域經歷三次文物普查,但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早期遺址的調查方面比較薄弱。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以上遺址的發掘為我們了解清水江流域早期人類的歷史提供了證據。
三、實物資料與相關問題的討論
前文我們梳理了清水江流域考古的歷程及其發展遲緩的原因,接下來就實物資料所見早期清水江流域人群的生計、社會互動和葬俗以及青銅器來源等問題進行探討。
(一)新石器時代清水江下游地區人群的生計與社會互動
新石器時代,狩獵和采集是清水江流域人群的主要生計方式。清水江流域位于沅水上游河段的地區,崇山峻嶺,河谷縱橫,氣候濕潤,植被蔥蔥。在這種環境中,早期人群的活動主要被限制在河流階地上。清水江流域植物種類繁多,蘊含著豐富的自然資源。除植物資源外,水產資源也是早期人群生活的重要資源。清水江流域的漁產資源在現代社會里仍然是重要的副業。考古表明,清水江流域史前時期的遺址集中分布在江水兩岸的臺地上,說明河流階地成為當時人群生產生活的主要場域。辭兵洲、陽溪等遺址的早期地層的石器原料主要來自江灘的礫石,石器類型多砍砸器,體形碩大,制作粗獷,說明這些工具有可能與狩獵和采集有關。這些遺址稍晚的地層出土了磨制石器,數量相對較少,類型有斧、鑿和錛等。新石器時代晚期,有些遺址的石器逐漸趨于小型化,石片增多,加工技術趨于復雜。盡管如此,清水江流域石器工業仍屬于典型的南方地區的礫石石器工業傳統,在形制方面與湖南沅江流域史前遺址的石器工業有著較多的聯系1。盤塘遺址的房址為排洞式建筑,柱洞直徑20厘米,平面略呈長方形,面積較小,室內未發現長期燒火的灶,表明該房子是一種臨時性的住所。此外,該流域的考古至今尚未發現大型聚落遺址和從事農業生產生活的證據,至少農業在新石器時代的清水江流域不占主導的經濟地位。在溪河的環境中,或許漁獵、采集是比農業更為可靠的生計。
清水江流域人群與高廟文化時期人群的互動。清水江與沅水同處一條河流,地貌特征均為山地與河谷相間。從清水江流域史前遺址文化特征來看,主要受到來自沅水地區高廟文化的影響。高廟文化是一支分布在以沅水中上游為中心的史前文化,該文化下層出土相當數量的夾砂陶、少泥質陶,器類有釜、罐、缽等,紋飾以戳印篦點鳳鳥紋、獸面紋等頗具特色2。清水江流域的盤塘遺址出土相當數量的夾砂陶,其中陶色主要有灰褐、紅褐、灰黑,紋飾有戳印篦點鳳鳥紋、鳳鳥紋、獸面紋等。又坡腳遺址09TPIT0301的第⑤、⑥層為新石器時代文化堆積,也包含較多夾砂陶和石器。陶色有紅褐、灰黑、黃褐、灰白等種顏色。陶器表面飾繩紋、弦紋、獸面紋以及各種形制的圖案。有研究者指出,坡腳遺址“無論陶質、器形與紋飾風格,均與高廟文化的中晚期遺存完全一致”3。很顯然,清水江流域的史前遺址,無論陶質、紋飾、器類、陶色,還是紋飾風格、制作工藝等方面均受到高廟文化的影響,說明兩者之間有考古學文化上的共性。因此,清水江流域的人群與高廟文化時期的人群存在互動的關系,使得清水江流域的人文生態得到不斷的變遷。
(二)清水江流域的青銅器來源之謎有望被揭開
關于清水江流域青銅器的來源,無非本土生產和外來流入兩種情況。清水江與沅水流域是一個被群山所環抱,且相對封閉的自然地理單元。歷史上,清水江流域曾被視為蠻夷之地。舊石器時代晚期以來,清水江流域就有著人類在此繁衍生息,并與沅水流域的人群有著密切的聯系。這種互動到新石器時期較為明顯,至商周時期以后較之前更為廣泛和深遠。事實上,這種互動關系在考古學上得到了證實。坡腳遺址清理了兩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出土兩件滑石璧,在質地、紋飾方面與湖南同時期墓葬所出的滑石璧有較大的共性(如圖4所示),足見清水江流域的葬俗受到湖南地區的影響4。清水江流域的青銅器“它包括有巴、楚和百越等其他族群系統的青銅文化特征”5,有可能是隨著戰爭流入清水江的6。因此,不可排除清水江流域所見的青銅器有外來的可能性。
清水江流域的青銅器出自本土的可能性較大。關于錦屏縣出土青銅器的文化特征,熊水富指出:“它的紋飾在滇文化和夜郎地域同類器物中見不到,也沒有巴蜀紋飾的特征,說明這是自身特點,是地域性的一種文化現象。”1清水江流域所見到的青銅器多系征集或意外發現2,并非考古發掘所獲,因此缺乏明確的地層關系及其標尺物。但是,隨著清水江流域考古的深入,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柱溪口遺址出土一定數量的青銅器,且地層關系明確,為判定青銅器的來源提供了依據。另外,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水江上游地區的考古發掘有望為我們揭開青銅器來源的問題。
(三)戰國至秦漢時期的墓葬與葬俗
目前,清水江流域經考古發掘的墓葬地點共有8處(如表1所示),分別是麻江縣谷洞,凱里市魚洞村、凱里市區、凱里市爐山,天柱坡腳遺址、溪口遺址、盤塘遺址、辭兵洲漆樹腳遺址等。其中清理墓葬共27座,墓葬形制有長方形豎穴土坑墓、豎穴土坑墓、石室墓,以長方形豎穴土坑墓為主,多數墓葬無葬具和葬式不明,隨葬品數量較少。墓葬年代最早為戰國時期,最晚為清代,以明代墓葬居多,其次戰國至秦漢,再次宋代,清代僅1座。部分墓葬的清理多系偶然性發現,因缺乏科學的編號和田野考古的規范意識,致使墓葬信息多有不全。但是,戰國至秦漢時期的墓葬在探索清水江流域早期喪葬文化方面尤為重要。
戰國至秦漢時期,清水江流域的喪葬習俗受到來自湖南地區的影響。清水江流域發掘戰國至秦漢時期的墓葬共6座,集中分布在下游地區,墓葬形制主要以長方形豎穴土坑墓為主,隨葬較少的器物。坡腳遺址發掘墓葬2座,較為典型3。M1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向為東南西北向,墓坑長3.35、寬2.48、深1.8米。墓壁較為規整,未見明顯的加工痕跡。然而在接近墓底的四周有可見黑色粉末,發掘者推測為木質葬具的痕跡。墓底兩端發現兩條承托葬具的枕木溝痕,其枕木溝長2.2、寬0.2、深0.07米,且墓底和枕木溝內均涂抹厚2 - 3厘米的青膏泥。在墓坑底部西側枕木溝之上出土滑石璧1件。M2形制大致與M1相同,墓底也發現枕木溝痕和青膏泥,且墓坑底部東南部亦出土滑石璧1件。既有的研究表明,墓底涂抹清膏泥和葬具下置枕木的習俗在同時期的湖地區墓葬中較為常見,主要分布于湖南湘西、長沙等地區1。湖南沅陵窖頭木馬嶺墓區共清理漢代墓葬36座,其中有2座墓出土了滑石璧,說明滑石璧的葬俗曾流行于湘黔地區2。除此之外,在兩漢時期西南地區的一些漢墓中也發現使用白膏泥的情況3,說明漢代墓葬使用白膏泥的習俗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四、清水江流域考古活動的影響
清水江流域的考古活動豐富貴州東南部地區的歷史文化內涵。明清以來士人常嘆:“黔省開辟較遲,文獻闕略。”1隨著貴州考古的發展,以往闕略的歷史得到了較大的改觀。清水江流域的考古相對其他流域而言較為薄弱。2009年以來,清水江流域發掘了天柱辭兵洲遺址、溪口遺址、盤塘遺址等,從而改變了黔東考古的現狀,彌補部分“文獻闕略”的歷史。其中,天柱辭兵洲遺址的發掘,直接將清水江流域的歷史推到舊石器時代晚期。以上遺址出土大量地石器、陶器、瓷器等實物資料,為了解清水江流域史前時期的人類歷史提供實物證據。此外,清水江流域的考古還發掘了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時期的房址11座以上,并出土一些生產工具、漁具等,有助于了解早期人群的生產生活。可見,清水江流域的考古豐富了歷史文化的內涵。
清水江流域的考古為建立和完善貴州史前考古學文化的序列提供材料。清水江流域的考古成果集中在史前階段,對建立和完善貴州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具有重要的價值。陽溪遺址是貴州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河流階地遺址,它實證了貴州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并非都居住在洞穴,改變了人們對舊石器時代人群生產生活的認識。清水江流域的考古表明,史前遺址基本位于河流階地,說明當時的人群主要在河流階地上繁衍生息和生產生活。另外,清水江流域的石器工業在新石器時代延續和發展了南方地區舊石器時代礫石石器工業的傳統,與同時期貴州其他地區相比,它在制作石器技術方面又略有不同。但是,它與湖南沅江流域史前的石器工業有著密切的聯系2,說明兩者之間的人群存在互動的關系。
清水江流域的考古為高廟文化的傳播及其區域文化的特點提供材料。清水江流域考古對高廟文化分布范圍和意義具有重要的價值3。在陶器制作工藝方面,清水江流域的陶器受到來自湖南地區強勢的高廟文化所影響。然而,高廟文化向清水江流域的傳播過程中所表現的物態形式卻存在著區域性的差異。這種區域性的差異與當時清水江流域的自然環境,經濟形態以及人的能動性有關聯。清水江流域的人們選擇性的接受高廟文化的元素,從而塑造了自身的文化特點。可見,清水江流域史前遺址的發掘,有助于認識高廟文化的內涵和對外傳播的歷史脈絡。
總言之,民國時期“雷公山殘刻”的發現,引起了金石學者的關注。直到1956年,麻江縣谷峒墳山腳墓葬的清理,標志著清水江流域考古的開始。21世紀初,清水江流域的考古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但整體上仍處于方興未艾的階段。其原因與清水江流域的人類遺存量,田野考古調查的深度以及國家政策有關。然而出土實物資料表明,清水江流域的石器工業、陶器制作工藝、喪葬習俗等方面受到來自湖南地區的影響,同時又保持了自身的特點。清水江流域的考古豐富了貴州歷史文化的內涵,為完善貴州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以及高廟文化的傳播提供實物證據。積極推進清水江流域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有助于闡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形成的歷史進程。
[責任編輯:龍澤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