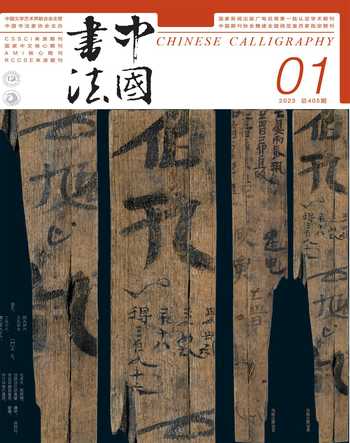篆刻史的文化形象
孫慰祖
我在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經認為:『現代階段上對于印學的研究,盡管一直有人在陸續地做,但相當時期內始終是一個很不景氣的領域。無論相對于書學還是畫學而言,都顯出明顯的失衡。』三十年過去,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變。無論古璽印研究還是篆刻藝術研究,這些年加速融入當代學術理念和相關學科的成果,由舊學脫胎為一門具有明確研究對象、研究任務和科學研究方法的現代新學。
在藝術領域中來看,文人篆刻研究取得的進展更多地受到關注。在比較宏觀的篆刻史層面,如關于文人篆刻形成的物質與文化條件的提出,文人篆刻起點的討論,文人印系的存在及其與文人篆刻遞承關系的揭示,早期篆刻家群體身份與流派定位的解析,文人篆刻與文人精神生活關系的探討,藝術品市場與篆刻家生存狀況的考察,篆刻表意格局與功能轉變關系的論述等等,都表明研究視野的提升并到達一定的史學高度。從相對微觀的層面來看,諸如篆刻家個案研究、早期印譜研究、印人流派風格及交游、印人作品技法及創作背景等研究,在搜求文獻的深度與廣度上均有很大突破,注重相關人文學科新觀念、新方法與新材料的引入也是這一時期研究者普遍的自覺。篆刻審美和創作技法理論,則在當下研究論述中體現出現代色彩,部分地置換了長期因循的體驗式的表達形態,盡管這一方向的研究仍然為數不多。
因而,構成這一時期研究高度的不僅是所形成的成果水平,還在于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標的更新。讀完朱琪的《小道可觀:中國文人篆刻》書稿,我的上述感受尤為強烈。
近十余年來,我讀過不少朱琪發表的明清篆刻研究的文章,深刻的印象是他的論題多緊扣篆刻文化與藝術兩方面的屬性,有他獨到的視角與論證,還有形成結論的嚴謹和文字的古雅。
十多年前我提出印學的視野不僅要在『印之內』,還應該延伸到『印之外』,印學的價值才能更多地體現出來,這就要求學術觸角盡可能地廣泛。朱琪把這本書冠以『小道可觀』之名,既言印章其小,而又洞悉其道之大,拓展其研究之大,充分表達了他對這一研究領域的深刻認識和堅定信念。本書圍繞著一般人看起來不過方寸的印章里面的種種問題,但所作的研究背后,涉及考古學、古器物學、文獻學、書畫鑒定、美學、社會學、史學等多個學科,由此可見,斯道焉能言其小哉!
多年前,朱琪持續地投入清代早期浙派印人的個案研究。近年他仍然咬定青山,孜孜無倦。現在我手中的這本書稿,顯示出朱琪的研究視野延展到更大的范圍,他對于一些歷史細節的思考也站在更為宏觀的高度,某些論題顯得更為自由也更有學科跨度。盡管發現冷題和盲點一直是他的興趣,惟陳言之務去是他的寫作原則。
在本書中,我讀到的幾個論題,不僅如他所自信的『新』,而且也是令我感興趣并深受啟發的問題。
在唐宋至民國文人篆刻發展這幾個歷史階段,他分別攫取了一些重要而又需要更深入闡釋的或者篆刻史上少有涉及的議題作出再思考。這些篇章善于運用新材料、新方法、新思路,也敏捷地汲納當下學術新成果,因而為這個冷寂學科做了不少填空的工作。舊題新論,是算得上是名實相副的。
早期文人篆刻及相關『印跡學』研究,闡述的是文人篆刻的早期萌芽狀態,這是兩宋文人用印體系逐漸成熟的階段。作者在宋代官印的形式變革部分,注意到了以往篆刻史研究少為人論及的祝溫柔,較為系統地論述了他對文人篆刻的風格美學的影響,是十分富于洞見力的。在『宋代印人、印事、印譜輯考』部分,通過經典文獻的釋讀,結合宋代詩文別集中的記述,考證宋代篆刻在文人階層與民間社會的活躍狀態,并提出宋代除集古印譜外,已經出現個人篆刻印譜,揭示出印譜史上兩種最重要的印譜形式都在宋代華麗登場。這些結論,充實了我們對中國早期篆刻史、印譜史的認識。
此外,我認為朱琪在文人篆刻溯源研究中,十分重視對出土文物、傳世實物的價值開掘,這與圈內長期局限于文獻記載、疏于關注文物考古新資料的風氣形成迥異的學術個性。他對新中國成立后出土(含征集)的大量明代文人印章作出全面梳理與考述,此前《新出土明代文人印章輯存與研究》一書就是第一次從考古學、文物學角度,全面審視明代印章、篆刻的基礎研究工作,他在這項工作中獲得了不少新的結論。如關于『印跡學』『前流派篆刻』等概念所引出的話題,深具建立在資料基礎上的學理依據,我相信將為學者的后續研究留下更深的啟發。
文人篆刻家的生存狀況是近十余年來印史研究的一個新論題,朱琪以多年來積累的資料整理成《晚清民國以來篆刻潤例匯輯》,是目前為止最為完整的『篆刻經濟』的微觀史料。藝術史研究從著眼作品到關注人文,是學術觀念的一大轉變。
坦率地說,無論從『印內』還是『印外』,無論學科意義上的印學研究格局還是文人篆刻研究這一支系,都是一個需要藝術實踐體驗的研究領域,這使得一些跨學科的研究者難免困于對研究對象的藝術體認與美學揭示。另一方面,如果深諳于創作但學術理論能力儲備不足的藝術家真正介入研究領域,亦容易受限于思辨的格局和研究方法與路徑。這是毋庸諱言的現狀。
實現這一跨越需要橋梁。正因為以上原因,朱琪近十余年來的成果特別引起印學界的關注與稱譽,這些年他不僅扎扎實實地拿出了幾部真學術的著作,而且屢屢獲得重要獎項。而我則更留意他研究范圍的拓展,對他的學術結構很感興趣。朱琪自幼喜愛書法、篆刻并且一直在勤勉地修煉、創作,研修文史的本科與研究生經歷,與他的愛好糅合成傳統文人的生活理想與自身氣質,也許一個偶然的契機激發起他進入文人藝術史研究的興趣,于是一發而不可收,轉而攻讀藝術學博士,接受更加嚴謹的專業訓練,也促使他的堅持心和探險心與日俱增。學藝并進,厚積薄發,鋪就他的學術與藝術的進境,而前者正是朱琪的學術歷練中體現出來的典型性。
書學、印學都不是讓『萬眾歡呼』的東西,學術的『冷攤』雖然空寂孤獨,但卻時有新鮮感。我相信,作者一定感受到了發現的快樂具有難以拒絕的誘惑力,哪怕別人看來微不足道。一路走來的這段黃卷青燈歲月和由此拓展出來的學術、藝術愿景,決定了他仍然會在這條『小道』上走下去。
作者單位:上海博物館
本文責編:蘇奕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