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期古剌諸土司地望問題新探
謝信業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廣東廣州 510275)
明成祖即位后,派遣中官楊瑄、給事中周讓等人招撫云南百夷諸部。永樂三年(1405),因得知“百夷之外萬余里”的大小古剌部落欲與中國通貢,楊瑄、周讓等人遂“由滇池入百夷,歷猿猴所家,蛇虺所都,魑魅所宅”(1)〔明〕 胡廣: 《胡文穆公文集》卷一二《贈給事中周讓重使古剌序》,線裝書局2013年版,第39—40頁。,長途跋涉數月之久,最終抵達其地。至永樂四年(1406)夏季,大古剌酋長潑的那浪派遣使團跟隨明使前往南京朝貢,且代表鄰境的小古剌、底馬撒、底板、八家塔等“自昔未通中國”的諸番部落,向明朝表示“愿內屬,乞設官統理之”。明朝于其地設置了大古剌、底馬撒二宣慰司,及小古剌、底板、八家塔等五處長官司。到永樂二十二年(1424),又為調停大古剌與底兀剌之爭,增設了底兀剌宣慰司。(2)〔明〕 嚴從簡著,余思黎點校: 《殊域周咨錄》卷九《云南百夷》,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329—330頁。
然而,古剌諸土司因位置僻遠,距離云南數月之程,與明朝的交流往來并不密切。到宣德以后,古剌諸土司已經“不能復通貢”。明代前中期的地理志書又以古剌諸土司皆系“遠小之極”,并無詳細載錄,以至于明代以來傳世文獻中的相關內容零散混亂。學界關于這些土司地理方位的探討長期存在爭議,逐漸形成“下緬甸說”與“阿薩姆說”。“下緬甸說”源于明末清初的地理志書,如《明史》等文獻皆稱“(大古剌)亦曰擺古”,“(底馬撒)在大古剌東南”(3)《明史》卷四六《地理志·云南》,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196—1197頁。。方國瑜受其影響,推測大古剌、底馬撒、底兀剌位于下緬甸地區。(4)方國瑜主要以《明史地理志》為依據,認為古剌、擺古是一地,即下緬甸之白古;底馬撒“疑即馬達班為地那悉林地區也”;又以“東胡即洞吾,亦作東牛、東吁,而底兀剌即其譯音異字”。參見方國瑜: 《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010—1014頁。國內學界大多采信其說,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7冊《明時期全圖(一)》中,便將大古剌、底馬撒、底兀剌三司標注于下緬甸勃固附近。(5)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7冊《明時期全圖(一)》,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第40—41頁。其后,尤中、龔蔭、賀圣達等學者在各自論著中也持有類似的觀點,參見尤中: 《中國西南邊疆變遷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154頁;龔蔭: 《中國土司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03、606頁;賀圣達: 《緬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頁;周振鶴主編,郭紅、靳潤成著: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10頁。相較之下,國外學界從20世紀初開始逐漸形成“阿薩姆說”。英國學者杰里尼(G. E. Gerini)、呂斯(G. H. Luce)、緬甸學者陳孺性(Chen Yi-sein)等人,根據發現于印度阿薩姆邦的明代“底馬撒宣慰司”信符這一線索,提出了底馬撒、古剌等土司分布于阿薩姆地區的觀點。(6)G. E. Gerini, Ti-ma-s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13, No.3; G. H. Luce and Tin Htway, A 15th century inscription and library at Pagan, Burma, Malasakera Commemoration Volume, Colombo: The Malasakera Commemoration Volume Editorial Committee, 1976; 陳孺性: 《關于“大古剌”“小古剌”與“底馬撒”的考釋》,《東南亞》1993年第2期。不過,陳孺性同樣遵循《讀史方輿紀要》諸書之說,認為大古剌宣慰司位于下緬甸地區,并將相悖之處牽強地歸咎于《明實錄》編寫有誤。(7)陳孺性: 《關于“大古剌”“小古剌”與“底馬撒”的考釋》,《東南亞》1993年第2期。因此,相關問題尚有進一步研討的空間。
對于大小古剌諸土司的地理方位的再檢討,有助于豐富明代前期云南邊疆形成與發展過程的細節,而信符的發現及前人研究的不斷推進,為進一步探究大小古剌諸土司的相關問題提供了新的方向與思路。本文擬通過梳理中、緬、印主要史料文獻,結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對大古剌、底馬撒等土司的地理位置等問題進行探討。
一、 古剌與孟族白古王國關系考辨
永樂初年,戶科給事中周讓兩次奉命出使古剌,對于推動古剌諸番與明朝建立政治聯系起到直接作用。在永樂五年(1407)第二次出使古剌前后,周讓特地撰寫了《重使古剌集》,記敘其出使古剌的事跡。然而該書亡佚于明清之際,僅存明初閣臣胡廣為之創作的《贈給事中周讓重使古剌序》。(8)〔明〕 胡廣: 《胡文穆公文集》卷一二,第39—40頁。此外,嘉慶《無為州志》等方志文獻中關于周讓出使古剌事跡的只言片語很可能也與《重使古剌集》有關。(9)嘉慶《無為州志》卷一九《人物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頁。遺憾的是,這些零星記錄并未留下太多關于古剌風土人情、地理方位的線索。宣德、正統以后,大古剌、底馬撒、底兀剌諸土司與明朝官方往來中斷,《云南圖經志書》《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等成書于景泰、天順年間地理志書也未記載大小古剌、底馬撒諸土司的內容,明人對這些土司地理方位的認知逐漸模糊。到明代晚期,隨著緬甸東吁王朝迅速崛起,原先作為云南屏藩的孟養、木邦、車里、八百、老撾諸土司相繼被緬甸吞并,云南內地也受到了威脅。在此邊疆危機背景下,晚明士人開始關注云南“外夷土司”的沿革情況,并且逐漸將大古剌、底馬撒諸土司與緬甸相聯系。譬如,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云:“大古喇,亦稱宣慰,不在六慰中。與底馬撒最先為緬甸所得,其先世不知所起,亦不知何姓。”(10)〔明〕 沈德符撰,楊萬里點校: 《萬歷野獲編》補遺卷四,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931頁。大古剌、底馬撒最先淪入緬甸之說在萬歷年間已經開始流行,其后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談遷《國榷》、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等著作或受此影響,皆言“大古喇亦曰擺古”“底馬撒在大古喇東南”“(擺古)即古喇宣慰司,擺古,夷語也”(11)〔清〕 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214頁;〔清〕 顧炎武撰,黃坤等點校: 《天下郡國利病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6頁。另有“是年,平緬酋莽瑞體據古剌宣慰司,殺其酋長,遂入孟養、八百、老撾。瑞體,莽紀歲幼子,避思倫法難,奔洞吾,近于古剌。古剌兄弟相攻,為解之,遂擁眾絕其道路,二酋皆死,盡有其地,緬自此始強”,參見〔明〕 談遷著,張宗祥點校: 《國榷》卷六○,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787頁。。到了清代,不僅《明史》修撰者采信顧祖禹等人的著作,地理志書也多附會其說。(12)如雍正《云南通志》謂大古剌宣慰司在八百大甸宣慰司之西,底馬撒宣慰司在孟養宣慰司金沙江下游。參見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四《土司附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329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5頁。正因這些記載,現代學者基本傾向于認為大古剌是下緬甸勃固地區由孟人(Mon)建立的白古王國(Pegu),底馬撒在丹那沙林(Tenasserim)。又因“底兀剌”與“洞吾”音近,置之于東吁(Taungoo)。(13)方國瑜: 《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第1012頁;尤中: 《中國西南邊疆變遷史》,第149—154頁;龔蔭: 《中國土司制度史》,第627—628頁。然而,通過檢尋中緬史籍后可知,明代初期的白古王國與大小古剌諸土司并不是同一個政權或者民族。
(一) 《明太宗實錄》所載的白古王國
永樂初年,明朝設置大古剌諸土司的同時,也曾嘗試與下緬甸的白古王國進行外交接觸。據《明太宗實錄》載,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命中官楊瑄“撫諭麓川、車里、八百、老撾、古剌、詔閩、特冷、冬烏、孟定、孟養、木邦等處土官”(14)《明太宗實錄》卷二二“永樂元年八月庚午”條,《明實錄》第6冊,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14頁。。其中,明朝重點招撫的對象之一“特冷”,就是孟人的舊稱“Talaing”。永樂二年(1404),楊瑄等人受阻于八百大甸(即蘭那王國),無法深入東南亞內陸,其出使特冷、冬烏的計劃只能暫時擱置,轉而與周讓一行撫諭孟養、古剌諸地。(15)《明太宗實錄》卷三三“永樂二年八月己丑”條,《明實錄》第6冊,第588—589頁。但是到了永樂三年九月,明廷又派遣連迪詔諭“速睹嵩及西里帳土官板洋等”(16)《明太宗實錄》卷四六“永樂三年九月己亥”條,《明實錄》第7冊,第710頁。。連迪是否抵達其地,史無詳載。(17)《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 有“又有速睹嵩者,亦西方之國。永樂三年,遣行人連迪等赍敕往招,賜銀鈔彩幣,其酋以道遠不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8587頁)。不過至永樂五年七月,“速睹嵩土官板洋”正式向明朝派遣了使團。(18)《明太宗實錄》卷六九“永樂五年七月乙丑”條,《明實錄》第7冊,第975頁。跟隨速睹嵩使團而來的還有緬甸王子“馬者速”的求援使者:
緬甸故土官卜剌浪次子馬者速遣人朝貢。初,卜剌浪分其地,使長子那羅塔管大甸;次子馬者速管小甸。卜剌浪死,那羅塔盡收馬者速土地人民,馬者速往依速睹嵩土官板洋,為贅婿。至是欲復居小甸,遣人來朝,且訴其情。(19)《明太宗實錄》卷七一“永樂五年九月庚申”條,《明實錄》第7冊,第995頁。
事實上,早在永樂四年,明廷便已經從木邦宣慰司處得知了緬甸土官那羅塔、馬者速兄弟相殺一事。據張洪《使緬錄》記載:
今年鄧伯通引木邦獻捷,說在著冷時,有得冷差人來告爾(那羅塔)殺兄收嫂,又欲殺弟只更,只更逃于木邦、轉奔得冷,乞朝廷處之。(20)〔明〕 張洪: 《使緬錄》,余定邦、黃重言編: 《中國古籍中有關緬甸資料匯編》,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77頁。
文中的“只更”為封邑之名,與緬甸“小甸”是同一地方,即緬甸北方重鎮實皆(Sagaing)。緬甸王子“馬者速”則是緬王明基蘇瓦紹蓋(Minkyiswasawke,卜剌浪)之子、明康(Minkhaung I,那羅塔)之弟明代達(Min Theiddat)。據緬甸史書《琉璃宮史》記載,緬歷762年(1400),明康在明代達的支持下奪得緬甸王位。明康即位后,冊封明代達為實皆侯,明代達因未能獲封副王而心懷怨恨,遂于緬歷768年(1406)起兵反叛。明康王很快挫敗了叛亂,明代達被迫流亡至白古,依附于孟王亞扎底律(Razadarit)。亞扎底律將王妹許配給明代達,所以明代文獻中稱馬者速是速睹嵩土官板洋的“贅婿”。緬歷769年(1407),明代達又因通緬之罪被亞扎底律處決。(21)李謀等譯: 《琉璃宮史》,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393—395、402頁;Jon Fernquest, Rajadhirat’s mask of command: military leadership in Burma (c. 1348-1421), SOAS Bulletin of Burma Research, 2006, Vol. 4, No.1, pp.12-15.結合中緬史書可知,白古王國即《明實錄》和《使緬錄》中的“速睹嵩”“得冷”。“速睹嵩”(Su-du-song)一詞的來源,應與孟人直通王國(Thaton)的梵式國號“Sadhuim”有關。至于土官“板洋”“板野”皆為孟人貴族頭銜“彬尼亞”(Binnya)的音譯,同時也是白古王國的一代雄主亞扎底律。
馬者速事件后,“速睹嵩土官板洋”于永樂七年(1409)冬再次向明朝進獻了馬匹與金銀器皿。(22)《明太宗實錄》卷九八“永樂七年十一月己丑”條,《明實錄》第7冊,第1291頁。永樂十年(1412)三月、永樂十三年(1415)七月,亞扎底律又以“特冷土官班野”之名向明朝進貢。(23)《明太宗實錄》卷一二六“永樂十年三月辛丑”條,《明實錄》第8冊,第1578頁;《明太宗實錄》卷一六六“永樂十三年七月癸丑”條,《明實錄》第8冊,第1860頁。盡管白古使團先后四次取道云南進貢,但始終未能得到明朝的足夠重視。明廷方面沒有像任命大古剌、底馬撒等土司一樣授予亞扎底律正式的土司官職,而是將其視為“未歸化”的土官。到了永樂末期,緬孟戰爭接近尾聲,白古王國已無須借助明朝的力量來制衡緬甸,所以停止了與明朝的非正式關系。
(二) “古剌”的多種涵義
明確了大古剌宣慰司與孟人白古王國是不同政權后,陳孺性關于“大古剌”一名源于孟地“Taikkala”的推斷便難以成立了。不過陳孺性也指出“古剌”一名與東孟加拉土著“Gola”人的泥屋建筑物有關。(24)陳孺性: 《關于“大古剌”“小古剌”與“底馬撒”的考釋》,《東南亞》1993年第2期。這其實是古代緬人將印度人稱為“kula/kala”來源問題的諸多假說之一。在緬語中,作為名詞的“kula/kala”通常表示“來自印度次大陸的人”(印度人)或者“緬甸以西國家的土著”(西洋人、洋人)。與緬人有著密切交流的德宏傣族人受其影響,同樣將印度人或者西洋人稱為“kala”。(25)孟尊賢編著: 《傣漢詞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關于“kula/kala”的原意,主流觀點認為該詞匯源于巴利語或梵語的“種族”“貴族后裔”(kula)之意。還有假說主張源于孟語“Gla”,意為“居住在泥筑房屋中的人”(26)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緬甸語教研室編: 《緬漢詞典》,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17頁;Khin Maung Saw, (Mis) Interpretations of Burmese words: In the case of the term Kala (Kula), MoeMaka, 20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27223806, http://eng.moemaka.net/2016/01/khin-maung-saw-misinterpretations-of-burmese-words-in-the-case-of-the-term-kala-kula/。。
雖然緬語中“kula/kala”的來源尚未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明代西南文獻中的“古剌”一詞確實來源于緬語或傣語,如《皇明經濟文錄》載景泰二年(1451)緬甸奏文稱:“這頭目不來時,古剌、答冷、百夷必笑我。天皇帝可憐見,放回來時,得養活他的父母。古剌、答冷、百夷聽得時,必然都喜歡。”(27)〔明〕 萬表編: 《皇明經濟文錄》卷三○《緬甸奏文三道》,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4年版,第78頁。明代晚期頗為知名的“古剌錦”也與緬甸有著極大的關系。(28)據《西南夷風土記》載:“緬甸、西洋出大布,而夷錦各夷皆出,惟古喇為勝。”萬歷二十年,緬甸向明朝進獻的物品中就有“番布古喇錦”。明代晚期以后的中國士人之所以將古剌與下緬甸的孟族白古王國混淆,或許正是源于緬甸輸入明朝的“古喇錦”。參見〔明〕 朱孟震: 《西南夷風土記》,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8頁;〔明〕 王士性: 《廣志繹》卷五,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26頁。因此,“古剌”一詞音譯自緬語、傣語中印度人“kula”的可能性較大。然而,緬語、傣語中“kula”一詞與梵文中“黑色”(kla)發音相近,這種帶有印度種姓制度色彩的詞匯讓生活在緬甸的印度裔感到不滿。盡管語言學者嘗試澄清“kula”一詞并無歧視之意,并且將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極端民族主義者視為制造此種“誤解”的始作俑者。(29)Khin Maung Saw, (Mis) Interpretations of Burmese words: In the case of the term Kala (Kula), MoeMaka, 20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27223806, http://eng.moemaka.net/2016/01/khin-maung-saw-misinterpretations-of-burmese-words-in-the-case-of-the-term-kala-kula/.但不可否認的是,古代印度人膚色以及語言發音等客觀情形,導致了該詞匯在傳播過程中逐漸演變為古代緬人和傣人對具有相同體貌特征族群的稱謂。例如,膚色黝黑是“古剌”“哈剌”的一個基本特征。錢古訓《百夷傳》云:“古剌,男女色甚黑。男子衣服妝飾類哈剌,或用白布為套衣;婦人如羅羅狀。”(30)〔明〕 錢古訓撰,江應樑校注: 《百夷傳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頁。明末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也稱:“古喇,貌極丑惡,上下如漆。男戴黑皮盔,女蓬頭大眼,見之可畏。”(31)〔明〕 朱孟震: 《西南夷風土記》,第4頁。尤中認為“古剌”是傣族對佤族的稱呼(32)尤中: 《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4—498頁。,因此“大小古剌”與黑膚色的“古剌人”應當有所區別。
錢古訓等人見到的“古剌人”很可能只是生活在滇西及上緬甸地區的土著部族。此外,永樂五年曾置古剌驛,隸屬金齒干崖長官司,或許就是以當地黑膚土著為名。(33)關于設置古剌驛的原因,有“李從人,騰沖土人,選充騰沖征緬招討司通事,永樂五年,跟隨長官刁思濃赴京,保任古剌驛驛丞”(〔明〕 佚名: 《土官底簿》,中國書店2018年版,第169頁)。又據《明太宗實錄》卷六八“永樂五年六月辛亥”條云:“云南干崖長官司刀歡等遣子刀思曩來朝,貢象馬金銀器皿方物,賜之鈔幣。”(《明實錄》第7冊,第963頁)可知李從人乃是以通事的身份跟隨干崖長官刁思濃(刀思曩)前往南京朝貢,而獲封古剌驛驛丞之職。值得注意的是,《明太宗實錄》卷六九“永樂五年七月壬子”條:“大古剌等處土人頭目刀放別等二十七人來朝,賜鈔及文綺紗羅襲衣。”(第965頁)筆者認為由于大古剌與明朝語言不通,需要“重數譯”,而此處的“土人頭目刀放別”或許正是大古剌使團中的傣族翻譯。《明太宗實錄》卷五四“永樂四年五月丁巳”條:“大古剌所屬諸酋長皆遣使朝貢” (第811頁),其中或許就包括了大古剌所屬的傣族部落。不過,由于干崖、南甸、騰沖一路為“通孟養、大小古剌”之道,也不排除古剌驛之名源于“大古剌”的可能性。然而,這些漫游于滇西及上緬甸山區的松散部族,絕非土地廣闊、自古未曾通貢于中國的“大古剌”。
二、 古剌諸番方位的再考察
據《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四年六月,大古剌使臣選馬撒曾言:“其鄰境有七,曰大古剌、小古剌、底馬撒、茶山、底板、孟倫、八家塔。”(34)《明太宗實錄》卷五五“永樂四年六月壬午”條,《明實錄》第6冊,第817頁。大古剌既非白古王國,那么與之“鄰境”的底馬撒、底兀剌、小古剌、八家塔、底板諸番部落自然也不應在下緬甸地區尋找。在上述諸部中,可以明確大致方位的只有茶山長官司。《明宣宗實錄》載,宣德五年(1430),茶山長官司奏稱:“所轄夷民,悉居深山,而滇灘當小茶山瓦高之沖”(35)《明宣宗實錄》卷六七“宣德五年六月丙子”條,《明實錄》第11冊,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575頁。,“滇灘”位于今云南省騰沖市滇灘鎮。又有《大明一統志》云:“騰沖軍民指揮使司,東至永昌府潞江安撫司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麻里長官司界三百里,南至南甸州界二十里,北至茶山長官司界二百四十里。”(36)〔明〕 李賢等: 《大明一統志》卷八七《騰沖軍民指揮使司》,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2頁。可知茶山長官司位于高黎貢山西麓、緬甸北部恩梅開江流域地區,而與之“鄰境”的大古剌諸土司當在此境附近。(37)關于茶山長官司的位置的考證,參見楊永生: 《茶山長官司史略》,《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羅勇: 《明代茶山、楊塘、鎮道隸屬關系及地理位置考》,林超民主編: 《西南古籍研究(2016年)》,云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事實上,明代前期地理文獻的相關記載大都表明“古剌”位于麓川或孟養(Mohnyin)的西部。例如,關于“古剌”方位的最早記錄見于錢古訓所著《百夷傳》:“百夷,在云南西南數千里,其地方萬里。景東在其東,西天古剌在其西,八百媳婦在其南,吐番在其北。東南則車里,西南則緬國,東北則哀牢(今之金齒衛也),西北則西番、回紇。”(38)〔明〕 錢古訓撰,江應樑校注: 《百夷傳校注》,第33—42頁。又有李思聰《百夷傳》載:“(百夷)東接景東府,東南接車里,南至八百媳婦,西南至緬國,西連戛里,西北連西天古剌,北接西番,東北接永昌。”(39)〔明〕 錢古訓撰,江應樑校注: 《百夷傳校注》,第146頁。陳孺性認為“西天古剌”斷句有誤,當為“西天、古剌”。(40)陳孺性: 《關于“大古剌”“小古剌”與“底馬撒”的考釋》,《東南亞》1993年第2期。盡管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但可以確定的是,“西天”是元明時期對于印度的稱謂(41)〔明〕 王宗載撰,羅振玉輯: 《四夷館考》卷下《西天館》,東方學會1924年本,第16頁。,無論是“西天古剌”還是“西天”和“古剌”,都反映了“古剌”位于麓川的西界,與印度相近。
結合后續文獻的記載可知,錢古訓、李思聰二人著述中位于百夷西界的“古剌”就是大小古剌。錢古訓、李思聰出使麓川和緬甸的六七年后,楊瑄、周讓等人奉命前往百夷地區尋訪“大小古剌”。當時明廷已在金沙江(伊洛瓦底江)以西的孟養設置宣慰司,楊瑄、周讓一行人取道孟養,前往大小古剌。(42)張洪《南夷書》載:“初,(孟養)刀木旦為思倫法陶孟,以女妻之生子三朋。及思倫法為昭(王也),以他女為昭曩,刀木旦蓄怒未泄。嘗率兵攻破金齒,又欲并吞戛里。值內官楊瑄、給事中周讓招諭古剌,往其處。刀木旦說以招戛里,遣人為之導,乃揚言于戛里曰:‘將招爾屬孟養,必盡殺之。’戛里怒,殺其導,刀木旦遂執詞以伐之。”參見王叔武: 《〈南夷書〉箋注并考異》,《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正統八年(1443),王驥追擊麓川思任法父子時奏稱:“(通事董義言)賊勢窘迫,聞知大軍再舉,必將奔遁金沙江、戛里、大古剌臧之地。”(43)〔明〕 徐日久: 《五邊典則》卷一九《西南》,《衢州文獻集成》第96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頁。以此揆之,大古剌當在金沙江、戛里(Kale)等地之外。景泰、天順年間成書的《云南圖經志書》《大明一統志》等地理文獻皆載孟養宣慰司“東至金沙江,南至緬甸宣慰使司界,西至古剌界,北至干崖宣撫司界”(44)〔明〕 陳文修,李春龍、劉景毛校注: 《景泰云南圖經志書校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346頁;〔明〕 李賢等: 《大明一統志》卷八七《孟養軍民宣慰使司》,第1343頁。。其所謂的“古剌界”無疑是位于“西天”的大小古剌。
楊瑄、周讓等人對“百夷之外萬余里”大小古剌諸部的認知顯然是來自麓川。根據《勐卯古代諸王史》等傣族歷史文獻記載,元代麓川土官思可法(思翰法)曾派遣其弟坤三弄率兵征討天竺的吠舍厘國(Vaishali)。坤三弄自孟養一路向西,最終征服了吠舍厘諸國,使得“思翰法的疆土到了大海洋”(45)云南省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辦公室編: 《勐果占壁及勐卯古代諸王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48、84頁。。這一看似荒誕不經的故事可以得到緬甸碑銘材料的印證,據1442年東敦侯底里澤亞都(Thirizeyathu)所立之蒲甘碑銘記載,“九十萬之主”思翰法(Suiw Khan Phwa,即思可法)之孫思任法(Suiw Nam Phwa)統治著二十一把“傘”(王國),其中就包含了“大海之濱,佩戴踝環的Kula(古剌)和Timmasa(底馬撒)”(46)G. H. Luce and Tin Htway, A 15th century inscription and library at Pagan, Burma, Malasakera Commemoration Volume, p.214; Taw Sein Ko. Inscriptions of Pagan, Pinya And Av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Rangoon: Government Printing, Burma,1899, p.38.。直到緬甸貢榜王朝時期,仍然將阿薩姆地區稱為“吠舍厘”(Vesali)。(47)Than Tun, The Royal Orders of Burma, Part Seven, AD 1811-1819, Kyoto: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1998, p.97.阿瓦王朝早期的緬人同樣與這一區域有著密切往來,1400年,緬王明基蘇瓦紹蓋豎立的碑銘宣稱,當時的緬國全境越過建都(Kandu)、崩龍(Ponlon)、坎底(Khamti)諸部,遠至那伽國(Naga)和以“殺人祭神”為風俗的底馬撒臘國(Timmasala)。(48)G. H. Luce and Tin Htway, A 15th century inscription and library at Pagan, Burma, Malasakera Commemoration Volume, p.211.元明之際麓川向西擴張活動推動了傣族大規模遷入阿薩姆邦,而傣人、緬人對于“西天”風土人情的見聞,又為錢古訓、周讓等出使西南的旅行者所獲悉。
20世紀初葉,“底馬撒宣慰司”信符的發現也佐證了古剌諸土司位于印度阿薩姆地區。大約在1912年前后,英國學者古爾登(P. R. Gurdon)在印度阿薩姆邦焦爾哈德縣(Jorhat)一位阿洪傣人王室后裔家中發現了“底馬撒宣慰司”信符。該信符為金屬材質,正面有“信符”二字,左上有“永樂五年月日造”等小字。背面篆書“皇帝圣旨”“合當差發”“不信者?儑”三列由上而下,由左而右,呈品字型排列。在信符的右側下端有“底馬撒宣慰司”小字。又側面中上部有“文”“行”“忠”“信”四字的半部。古爾登發現信符后,邀請了當時著名的緬甸華人學者杜成誥(Taw Sein Ko)對信符進行鑒定。時人認為底馬撒位于泰國北部的清邁,故而杜成誥推測此物或為緬甸征服清邁時獲得,隨后在緬甸征服阿洪王國過程中流入阿薩姆。(49)P. R. Gurdon, The origin of the Ahom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13, No.2, pp.283-287; W. W. Cochrane and Taw Sein Ko, The origin of the Ahom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14, No.1, pp.150-158.1913年,在古爾登發表相關文章后不久,英國學者杰里尼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他認為底馬撒(Timasa)實際上是阿薩姆地區迦車厘人(Kachari)建立的“底馬撒王國”(Dimasa)。(50)G. E. Gerini, Ti-ma-s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13, No.3, pp.690-694.呂斯、陳孺性等人也認為“底馬撒”即生活在阿薩姆地區的迦車厘人。(51)陳孺性: 《關于“大古剌”“小古剌”與“底馬撒”的考釋》,《東南亞》1993年第2期。

圖1 永樂五年所頒之底馬撒宣慰司信符
底馬撒王國統治著布拉馬普特拉河南岸以丹斯利河(Dhansiri)流域為中心的地區,位于那伽蘭邦的底馬普爾縣(Dimapur)是其都城。16世紀前后,傣族人建立的阿洪王國(Ahom)崛起于阿薩姆平原東部,并且在不斷向西擴張的過程中與迦車厘人頻繁發生戰爭。迦車厘人被迫退往那伽蘭邦山區,其政治中心也遷往了梅邦(Maibong)。(52)Nityananda Gogoi,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Medieval Assam, India: EBH Publishers, 2016, p.334.杰里尼推測,或許是在入侵底馬撒王國的戰爭中,阿洪傣人繳獲了明朝頒給底馬撒土官臘罔帕的信符。(53)G. E. Gerini, Ti-ma-s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13, No.3, p.694.由于明朝與阿薩姆地區的政治聯系早已中斷,信符不再具備作為同明朝政府交往的勘驗憑證,而是被阿洪傣人視為一種貴重的裝飾品。直到20世紀初被古爾登發現,此塊信符一直為阿洪傣王室成員及其后裔所保存。(54)P. R. Gurdon, The origin of the Ahom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13, No.2, pp.283-287.總之,無論是明代早期的地理文獻還是發現于阿薩姆的“底馬撒宣慰司”信符的實物,均表明了大古剌、底馬撒諸土司分布于上緬甸乃至印度東北布拉馬普特拉河谷的廣泛區域。
三、 大古剌、底兀剌等土司的地望與族屬
通過前文的梳理與探析,大致可以確定明代永樂年間所設置的大古剌、底馬撒、底兀剌等土司位于上緬甸或印度阿薩姆邦境內。除了底馬撒宣慰司與茶山長官司的地理位置并無太多爭議,其余大古剌、底兀剌、小古剌、底板、八家塔、孟倫諸土司的具體地望及族屬都需逐一討論。
(一) 孟倫長官司
孟倫長官司為孟養(迤西)境內的屬邦,據《西南夷風土記》載:“(迤西)內有孟倫、安都六之勁兵;中有謙底、底乃之險峻;外有孟戛里、孟掌之兩卒土地。”(55)〔明〕 朱孟震: 《西南夷風土記》,第9頁。方國瑜推測孟倫在孟養南部之茂盧(Mawlu)(56)方國瑜: 《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第992頁。,然而按《緬略》所載:“(瑞體)自率兵侵迤西,屢為思個所敗。個亦退保猛倫,相持不下。”(57)〔明〕 包見捷: 《緬甸始末》,方國瑜主編: 《云南史料叢刊》第4卷,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32頁。思個拒緬之事發生在萬歷元年(1573)前后,《琉璃宮史》云: 緬歷933年(1571),孟養、孟拱土司起兵反緬,緬王勃印曩多次發兵鎮壓。至緬歷937年(1575)底,緬軍為追捕逃入山林之中的孟拱土司(即思個),深入緬北山區,“從坎底坎寧到達孟隆”,最后到達雪山之麓。(58)李謀等譯: 《琉璃宮史》,第791—794頁。此處提及的“孟隆”應即明代文獻中記載之“孟倫”“猛倫”,位于緬甸克欽邦葡萄縣(Putao)一帶,舊時稱為“罕底龍”土司(Hkamti Long)。永樂四年(1406)明廷任命的孟倫長官名為“刀罕替”,實際上就是“Hkamti”的音譯。
(二) 底板長官司
“底板”(Di-ban)一名來源于“Tipam”。(59)陳孺性: 《關于“大古剌”“小古剌”與“底馬撒”的考釋》,《東南亞》1993年第2期。底板人(Tipamias)曾多次與阿洪傣人發生戰爭。據阿洪傣人的編年史《阿洪菩楞記》記載,15世紀前后,底板人起兵作亂,曾迫使一位貴族投奔孟卯的思任法(Shurenpha)。后來阿洪傣王蘇當法(Shudangpha)發兵征服底板,迫使底板人定期向阿洪朝貢。(60)Rai Sahib Golap Chandra Barua, Ahom-Buranji: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End of Ahom Rule, Calcutta: Baptist Mission Press, 1930, pp.49-51.15世紀中期以后,底板人逐漸被阿洪傣人同化,成為阿洪王國早期主要的聯姻部族與王侯封邑。(61)Nityananda Gogoi,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Medieval Assam, pp.304-305.今阿薩姆邦底興河(Dihing)北岸的納哈爾卡蒂耶縣(Naharkatiya)境內尚有底板村(Tipam Gaon),底興河南岸的迪布魯加爾縣(Dibrugarh)亦有底板米亞村(Tipamia)。
(三) 八家塔長官司
“八家塔”(Ba-jia-ta)為傣族阿洪王國早期都城“Bakata”的音譯,位于阿薩姆邦東部希瓦薩加縣(Sivasagar)東部底桑河(Disang)北岸。(62)Nityananda Gogoi,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Medieval Assam, p.379.根據《明太宗實錄》的記載,八家塔土官名為“刀輕罕”,屬于典型的傣族酋長稱號。阿洪傣人的編年史聲稱傣族君主蘇可法(Sukapha)于13世紀初葉就已經建立了阿洪王國,而蘇可法的現實原型之一是元末麓川土官思可法,故而傣族人在阿薩姆平原崛起的時間不會早于14世紀中期。作為阿薩姆平原為數不多的傣族小國,八家塔很可能是傣族人西遷至阿薩姆過程中最早建立的城邦,同時也是阿洪王國的前身。
(四) 底兀剌宣慰司
據《明太宗實錄》載,永樂二十二年二月,大古剌入侵底兀剌。底兀剌土官之孫納蘭派遣頭目朵馬實里智,與孟倫、小古剌使臣入貢,并向明朝告急。明廷遂以其地設置底兀剌宣慰司,任命納蘭為宣慰使,頒賜印信、金牌、信符等物,并且敕諭大古剌退還侵奪之地。(63)《明太宗實錄》卷二六八“永樂二十二年二月戊辰”條,《明實錄》第9冊,第2432頁;《明太宗實錄》卷二六九“永樂二十二年三月己卯、丙申”條,《明實錄》第9冊,第2437、2439頁。相關研究者多將“底兀剌”與緬甸中部錫當河谷的東吁(Taungoo)相聯系。然而明代初年將東吁稱為“冬烏”“東胡”,與“底兀剌”頗有差異。又根據《琉璃宮史》《白古紀年》等緬甸文獻記載,此年前后東吁并未遭受白古的襲擊,而且東吁國中也沒有無權力更替之事。(64)李謀等譯: 《琉璃宮史》,第551頁;Arthur P. Phayre, On the history of Pegu,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873, No.2, pp.120-159.所以,底兀剌為東吁之說應有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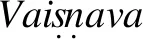
(五) 大古剌宣慰司
大古剌與底馬撒皆因“地廣”而設宣慰司,又據《明太宗實錄》載,永樂六年(1408),大古剌土官潑的那浪出兵攻打底板、孟倫、八家塔三司。永樂二十二年,大古剌侵據底兀剌。(68)《明太宗實錄》卷八二“永樂六年八月丙子”條,《明實錄》第7冊,第1903頁;《明太宗實錄》卷二六八“永樂二十二年二月戊辰”條,《明實錄》第9冊,第2432頁;《明太宗實錄》卷二六九“永樂二十二年三月己卯、丙申”條,《明實錄》第9冊,第2437、2439頁。可見大古剌是阿薩姆地區的一大霸主。《南詔野史》稱潑的那浪為“大古剌王”(69)〔明〕 倪輅輯,〔清〕 王崧校理,〔清〕 胡蔚增訂,木芹會證: 《南詔野史會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頁。,應即迦摩縷波史書(KamaruparBuranji)中提到的迦摩達王速達蘭迦(Sudaranka),或者密里敢迦(Mriganka)。迦摩達王國(Kamata)占據著布拉馬普特拉河中下游之地,其都城迦摩達補羅(Kamatapur)位于今天印度西孟加拉邦北部科奇比哈爾縣(Koch Bihar)附近。密里敢迦(Mriganka)統治時期,迦摩達國的疆土西起加羅陀耶河(Karatoya)與榜葛剌國相鄰,向東則擴張到薩地亞城。(70)Nagendra N. Acharyya,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Assam (A.D. 1228 to 1603),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7, p.163.這與明代文獻所載大古剌侵占底板、孟倫、八家塔、底兀剌諸地之事頗為契合。
陳孺性推測“潑的那浪”(Po-di-na-lang)來源于巴利文“海港之主”(Pattnana Rhang)。(71)⑩ 陳孺性: 《關于“大古剌”“小古剌”與“底馬撒”的考釋》,《東南亞》1993年第2期。結合古代阿薩姆地區的王號來看,“潑的”一詞與梵文“君主”(pati)發音相近,而“那浪”應當與底兀剌納蘭一樣,源于“narayan”。
(六) 小古剌長官司
陳孺性認為“小古剌”即孟加拉境內錫爾赫特(Sylhet)地區北部的高羅(Gour)。⑩然而15世紀前后錫爾赫特地區王國眾多,高爾之北尚有加延底亞(Jayantiya)、牢爾(Laur)諸國,不可能不為明朝使臣所發現。按照《明太宗實錄》記載:“給事中周讓等使小古剌等處還,賜鈔、文綺、襲衣”(72)《明太宗實錄》卷五四“永樂四年五月甲辰”條,《明實錄》第7冊,第805頁。,可見周讓第一次出使任務的對象是小古剌,而據《贈給事中周讓重使古剌序》記載:
至則其酋率其類驅象馳馬,具舟艦供張,張旗伐鼓,陳兵出迎于道,咸喜愕以手加額曰:“使者從天而下也!”于其國中設新亭館以居讓等,即遣使從他使者至京師報謝。留讓居歲余日,勞燕甚至。今年夏,遣使同讓備方物來貢,且請臣置吏,天子錫以冠帶印章,授以古剌宣慰使,賚予有加,復命讓再往。(73)〔明〕 胡廣: 《胡文穆公文集》卷一二,第39—40頁。
永樂三年八月周讓從南京出發,次年五月已經還朝,所以絕無可能“留讓居歲余日”,“歲”或為“月”之誤。(74)嘉慶《無為州志》卷一九《人物志》載:“永樂初,兩使西域,艱難萬狀。西人懾以威勢,徙諸荒野,瀕死者數四。時同行有中使二人,恇懦欲服。讓引諭蘇武自況,眾志以定,西人服讓忠誠。讓復諭以朝廷威德,辭旨厲害了然,西域諸國咸隨入貢。”(第4頁)筆者推測,周讓“瀕死者數四”的遭遇應當是發生在永樂五年第二次出使古剌期間。當周讓自大古剌歸來后,便向明廷報告了大古剌土官潑的那浪發兵侵入底板、孟倫、八家塔之事。又永樂四年夏季,只有大古剌派遣使臣選馬撒等人跟隨騰沖千戶孟景賢回國復命,“報謝”“進貢”當為同一批使臣。小古剌人所從之“他使者”,應即孟景賢、選馬撒一行人等。其年五月甲辰日(6月1日),出使小古剌的周讓先至南京。十余天后的丁巳日(6月14日),孟景賢及大古剌使臣選馬撒等人才抵京。(75)《明太宗實錄》卷五四“永樂四年五月丁巳”條,第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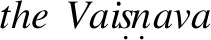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亞學者韋杰夫(Geoff Wade)認為大小古剌之名來源于印度東北布拉馬普特河地區傳統地理概念“北岸”(uttara-kula)和“南岸”(dakshina-kula)。(78)Geoff Wade, Da Gu-la, Southeast Asia in the Ming Shi-lu, https://epress.nus.edu.sg/msl/place/da-gu-la.中世紀阿薩姆碑銘中用以表示“河岸”“海岸”的“kūla”(79)關于“uttara-kula”“dakshina-kula”的梵文寫法,可參見Mukunda Madhava Sharma, Inscriptions of Ancient Assam, Gauhati: Gauhati University, 1978, pp.119, 199。,與梵文“種族”(kula)發音十分相近,是以緬甸、麓川將迦摩縷波地區稱為“古剌”。
結 語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明代初期設置的大古剌、底馬撒、底兀剌三處宣慰司及小古剌、底板、八家塔三處長官司位于今印度東北布拉馬普特拉河沿岸地區。孟倫、茶山二處長官司則位于今緬甸北部,地處云南通往阿薩姆的道路之上。
明代西南邊疆政區存在著明顯的“內外分野”,而云南最為典型。明朝所置之車里、孟養、木邦、緬甸、八百、老撾諸土司都屬于“外夷衙門”,這是一個與云南直隸府、州、司相對的概念,現代學者將其概稱為“外邊政區”或者“邊區土司”。(80)陸韌、凌永忠: 《元明清西南邊疆特殊政區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219頁;秦樹才、辛亦武: 《明代云南邊區土司與西南邊疆的變遷》,《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1期。從這些“外夷土司”的地理分布態勢上看,布拉馬普特拉河谷的大古剌、底馬撒、底兀剌諸土司實際上與湄公河流域的車里、八百、老撾諸土司,伊洛瓦底江流域孟養、木邦、緬甸諸土司,構成了明代云南政區體系最外部的三大區塊,同時也反映了明代前期在云南外邊的三個拓展方向。布拉馬普特拉河谷地區自漢唐以來就是滇、蜀地區溝通南亞、西亞的交通要道。然而隨著宋元時期海上貿易的蓬勃發展,以及滇、緬地區地方政權的阻絕,傳統的南方絲綢之路逐漸淡出了中原王朝的視野。明朝統一云南前后,曾多次主動派遣使者探尋、聯絡西南諸國。到了永樂初年,撫諭西南的活動達到了高潮,遂有楊瑄、周讓等人大規模撫諭百夷諸部落,“往返數萬里,重數譯”而遠至大小古剌的壯舉。從中外交通角度來看,楊瑄、周讓之行其實是明朝試圖重新開拓漢唐以來“蜀身毒道”的一次嘗試。為了控制這條連接西南邊疆與南亞次大陸的陸上走廊,明朝先后設置了大古剌、底馬撒、底兀剌等土司,同時也使得明朝在西南邊疆政治影響力所輻射的范圍達到了歷史頂峰。
此外,永樂初年對于西南邊疆地區的地理探索與稍后的鄭和下西洋事業海陸并舉,極大地拓寬了明代士人的視野。據《西南夷風土記》載:“西抵西洋大小古喇、赤發野人、小西天,去天竺佛國一間耳”(81)〔明〕 朱孟震: 《西南夷風土記》,第1頁。,以及沈懋孝《雜記》云:“袁履善為余言,曾至小西天極界上,去蜀中三萬里,滿地皆旱蓮。”(82)〔清〕 黃宗羲: 《明文海》卷四七九,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0頁。這表明明代中晚期的士人對于云南通印度之道已經相當熟知。然而,和下西洋事業戛然而止的命運類似,隨著宣德、正統以后明帝國對外政策總體趨于保守,古剌諸土司與明廷的政治互動頻度不斷下降。加之正統、景泰時期西南通道因麓川之役阻絕,以及阿薩姆地區政治局勢的快速轉變等諸多原因,最終使得明朝與古剌諸土司之間的聯系徹底中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