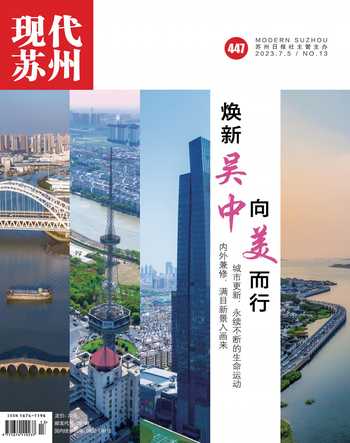【蘇說蘇軾】滟滪堆
王國剛
嘉祐元年(1056)春天,蘇軾21歲,蘇轍18,在蘇洵的帶領下,“三蘇”第一次共同離開家鄉。經成都,過閬中,穿褒斜谷,古棧道陡峭曲折,翻秦嶺,進入關中,前往京師。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這是一條出蜀之旱路。
事隔三年(1059),秋天,蘇軾與蘇轍,兄弟兩人在還鄉為母親大人受制期滿后,再次在父親的引領下,帶上家中所有,包括各自內人、家傭等,沿岷江,經樂山、瀘州,順長江,重慶、涪陵、忠縣、奉節。此為一條離開四川的水道。
兩條途經,異樣風景,身為父親,蘇洵欲使兩個兒子盡可能多地見識一些世界上的不同。兩岸青山遮不住,一江秋水難倒流。不知不覺,舟行已九百多公里,前方是三峽西大門,瞿塘之夔。
據《山海經·大荒東經》記載,夔是一種野獸,人們將其視同為神的化身。說在東海,深達七千里外有座流波山,上有形狀像普通之牛,青色的身子,沒有長角,僅一條腿。入海出水,披風戴雨,發出的光芒就像太陽和月亮,吼聲如同雷鳴。以夔而名,天下之第一雄關也。
當年,夔門前突出著一塊名為“滟滪堆”,又稱淫預、猶豫、燕窩的巨石,如馬似牛若龜比象,有歌謠朗朗上口,“滟滪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游;滟滪大如龜,瞿塘不可回;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水經注·卷三十三·江水一》有詳細描述: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為淫預石,冬出水二十余丈,夏則沒,亦有裁出處矣。淫預石即為滟滪堆,在酈道元看來,冬天高達66米多,夏天沒入江中,時有冒出江面處。
站在船頭,望著江水,自唐古拉山脈融化了的雪水,經過二千五百公里左右的長途奔騰,會百水而至,彌漫浩瀚,如橫流,奔放于廣闊的平原,氣象萬千。遇滟滪堆,杜甫有詩云,“眾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巨石水中央”“如馬戒舟航”。舟行至此,多有傾覆,世人將此怪罪于巨石者多,說它是天下最危險的地方。
蘇軾有著與常人不一樣的看法。三峽之寬,尚不足江面的十分之一,如果沒有滟滪堆首先在此“挺身而出”,殺一殺水勢,那么,飛流直下,江水毫無阻攔地狂瀉奔騰,銳勢直沖峽口,進入三峽的船只命運,或將面臨更為兇猛險惡之境遇。“以余觀之,蓋有功于斯人者。”非但無罪,更有其功。
獨特的思考方式,加深了蘇軾對水的認識。天底下最有規律的事物,江河浩廣,大海深邃,我們都可以用意識去揣度,而水卻是沒有固定的形狀,隨著他物之異同而自身隨時發生著千變萬化,且極具規律。
江水驕縱暴孽,來到峽口,近狹窄,被逼之萬頃,突然之間猛然匯于一杯,卻不知滟滪堆的“身”后有三峽之彎道,僅憑一己之蠻力,猛然暴怒瘋狂地沖擊,猶如戰車,搏斗喧鬧,吼聲震天,一輪又一輪,發動著進攻。
好似一座城垣,滟滪堆堅不可摧。江水就像攻城之敵人,劍折箭盡,紛紛撲倒在了巨石的下面。雖然竭盡全力,最后,只能彎彎曲曲繞著城垣緩緩東流。自此,匯入瞿塘峽口,安然平緩,而去。
“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事物本來就存在因安逸而生變故,處于危難而得安全的規律。推而廣之,自然界有著事物變化的固有道理。豐富的想象,帶出了蘇軾對人生更為深刻的思考。
此時的蘇軾,年齡24歲。帶著如此清醒的認識,前方的人生道路,還有什么艱難困苦能夠阻擋他一路向前呢?
年輕時,曾經的一群小伙子,在如父輩之領導帶領下,乘火車到南京,轉輪船,逆流而上,至武漢,前往宜昌,到達三峽。此刻,大壩已開建。其中,一個從不吃辣的蘇州人,歸來后,從此無辣不歡。蜀人之好,姑蘇有人被染。
讀《滟滪堆賦并敘》,人生的道路上,立柱學把萬夫關。從此,走過了一個又一個險灘。望向前,高峽平湖出,輕舟已過萬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