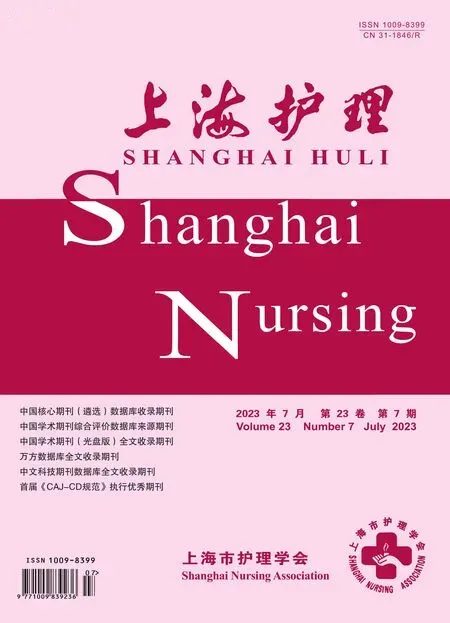中藥熱奄包對脛骨平臺骨折術后肢體腫脹患者膝關節功能的影響
彭娟文,楊小芳,黃金華,曾莉,劉珍玲
(宜春市中醫院,江西 宜春 336000)
脛骨平臺骨折是常見的骨折類型,多由暴力因素所致,常伴有關節面移位、塌陷,嚴重影響患者膝關節功能。目前,脛骨平臺骨折的臨床治療仍以手術治療為主,旨在恢復正常關節解剖結構。但同時,手術創傷可能會影響血管靜脈回流,增加血管通透性,從而引發肢體腫脹,影響骨愈合,延長患者康復時間[1]。對于術后肢體腫脹,目前臨床多采取冰敷、鎮痛等干預方法,其雖有一定效果,但效果維持時間較短,整體干預效果有限[2]。祖國醫學提出,骨折為“傷骨”范疇,加之手術損傷會導致氣血瘀滯、脈絡不通,從而致使肢體腫脹,干預需以止痛、活血化瘀、消腫等為原則[3]。中藥熱奄包作為中醫常用外治法,是將加熱好的藥包直接置于患處,利用熱蒸氣使藥效直達病處,從而起到調氣血、溫經絡、活血等作用[4]。本研究旨在探討中藥熱奄包對脛骨平臺骨折術后肢體腫脹患者膝關節功能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選取宜春市中醫院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收治的脛骨平臺骨折術后肢體腫脹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經醫師局部查體并結合X線攝片、CT等影像學檢查確診為脛骨平臺骨折,且為新鮮閉合性骨折;②單側骨折;③具有手術治療指征,并首次行切開復位、內固定術;④重要臟器功能正常;⑤術后切口四周腫脹;⑥精神、認知正常;⑦依從性好,可配合研究的開展;⑧患者及家屬對此次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標準:①凝血功能異常者;②既往有脛骨平臺骨折史者;③合并有嚴重心腦血管疾病、感染性疾病、出血性疾病、神經功能障礙或惡性腫瘤者;④合并其他部位骨折者;⑤患處皮膚有潰爛者;⑥裝有心臟起搏器者;⑦哺乳期、妊娠期或月經期患者。研究通過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倫理審查批號:20200413)。此次研究共納入患者79例,根據患者入院單尾號進行分組,單號為對照組(n=40),雙號為觀察組(n=39)。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詳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1.2 干預方法
1.2.1 對照組術后接受常規護理干預。術后適當抬高患肢,按時查看切口情況,并予以24 h冰敷干預,之后根據患者恢復情況指導其進行康復訓練,如逐漸從床上肢體伸縮與屈伸運動、踝關節運動、膝關節運動等,緩慢過渡到踝關節牽拉、內翻等,之后協助患者下床進行負重訓練(雙拐—單拐—無拐),訓練強度以患者耐受為宜。患者出院后每周進行1次電話隨訪,了解其訓練情況并給予相應指導。
1.2.2 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術后24 h進行中藥熱奄包熱敷干預。取透骨草30 g、伸筋草30 g、艾葉30 g、威靈仙30 g、羌活15 g、花椒20 g、虎杖30 g、細辛15 g、紅花20 g、炒蒼術30 g、獨活15 g,將上述藥材混合均勻后置入雙層紗布袋內,用冷水浸泡30 min后,置于電蒸鍋,水開后蒸30 min左右,然后用無紡布包裹(注意溫度控制在50~70℃),再用3條浴巾包裹后熱敷患肢。注意熱敷時應避開切口部位,每次熱敷20~30 min,2次/d。出院后囑患者居家期間按時熱敷。兩組干預周期均為4周。
1.3 觀察指標
1.3.1 患肢腫脹面積分別測量兩組患者干預前(術后24 h時,護理干預之前)及干預4周時手術側肢體腫脹面積。由護士統一使用皮尺繞患肢腫脹處1周,測量其周徑,并測量腫脹長度范圍,測量前去除紗布,注意嚴格按照無菌操作進行。腫脹面積=腫脹長度×腫脹周徑。
1.3.2 疼痛程度干預前及干預4周后,采用視覺模擬評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6]評估兩組患者手術側肢體的疼痛程度。要求患者在一條長10 cm并標記有0~10分的直線上,根據自覺疼痛程度標記對應的位置,分值越高則疼痛感越強。
1.3.3 炎性因子水平干預前及干預4周后,分別采集兩組患者空腹靜脈血4 mL,以4 000 r/min轉速離心處理10 min,取血清并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測定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C反應蛋白(CRP)及白介素6(IL-6)水平。
1.3.4 膝關節功能采用膝關節功能Lysholm評分[7]評估兩組患者干預4周后的膝關節功能。Lysholm評分由Lysholm與Gillqui于1982年創建,評估內容包括疼痛、蹲姿、使用支撐物、腫脹度、跛行、不安定度、閉鎖感、樓梯攀爬8個項目,總分值范圍0~100分,分值越高表明膝關節功能越好。該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680,重測信度為0.940。
1.4 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23.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處理。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頻數、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視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干預前后兩組患者患肢腫脹面積比較干預前,兩組患者手術側肢體腫脹程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4周后,兩組患者患肢腫脹面積均較干預前明顯縮小(P<0.05),且觀察組腫脹面積較對照組更小,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術側肢體腫脹面積比較(cm2,xˉ±s)
2.2 干預前后兩組患者患肢疼痛程度比較干預前,兩組患者術側肢體疼痛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4周后,兩組患者患肢疼痛評分均較干預前明顯降低,且觀察組評分更低,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3。

表3 兩組疼痛程度比較(分,xˉ±s)
2.3 干預前后兩組患者炎性因子水平比較干預前,兩組患者的TNF-α、CRP及IL-6等3項炎性因子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4周后,兩組患者的3項炎性因子指標水平均較干預前有所降低,且觀察組各指標水平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干預前后兩組患者炎性因子水平比較(xˉ±s)
2.4 干預后兩組患者患側膝關節功能評分比較干預4周后,觀察組Lysholm評分為(86.35±6.74)分,高于對照組的(79.51±6.69)分,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4.527,P<0.05)。
3 討論
3.1 脛骨平臺骨折術后肢體腫脹的病因及護理現狀手術作為脛骨平臺骨折的首選治療方案,雖可使骨折端良好復位,利于膝關節恢復,但也會對軟組織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傷,加之術后制動等,易出現患肢血液循環受阻,造成肢體腫脹、疼痛,從而延長患者術后康復時間[8]。目前,針對臨床骨折術后患肢腫脹,多采取冰敷患側肢體,以促進腫脹消退;同時鼓勵患者術后早期進行康復鍛煉,以促使肢體血液流通,從而改善肢體腫脹、疼痛等情況[9]。但臨床應用也發現,冰敷對于腫脹緩解的維持效果較短,且患者康復依從性不佳,整體干預效果有限[10]。
3.2 中藥熱奄包對脛骨平臺骨折術后患肢康復的影響
3.2.1 有助于緩解患肢腫脹及疼痛中醫將骨折術后肢體腫脹歸為“傷筋”范疇,認為其病機在于氣血瘀滯、血行不暢、脈絡不通等,干預原則在于活血化瘀、通脈絡、止痛等[11]。中藥熱奄包為中醫“熱療”療法之一,通過將加熱好的藥包置于患處,利用熱蒸氣促使患處毛細血管擴張,調節血循環,可起到溫通脈絡、行氣活血、止痛散寒等作用[12]。表2及表3結果顯示,干預4周后,觀察組手術側肢體腫脹面積小于對照組,疼痛評分低于對照組,說明中藥熱奄包干預有助于緩解脛骨平臺骨折術后肢體腫脹、減輕患者疼痛。這也與李女仙等[13]的研究結果類似。分析其原因在于,中藥熱奄包中的透骨草可活血化瘀、消腫止痛,伸筋草可舒筋活絡,艾葉、羌活、花椒、細辛可散寒止痛,威靈仙可通絡止痛,虎杖可活血止痛,紅花可活血化瘀,炒蒼術可祛風散寒,獨活可祛風濕、止痛,多種藥材聯合應用可起到活血化瘀、消腫止痛等作用,且藥包熱敷可使藥效直達病處,從而利于緩解患者肢體腫脹、減輕疼痛。
3.2.2 有利于降低術后炎性因子水平骨折發生后,局部壞死組織會促使機體釋放炎性因子,引發炎癥反應,而手術損傷則會進一步加重炎癥反應,從而導致患肢腫脹,增加感染風險,影響患者康復[14]。TNF-α、CRP、IL-6作為臨床評估炎癥反應的常用指標,其中TNF-α主要由巨噬細胞分泌,可誘導多種炎性因子釋放;CRP為急性時相蛋白,炎癥狀態下水平顯著升高;而IL-6為促炎因子,具有促進炎性介質釋放作用,可增強炎癥反應[15]。表4顯示,干預4周后,兩組患者的TNF-α、CRP及IL-6水平均有所降低,且觀察組患者較對照組更低。這也說明中藥熱奄包干預有利于減輕脛骨平臺骨折術后患者的炎癥反應。分析原因在于,中藥熱奄包中的威靈仙、羌活等多種藥材均具有抗炎作用,可從根本上抑制炎性因子釋放,同時熱蒸氣將藥效帶入患處,可促使毛細血管擴張,強化組織對藥物的吸收,從而利于炎性物質吸收,減輕炎癥反應[16]。
3.2.3 有助于改善患者膝關節功能結果顯示,干預4周后,觀察組患者膝關節功能Lysholm評分較對照組更高,說明中藥熱奄包干預對促進脛骨平臺骨折術后肢體腫脹患者膝關節功能恢復有積極意義。究其原因在于,患肢腫脹面積的縮小及疼痛減輕,有利于患者早期進行關節功能鍛煉和早期下床行走,從而利于提高肢體功能,促使膝關節功能恢復。
4 小結
中藥熱奄包干預有助于促進脛骨平臺骨折術后肢體腫脹患者局部水腫消除及疼痛緩解,有利于降低炎性因子水平,進而可改善患者膝關節功能、促進其術后康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