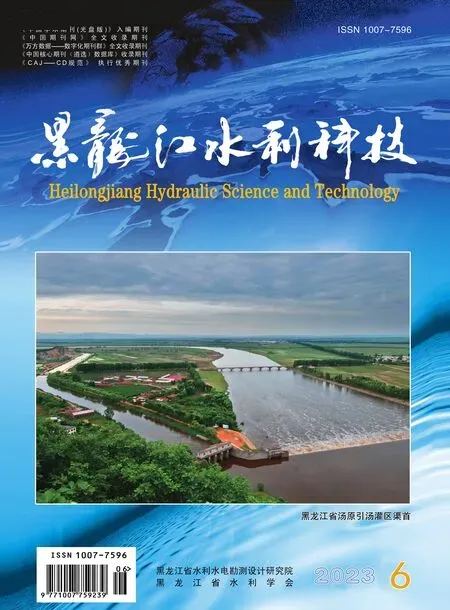引水式小水電梯級開發環境影響的生態足跡分析
陳麗君
(玉門市水務局,甘肅 玉門 735211)
0 引 言
在國內,裝機容量不超過50 MW 的水電被定義為小水電(SHP)。截至2015 年底,國內已建成47000 多座水電站,總裝機容量73 GW,年發電量23000 億kW·h,占全國水電的25%。小水電的開發在改善偏遠山區的能源供應和農村電氣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小水電已經是許多農村地區的主要發電方式。利用SHP 是減少木材消耗防止森林砍伐的一種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然而,小水電的開發,特別是引水小水電的開發也可能造成環境干擾和破壞,包括水文條件的變化、水生生態系統結構的改變、植被破壞、土壤侵蝕等[1]。引水式小水電開發的這些影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生態系統的損失。人們可能認為單一引水式小型水電站對環境的影響并不嚴重。但隨著流域的梯級開發,其影響可能會增加。
以往對引水式小水電的環境影響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很少有研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對梯級引水SHP 的累積效應進行評估。為了評估和比較積極和消極累積效應的程度,有必要使用統一方法對其進行量化[2]。生態足跡(EF)分析方法是一種基于生物物理量的簡單評估工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密切相關。EF 以國際單位hm2表示。國際單位hm2是指一公頃具有世界平均生產力的生物生產空間。EF 可用于測量任何產品、活動或影響。所需數據容易獲得,操作方法簡便。因此,環境足跡可用于環境管理和規劃工具。
文章研究的第一個目的是使用EF 方法評估小型河流中梯級引水SHP 電站的累積環境影響。第二個目標是比較環境足跡成分,以確定需要特別注意的環境影響的最主要因素。
1 研究區概況
本研究的研究區域河流全長約85km,流域面積634km2,海拔800~1200m,研究區域年降水量1200~1600mm。該河流流域植被覆蓋率超過74%。盆地內裸露的巖石相對破碎,風化,加上高山陡坡,暴雨和山洪暴發時會發生滑坡、崩塌或泥石流等地質災害,平均侵蝕強度為1000 t/km2。
從上世紀末開始,在該河上修建了七座梯級引水小水電站,即一至七座小水電站,分別表示為H1、H2、H3、H4、H5、H6 和H7。表1 列出了七個引水小水電站的裝機容量、年發電量、代柴發電量、減水段面積、植被破壞面積、水土流失面積。

表1 七個梯級引水小水電站的基本情況
2 研究方法
2.1 環境足跡計算框架
考慮到上文討論的引水式小水電開發的主要正面和負面環境影響,提出了環境足跡計算框架。在本研究中,正面影響被定義為生態供應足跡(ESF),主要指通過使用引水SHP 替代木材來保護植被。負面影響被定義為生態損失足跡(ELF),包括施工期間和施工后運營期間,減水段的魚類和凈初級生產力損失、植被破壞和引水SHP造成的土壤侵蝕。
2.2 換算系數
環境足跡賬戶包括兩個轉換因子的組合:等價因子和收益因子。
2.2.1 等效因子。
等效因子是一種比例因子,它將特定土地類型(如農田或森林)轉換為生物生產面積的通用單位hm2。當量系數表示給定生物生產區域相對于所有生物生產區域的世界平均潛在生產力的世界平均潛在生產力。對于生產力高于地球上所有生物生產區平均生產力的土地類型(如森林),當量系數>1。給定年份的不同區域具有相同的等效因子,每年僅略有變化。本研究中使用的等效因子為森林1.1,生產水域 0.2。
2.2.2 屈服因子。
由于不同地區的生產要素(如氣候、土壤、技術等)不同,同一塊土地在不同地區的生產能力也不同。產量因子表示一類生產空間(如森林)的當地產量與一類生產空間(如森林)的全球平均產量之間的差異。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一套產量因素,每種類型的生物生產區各有一套。在本研究中,森林的產量因子為0.91,生產水域的產量因子為1.0。
2.3 ESF 的評價模型
2.3.1 單引水小水電ESF 評價模型。
電可以轉換成熱。全球水電平均生產率為1000GJ/hm2. 換算關系如下:1 GJ 等于1×109焦耳(J),1 J 等于2.778×10-7kW·h。采用熱換算法(將取代木材的小水電發電量轉換為熱量)評估植被保護面積:
式中:EFf為單引水SHP的生態供應;φ為替代木材的發電量與總發電量的比率;Qe為平均年發電量;r3為森林的等效因子;y3為森林的屈服因子。
2.3.2 梯級引水小水電ESF 評價模型。
梯級引水水電站的ESF 為單個引水水電站的ESF 之和:
式中:EFnf為引水式小水電n級電站的生態供應;φn為n號引水式小水電中用于替代木材的發電量與總發電量的比率;Qne為n號引水式小水電的年平均發電量。
2.4 ELF 的評價模型
2.4.1 單一引水小水電的生物量和凈初級生產力損失。
生產單位重量的魚消耗的浮游植物量至少是浮游植物量的25 倍。因此,引水水電站減水段魚類和凈初級生產力損失足跡之間存在定量關系:
式中:EFr為魚類和單一引水SHP 的凈初級生產力損失足跡;k為凈初級生產力與魚類生物量的比率,k取25;Sr為減水段水域面積的減少,hm2;r5為生產水域的當量系數;y5為生產水域的產量系數。
2.4.2 梯級引水小水電的魚類和凈初級生產力損失。
基于理論分析和現場研究,假設n級引水式小水電級的魚類和凈初級生產力累積損失呈非線性增加。隨著引水SHP 電站數量的增加,引水SHPn梯級的魚類和凈初級生產力損失足跡將增加λn-1倍:
式中:EFnr為n梯級引水SHP 的魚類和凈初級生產力損失足跡;EF(n-1)r為(n-1)梯級引水SHP 的魚類和凈初級生產力損失足跡;k為凈初級生產力與魚類生物量的比率(k取25);Snr為n級引水SHP 減水段水域面積減少量,hm2;λ為河流生態破壞程度指數(λ=1.3)。
2.4.3 單一引水水電站的植被破壞。
引水式小水電的植被破壞主要是由于長距離引水管道工程的施工造成的。單個引水SHP 的植被破壞足跡可按以下模型計算:
式中:EFv為單引水水電站的植被破壞面積,hm2;Sv為長距離引水管道工程施工造成的植被破壞面積,hm2。
2.4.4 梯級引水小水電的植被破壞。
梯級引水水電站的植被破壞足跡為單個引水水電站的植被破壞足跡之和:
式中:EFnv為指n梯級引水水電站的植被破壞足跡;Snv為指在引水水電站修建長距離引水管道工程而造成的植被破壞區域。
2.4.5 單引水小水電的土壤侵蝕。
引水式小水電站的水土流失主要是由于長距離引水管道工程的建設造成的。單個引水水電站的土壤侵蝕足跡可按以下模型計算:
式中:EFe為單引水水電站的土壤侵蝕足跡;Se為長距離引水管道工程施工引起的土壤侵蝕面積,hm2。
2.4.6 梯級引水小水電的土壤侵蝕。
梯級引水小水電站的土壤侵蝕足跡為單個引水小水電站的土壤侵蝕足跡之和:
式中:EFne為n梯級引水式小水電的土壤侵蝕面積;Sne為n梯級引水式小水電中修建長距離引水管道工程而產生的土壤侵蝕面積,hm2。
2.5 環境影響的判斷
通過ESF 和ELF 的比較,可以定量分析引水式小水電站的環境影響。生態供給的數值加上生態損失的數值得出的積極結果表示引水式小水電對環境的有利影響,兩者之間的差異越大表示積極影響越大。負面結果表示引水SHP 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兩者之間的差異越大,負面影響越大。
3 結果和討論
圖1中給出了單引水小水電的ESF 和ELF,其計算符合基于表1 數據的公式(1)、(3)、(5)和(7)。在本研究中,ESF 值范圍為3.24 ~37.26 hm2,ELF 值范圍為4.88 ~19.65 hm2。對于H1、H4、H5和H6 的單導流SHP,ESF 超過ELF,而對于H2、H3 和H7,ESF 小于ELF(圖2)。從單引水小水電的角度來看,大多數項目對環境有積極影響,少數項目有輕微的負面影響。

圖1 單引水水電站ELF 和ESF 的比較
圖2給出了梯級引水SHP 的累積ESF 和ELF,其計算符合基于表1 數據的公式(2)、(4)、(6)和(8)。對于梯級引水水電站,隨著水電站數量的增加,累積ESF 和ELF 顯著增加。累積ESF 值在15.93~122.41hm2之間,累積ELF 值在15.00~172.47 hm2之間。研究區域內2、3、4 級引水小水電的累積生態損失與供給之間沒有顯著差異。但對于5、6、7 級引水小水電來說,累積生態損失與供給之間的不平衡是明顯的。隨著引水式小水電站數量的增加(n >4),生態損失和供給之間的差異明顯增大,表明梯級引水式小水電的不利影響將在研究區域內累積。

圖2 梯級引水水電站ELF 和ESF 的比較
對于梯級引水小水電,生物和凈生產力的累積損失是最大的生態損失,占總損失的52.3%~85.1%(圖3)。

圖3 梯級引水水電站ELF 的組成
隨著引水水電站數量的增加,魚類和凈生產力累積損失在總生態損失中所占的比例逐漸增加。魚類和凈生產力的累積損失增加表明,梯級引水SHP造成的更多減水段可能會對水生生態系統造成巨大的不利影響。因此,梯級引水水電開發的魚類和凈生產力損失需要更多的關注。與魚類和凈生產力相比,累積植被破壞(8.3%~25.0%)和土壤侵蝕(6.8%~22.7%)相對較小。這表明,在研究區域的梯級引水SHP 開發過程中,植被破壞和土壤侵蝕不會像魚類和凈生產力損失那樣嚴重。
4 結 論
EF 分析方法可用于定量評估梯級開發引水小水電的累積環境影響程度。根據建立的評價模型,計算了該地區梯級引水水電站的ESF 和ELF。在本研究中,ESF 和ELF 在梯級引水SHP 中表現出相似的變化趨勢。對于<4 級(n ≤4)的引水小水電,累積ESF 和ELF 之間沒有顯著差異。隨著引水式水電站數量的增加(n >4),ELF 和ESF 之間的差異明顯增大,表明梯級引水式水電站的不利影響在研究區域積累。與植被破壞和土壤侵蝕相比,魚類和凈生產力的累積損失是梯級引水水電不利影響的最重要方面,需要引起更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