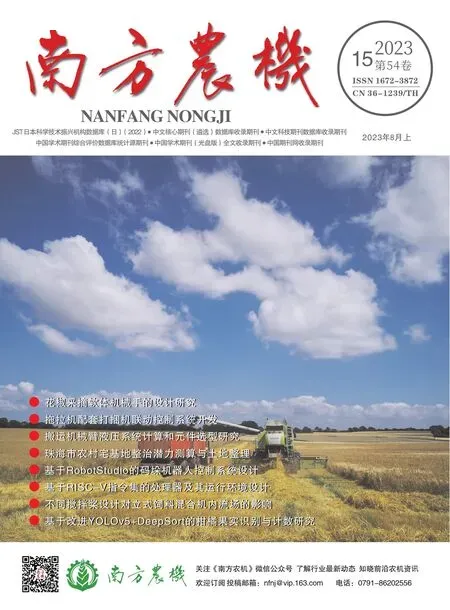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實現(xiàn)可持續(xù)增收的路徑研究
尚果卓麻 ,達巴姆
(西藏大學(xué),西藏 拉薩 850000)
1 概念界定與現(xiàn)狀分析
2020 年底,我國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wù),歷史性地消除了絕對貧困,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實現(xiàn)了黨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現(xiàn)行標準下9 899 萬農(nóng)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極大地改善了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水平,有力提升了低收入群體抵御未知風險的能力。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shù)大、區(qū)域之間發(fā)展不平衡等原因,仍存在較大規(guī)模的低收入群體,其收入水平與中高收入群體有較大差距,同時面臨著欠收和增收的可持續(xù)性等問題。因此,在實現(xiàn)共同富裕的進程中,如何使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實現(xiàn)增收的可持續(xù)性,徹底擺脫返貧風險顯得至關(guān)重要。
1.1 低收入群體的內(nèi)涵
國際上的低收入群體特指收入水平低于社會普遍收入的群體;國家統(tǒng)計局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為五組,把處于最底部的20%稱為低收入群體;林閩鋼[1]認為低收入群體不僅與經(jīng)濟收入掛鉤,還是社會中“最少受惠者”的代表,同時也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點保障對象;楊立雄[2]將低收入群體界定為家庭收入處于低收入線以下的人口(處于國家統(tǒng)計局界定的收入水平底部的20%),認為國家在促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過于重視區(qū)域差距,而忽視了群體間的差距,其中的群體差距主要是指低收入群體與中高收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楊穗[3]將低收入群體分為相對貧困人群(各級政府的救助對象)和收入水平與當前中等收入群體的下線相差不大的潛在中等收入群體。綜合以上各定義,本文將低收入群體界定為收入水平處于社會中等收入水平以下,且大部分收入來自政府轉(zhuǎn)移支付的受社會救助的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在以往的文獻中專門針對低收入群體可持續(xù)增收的研究較少,但要想實現(xiàn)共同富裕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低收入群體僅僅依靠社會保障暫時擺脫絕對貧困狀態(tài)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本文將以如何實現(xiàn)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增收的可持續(xù)性為研究對象展開研究。
1.2 我國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現(xiàn)狀
2021 年我國基本建成低收入人口數(shù)據(jù)庫,形成了一個動態(tài)監(jiān)測信息平臺。該平臺顯示,截至2021年底,全國農(nóng)村低收入保障對象為3 474.2 萬人,農(nóng)村特困救助對象為437.8 萬人;享受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的人數(shù)分別為1 187.3 萬人和1 499.2 萬人,為17.2 萬孤兒提供兒童社會福利,全年實施臨時救助1 089.3萬人次[4]。
目前,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規(guī)模龐大,其內(nèi)部收入差距也較為明顯。農(nóng)村居民收入水平及相對收入差距如表1 所示,2021 年五等份分組的農(nóng)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4 856 元、11 586 元、16 546 元、23 167元和43 082 元,按國家統(tǒng)計局2021 年中等偏下收入群體的1.8 萬元的標準來看,農(nóng)村仍有超過60%的人群是低收入群體。2021 年,全國農(nóng)村收入最低的20%群體的收入只有平均收入的25.7%,中間偏下的20%群體的收入是平均收入的61.2%,中間的20%群體的收入為平均收入的87.4%。最高的20%與最低的20%群體的收入差距仍然較大,最高的20%與中等偏下的20%群體的收入差接近4 倍[5]。

表1 農(nóng)村居民收入水平及相對收入差距
2 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實現(xiàn)可持續(xù)增收的必要性
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一般都具有受教育程度低、家庭負擔重、掌握的生產(chǎn)技能少、收入渠道單一、家庭勞動力少、就業(yè)穩(wěn)定性差等顯著特征[6],同時,有研究發(fā)現(xiàn),扶貧制度下的低收入群體與社會救助制度下的低收入群體存在一定的重合,皆包含由于重大疾病或突發(fā)事件導(dǎo)致貧困的支出型困難家庭[3]。羅楚亮等[7]通過對農(nóng)村住戶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在1995—2017 年期間的轉(zhuǎn)移凈收入呈持續(xù)增長趨勢。根據(jù)民政部相關(guān)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截至2021 年底,全國農(nóng)村最低生活保障戶數(shù)為1 944.9 萬戶,全國農(nóng)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標準為每人每年6 362.2 元[4]。從2020—2021 年的收入數(shù)據(jù)來看,農(nóng)村低收入家庭(最低的20%)人均純收入從4 681 元增加到4 856 元,年均增長率不到4%。
以上數(shù)據(jù)表明,農(nóng)村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為社會救助類的政府轉(zhuǎn)移性支付,黃征學(xué)等[8]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我國有將近兩成的低收入群體依賴轉(zhuǎn)移性收入,而這類收入隨著脫貧攻堅的結(jié)束增長速度緩慢且未來的增長空間有限。因此,在解決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實現(xiàn)可持續(xù)性增收這一問題時應(yīng)從激發(fā)這一群體的內(nèi)生動力出發(fā)。
3 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實現(xiàn)可持續(xù)性增收的路徑
人的生活不能完全依靠社會保障,還要靠自身的努力,而且一個人得到的社會保障越多,自身的努力往往就越少[9]。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的可持續(xù)性面臨的首要問題便是這一群體的內(nèi)生動力不足,長期處于“等、靠、要”的狀態(tài),自身尚未完全形成創(chuàng)造財富的能力。現(xiàn)行反貧困的救助方法主要是通過社會保障制度來保證低收入群體的生存權(quán)利,保障方式簡單易行,單一的現(xiàn)金轉(zhuǎn)移支付的保障方式雖在短期內(nèi)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從發(fā)展的長期性來看,不利于被救助者及其家屬的能力建設(shè)。因此,結(jié)合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的特征,政府應(yīng)在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同時,通過不斷投資其人力資本,提升其技能、知識和健康素質(zhì)等綜合水平,來實現(xiàn)這一群體增收的可持續(xù)性。
3.1 加強農(nóng)村基礎(chǔ)教育,增強人力資本
在初次分配中,除無勞動能力的殘疾人以外,低收入群體中身體素質(zhì)差、技能水平低的弱勞動能力者在勞動力市場中處于弱勢地位,同時有研究表明,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能明顯降低其貧困的脆弱性,這一點在貧困家庭中尤為明顯[10]。因此,首先要加強農(nóng)村的基礎(chǔ)教育,追蹤監(jiān)測農(nóng)村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入學(xué)率、升學(xué)率,有效消除低收入家庭子女的輟學(xué)率,保證其完成義務(wù)教育,增強子女的人力資本,阻斷貧困在代際之間的傳遞;其次,政府在加大對職業(yè)教育的投入力度的同時,應(yīng)對文化水平較低的、符合勞動年齡且具有勞動能力的低收入人群進行有針對性的、與市場需求相匹配的職業(yè)技能培訓(xùn),強化生產(chǎn)技能,減少其受外部沖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有效增強低收入群體的市場競爭力,增加其靈活就業(yè)機會,通過提高工資性收入來擺脫自身目前較弱的社會地位,提高生活水平。
3.2 因地制宜發(fā)展產(chǎn)業(yè),增加就業(yè)機會
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除了受其本身微觀因素影響以外,還受宏觀因素,如地區(qū)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經(jīng)濟增長速度以及產(chǎn)業(yè)政策等的影響。區(qū)域之間的發(fā)展水平也制約著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的發(fā)展,因此要加快區(qū)域發(fā)展一體化,縮小城鄉(xiāng)差距。首先,農(nóng)村地區(qū)可因地制宜發(fā)展特色產(chǎn)業(yè),充分利用農(nóng)村資源條件,如青海、西藏等地的農(nóng)牧區(qū)可依托農(nóng)牧業(yè)與生態(tài)環(huán)境優(yōu)勢,發(fā)展牛羊繁育、絨毛加工、中藏藥藥材種植等特色產(chǎn)業(yè),進一步縮小地區(qū)之間的發(fā)展差距;其次,農(nóng)村在發(fā)展特色產(chǎn)業(yè)的同時,政府可在這些產(chǎn)業(yè)的加工、運營、零售等具體部門設(shè)立公益性崗位,為參加職業(yè)技能培訓(xùn)且培訓(xùn)成績合格的低收入群體提供更多對口的就業(yè)崗位,實現(xiàn)低收入群體經(jīng)濟收入的穩(wěn)步增長;最后,通過以縣域為切入點,增強城市與農(nóng)村之間資源的自由流動,包括人才、資金、技術(shù)等要素的順暢流通,建立城鄉(xiāng)互補、工農(nóng)互促、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新型和諧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
3.3 改革社會福利方式,激發(fā)工作熱情
隨著社會保障服務(wù)的覆蓋面越來越廣和現(xiàn)金轉(zhuǎn)移支付水平的不斷提升,兜底保障對象易產(chǎn)生福利依賴性,進而導(dǎo)致其尋找工作的概率降低[11]。因此,在實施社會救助的過程中,要注意福利制度的門檻不宜過低,遵循分層分類分群的原則實施紓困幫扶。首先,對于有勞動能力的低收入群體實行的紓困幫扶應(yīng)是暫時性的,讓其實現(xiàn)就業(yè)和再就業(yè)才是提高可持續(xù)生計發(fā)展能力的重要保障[1]。針對有就業(yè)能力的福利受益者,可將其所受福利待遇與其參與職業(yè)技能培訓(xùn)的時長和培訓(xùn)結(jié)業(yè)成績掛鉤,同時對其享受福利待遇的時間做出合理規(guī)劃,防止出現(xiàn)“搭便車”現(xiàn)象。其次,構(gòu)建正向的就業(yè)激勵機制,對于主動尋求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機會的受福利待遇的低收入人口給予物質(zhì)和精神的雙重獎勵。再次,針對無勞動能力的老人、孩童和殘疾人群建立專項幫扶資金,減輕其家庭養(yǎng)老和育兒負擔。最后,政府應(yīng)為尋求就業(yè)和完成就業(yè)的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提供良好的就業(yè)保障,建立并完善就業(yè)和再就業(yè)保障制度,幫助其更好地實現(xiàn)充分就業(yè)和穩(wěn)定就業(yè)。
3.4 加大衛(wèi)生醫(yī)療救助力度,保障健康素質(zhì)
貝克爾在其人力資本理論中提出,不僅勞動力的技能和知識水平是推動經(jīng)濟增長的巨大動力,而且其健康素質(zhì)更是能夠為個人、家庭乃至社會長期創(chuàng)造財富的最有力的投資。因此,政府應(yīng)該在公共衛(wèi)生服務(wù)和基本醫(yī)療方面給予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全方位的生命健康保障,解決低收入群體在生活和就醫(yī)等方面的困難。首先,可在目前農(nóng)村醫(yī)療報銷比例的基礎(chǔ)上再進行提升,擴大其報銷范圍,減少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在醫(yī)療方面的剛性支出。同時,推進基本醫(yī)療保險跨省異地結(jié)算,簡化醫(yī)療保險異地報銷程序。其次,政府應(yīng)攜手各級醫(yī)療部門對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制定定期的體檢計劃,有效減少這一群體因病返貧或因病“丟薪”現(xiàn)象發(fā)生。最后,在鞏固原有醫(yī)療保障的基礎(chǔ)上,擴大以農(nóng)民工為重點參加社會保險的范圍,合理引導(dǎo)其參加職工基本醫(yī)療保險和職工基本養(yǎng)老保險,敦促用人單位為就業(yè)低收入群體繳納各類保險費用,讓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真正實現(xiàn)看病無憂,安心用心奉獻于工作崗位,實現(xiàn)經(jīng)濟增收的可持續(xù)性。
4 結(jié)語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體現(xiàn),近年來黨中央和各級政府也在“提低擴中”上擼起袖子加油干,但僅依靠社會保障來實現(xiàn)共同富裕,實現(xiàn)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增收的可持續(xù)性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是無以為繼的。要明確認識到,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改變自身生活狀況的主體應(yīng)是其自身。因此,更重要的是激發(fā)低收入群體的內(nèi)生動力和發(fā)展?jié)摿Γ浞终{(diào)動這一群體改變自身狀況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培養(yǎng)農(nóng)村低收入群體自尊、自強、自立精神,以此增強其抵御未知風險的能力,降低其致貧返貧的可能性,早日實現(xiàn)發(fā)展和增收的可持續(x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