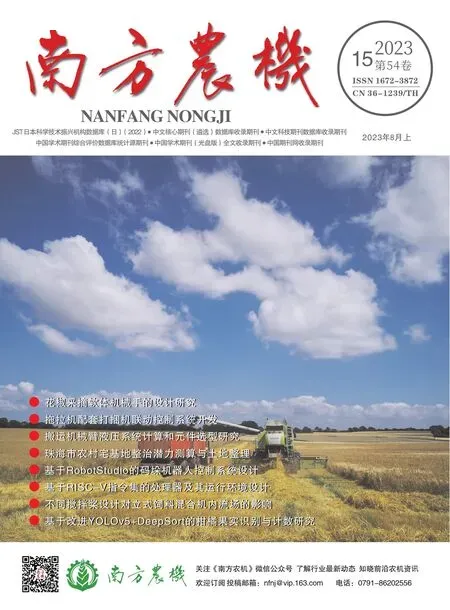不同滲漏強度下兩種水稻節(jié)水灌溉控制指標對比研究
周姣艷 ,馬創(chuàng)業(yè)
(1.昆山市水務水文調度中心,江蘇 蘇州 215300;2.昆山水務工程建設管理處,江蘇 蘇州 215300)
0 引言
在我國,水稻常年種植面積高達3 000萬hm2,約占全國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約占全球水稻種植面積的五分之一[1]。截至2019 年年底,我國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shù)為0.559,與發(fā)達國家相比仍具有較大差距[2],因此推行稻田節(jié)水灌溉制度對我國農業(yè)節(jié)水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已推行的水稻節(jié)水灌溉技術有間歇灌溉、淺濕灌溉、控制灌溉、薄露灌溉等[3-5],主要特點是使水稻在某些生育期內保持田面無水層或使稻田土壤處于非飽和狀態(tài)。在節(jié)水灌溉制度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灌水時間與灌水量主要由灌水下限決定,而灌水下限主要通過土壤水分傳感器等儀器進行監(jiān)測。但儀器測量結果的精確程度易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徐愛珍等[6]的研究結果表明,TDR法測定土壤含水率的絕對偏差和相對偏差隨著土壤含水量的增大而減小,土壤含水量在半濕潤條件下偏差最大;孫蕾等[7]也發(fā)現(xiàn)中子法只能測出較深土層中的水,而不能用于土表的薄層土。儀器不僅存在監(jiān)測精度低的問題,其購買成本和維護費用也很高,這使其難以在水稻種植區(qū)內推廣應用。為使農民能更簡便快速地掌握水稻的水分虧缺狀況,有研究采用足跡深度、稻田裂縫程度等土壤描述性指標[8],以此解決設備成本過高、監(jiān)測精度低等問題,但上述指標主要依靠農民的經驗判斷,其精確性無法保證,用其指導水稻灌溉尚存在明顯缺陷。
為解決上述問題,少量研究已經開始關注以地下水埋深指導灌溉,徐俊增等[9]采用Hydrus-1D 模型模擬結果得出,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的控制下限來指導灌溉,可以準確反映田間水分狀況,但實際種植效果尚不明確。本文采用盆栽實驗,設置不同滲漏情況下的土壤環(huán)境,以此探究水稻生長發(fā)育情況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與以土壤含水率為指標指導灌溉的差異性。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概況
試驗在黑龍江省慶安縣和平鎮(zhèn)水稻灌溉試驗中心(125°44'E、45°63'N)內進行,試驗區(qū)地處寒溫帶大陸性氣候區(qū),年降雨集中在7—9 月,多年平均降雨為579 mm。當?shù)厮旧L期一般為5 月中旬至10 月初,試驗地土壤類型為寒地黑土。
1.2 試驗設計
試驗采用直徑50 cm、高60 cm 的圓柱形桶進行盆栽試驗。桶內裝土深度為50 cm,根據(jù)田間容重按5 cm 一層回填、夯實。桶底設置厚度為5 cm 的細沙濾層,內設透水管,透水管通過筒壁連接一控制閥門,通過閥門開度控制滲漏強度,即在觀測期內每2 h 打開閥門排出定量的水,水量由滲漏強度換算成每2 h 的排水質量,借助天平稱重實現(xiàn)排水量的精確測量。
試驗通過控制圓桶底部的閥門開度設置3 種滲漏強度,即1 mm/d、2 mm/d、3 mm/d,分別用D1、D2、D3 表示,每種滲漏強度下均設置以土壤含水率為指標(W1)和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W2)的控制灌溉模式來指導灌溉,各生育期控制指標如表1 所示。試驗共設置6個處理,每個處理設3次重復。

表1 不同耗水強度下水稻控制灌溉不同生育期土壤含水率和地下水埋深控制指標
試驗水稻品種為龍慶稻9 號,種植密度為30 cm×15 cm,田間管理按當?shù)厮痉N植習慣進行管理。全生育期總施氮量為110 kg/hm2,按照基肥∶蘗肥∶穗肥=5∶3∶2 的比例施用;P2O5施45 kg/hm2,作基肥一次施用;K2O 按80 kg/hm2分別在基肥和幼穗分化期以1∶1 的比例施用兩次。5 月19 日移栽,9 月22日收割。
1.3 項目測定與方法
1.3.1 灌水量
在試驗期內,每個圓柱形桶單獨灌溉,在達到土壤表層有薄水層且排水管內水位與圓柱形桶內水位齊平時停止灌溉,采用量杯灌水,記錄灌水總量。若在觀測期內遇降雨且雨后桶內水層高度超過3 cm,記錄初始水層高度,土表排水至水層高度為3 cm。降雨量由氣象站直接給出,利用水量平衡計算方法,減去土表排水量,即為灌溉量。若在降雨后土表無水層,降雨量即為灌溉量。
1.3.2 土壤含水量
采用TDR 測量,烘干法校核。烘干法測土壤含水量時,在試驗觀測周期內,土壤樣品每日8:00 用土鉆取土;在觀測周期外的過渡期,每2 d 取一次土樣。取樣深度為40 cm,截取0~5 cm、5 cm~10 cm、10 cm~15 cm、15 cm~20 cm、20 cm~25 cm、25 cm~30 cm、30 cm~35 cm、35 cm~40 cm 共8 段,每段樣本取出后均用密封袋包裝,帶回實驗室。烘干溫度為105℃,烘干時間為8 h,烘干前后土壤重量用高精度電子天平稱得。取土后需要及時填土,填土質量必須與取土質量相等。
1.3.3 地下水埋深
地下水埋深觀測利用安裝在桶內的水位計自動監(jiān)測,定期讀取數(shù)據(jù)并保存。
1.3.4 水稻生長指標
在水稻生長期內,每隔5 d 觀測一次植株株高、分蘗數(shù),在分蘗期需加大分蘗數(shù)觀測頻率,可每隔2 d 觀測一次分蘗數(shù)。葉面積每隔10 d 觀測一次,采用長寬系數(shù)法測定盆栽內所有植株,測量葉片的長與寬。在收割前考察有效穗數(shù)、每穗粒數(shù)、實粒數(shù)、千粒重,各處理單打單收,曬干揚凈后,測定實際產量,確定灌溉水分利用率。
2 結果分析
2.1 水稻分蘗數(shù)與株高變化規(guī)律
水稻全生育期分蘗數(shù)與株高變化規(guī)律如圖1 所示,從圖1(a)中可以看出,所有處理下水稻分蘗的變化規(guī)律基本一致,均呈現(xiàn)出隨生育期的推進先增大后逐漸減小的變化規(guī)律。相同滲漏強度下,在分蘗中后期前所有處理增長速率均一致,W2 處理下的分蘗數(shù)略高于W1 處理。分蘗中后期,所有處理的分蘗速率均加快,W2 處理下的分蘗速率均明顯高于W1 處理,分蘗數(shù)均達到峰值,兩種灌溉指標下分蘗數(shù)達到峰值的時間基本一致,但W2 處理下的分蘗數(shù)峰值與W1 處理相比顯著增加,二者峰值在不同的滲漏強度處理D1、D2、D3 下的差異分別為16.48%、15.65%、16.67%。拔節(jié)孕穗期水稻分蘗進入消退期,分蘗數(shù)逐漸減少直至趨于穩(wěn)定,但相同滲漏強度下,W2 處理的最終分蘗數(shù)均大于W1處理。

圖1 不同水分處理下的水稻全生育期分蘗數(shù)與株高變化規(guī)律
兩種灌溉指標在不同滲漏強度下的水稻株高變化并無明顯差異,如圖1(b)所示。分蘗期—拔節(jié)孕穗期時,各處理生育前期株高增長迅速。進入抽穗開花期后,株高增長速率變緩直至趨于平穩(wěn),此時,相同滲漏強度下,W2 處理下的水稻株高均略高于W1處理。
2.2 葉面積指數(shù)變化規(guī)律
所有處理中水稻的LAI 變化規(guī)律同莖蘗動態(tài)規(guī)律相似,如圖2 所示。分蘗前期LAI 較低,進入分蘗中后期,隨著莖蘗的增加和葉片的生長,LAI 快速增大,在拔節(jié)孕穗后期—抽穗開花期達到全生育期的最大值。在滲漏強度相同的情況下,W2 處理下水稻LAI 峰值均高于W1 處理,兩者峰值在不同的滲漏強度處理D1、D2、D3 下差異分別為8.91%、19.67%、17.91%。此后因無效莖蘗消亡、葉片衰敗等原因,LAI 逐漸降低,W2 處理的最終LAI 仍高于相同狀態(tài)下的W1 處理。最大葉面積指數(shù)和最終葉面積指數(shù)在兩種灌溉指標處理下的對比顯示,D1 處理的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的控制灌溉下過大的最大葉面積指數(shù)也伴隨著較大的后期葉面積消亡,D2 處理和D3 處理下的兩種灌溉指標的葉面積消亡基本一致。

圖2 不同水分處理下的水稻全生育期LAI變化規(guī)律
2.3 水稻干物質累積
不同處理下水稻生育期的干物質累積量如圖3 所示,由圖可知,隨著水稻生育進程的推進,水稻干物質累積量不斷增大。在同一滲漏強度處理下,除分蘗中期外,處在相同生育期的水稻干物質累積量W2 處理均略高于W1 處理。D1 處理下,分蘗中期,相同滲漏強度下兩種灌溉指標的干物質累積量均相差不大;分蘗后期,由于分蘗數(shù)峰值的差異較大,W2 處理下的干物質累積量比W1 處理高7.69%;拔節(jié)孕穗期,葉面積峰值差異較大,W2 處理下的干物質累積量比W1 處理高9.32%;而后,伴隨無效莖蘗和葉面積的消亡,兩種灌溉指標的差異逐漸縮小,可以看出,W2 處理下的無效莖蘗和葉面積的消亡高于W1 處理,D2、D3 處理的差異并不顯著。成熟期,水稻干物質累積量達到最大,W2 處理下的最大干物質累積量與W1 處理在不同滲漏強度D1、D2、D3 下的差異分別為4.07%、3.28%、2.02%。

圖3 不同處理下水稻生育期的干物質累積量
2.4 水稻產量及灌溉水利用率
在相同滲漏強度下,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的控制灌溉產量均大于以土壤含水率為指標的控制灌溉產量,如表2 所示。D3 處理下的兩種灌溉方式產量相差最大,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控制灌溉下的水稻比以土壤含水率為指標控制灌溉下的水稻增產14.60%,D1 和D2 兩種滲漏強度下W2 相比W1 分別增產7.82%、3.80%。兩種灌溉方式均表現(xiàn)為滲漏強度越大,水稻產量越低。這可能是由于滲漏強度大的處理容易造成化肥等養(yǎng)分流失,作物得不到充分的養(yǎng)分補給,使得產量下降。由顯著性分析可知,在D1 和D3滲漏強度下,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的灌溉方式下的水稻產量與以土壤含水率為指標的灌溉模式下的水稻產量差異顯著,表明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的灌溉方式相比以土壤含水率為指標的灌溉方式具有更大的產量效益。在三種滲漏強度下W2 的灌水量均略高于W1,但相差小于5%。而對于灌溉水利用率,在D3滲漏強度下,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的灌溉方式相比以土壤含水率為指標的灌溉方式具有更高的IWUE,其他兩種滲漏強度下則無明顯差異。

表2 不同處理下水稻產量及其構成因素
3 結論與討論
研究結果表明,將兩種節(jié)水灌溉技術下的水稻在作物生理生長、灌水量及水分生產率等方面進行比較,在節(jié)水和增產層面上兩者并無顯著差異,表明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的控制灌溉能達到精準灌溉與提高灌溉水利用率的目的。
在此次試驗中,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控制灌溉的水稻最大分蘗數(shù)及有效分蘗數(shù)均比以土壤含水率為指標的控制灌溉下的水稻大,這意味著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的控制灌溉比以土壤含水率為指標的控制灌溉更能促進水稻分蘗;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控制灌溉的水稻株高均大于以土壤含水率為指標控制灌溉的水稻,在滲漏強度相同的情況下,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的控制灌溉比以土壤含水率為指標的控制灌溉更能促進水稻葉面積增大。但滲漏強度越大,LAI 峰值越小。隨著滲漏強度的增大,水稻的最終產量越低,這與欒雅珺等[10]的研究結果一致,造成此原因的結果可能是由于滲漏強度大的處理容易造成化肥等養(yǎng)分流失。
土壤含水率和田間無水層天數(shù)是水稻節(jié)水灌溉技術的主要控制指標[11-13],目前已經得到較廣的推廣應用,但是在成本投入和數(shù)據(jù)可靠性等方面仍存在很大的缺點。本研究通過對以地下水埋深和以土壤含水率為控制指標的兩種節(jié)水灌溉技術下的水稻生長及水分利用率進行對比,發(fā)現(xiàn)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的控制灌溉對于水稻生長并無不良影響,而同價位的水位計測量精度遠遠高于土壤水分傳感器。因此,以地下水埋深為指標的控制灌溉遠遠優(yōu)于以土壤含水率為指標的控制灌溉,使用地下水指導灌溉更有利于推廣節(jié)水灌溉。但本試驗結果僅限于東北黑土地區(qū),對于不同地區(qū)的節(jié)水灌溉地下水位下限仍需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