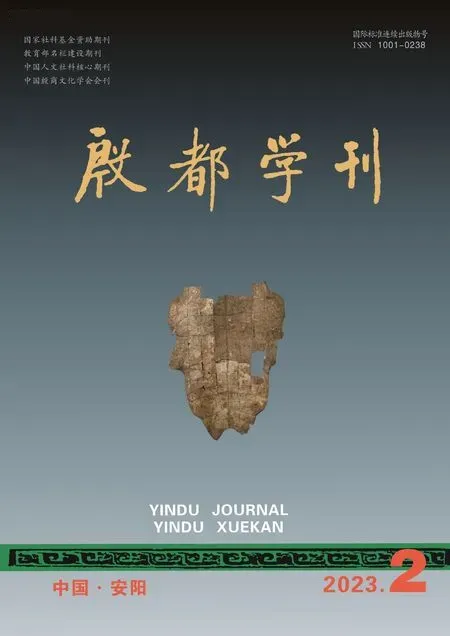金文所見商周宗族秩序的建構
黃國輝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0875)
宗族秩序是宗族內部親屬成員之間關系的規范化。商周是宗法封建社會,在此社會中,親族血緣是基礎,等級政治是靈魂。宗族族長對宗族內部成員具有制約和領導的權力,承當著維護宗族秩序的職責,在經濟和政治上處于主導支配地位,而普通宗族成員則需要遵從族長的權威和領導。宗族族長與其成員之間的這種等級關系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君臣關系。在宗族內部,宗族首領既是宗,又是君,而其他宗族成中成員既是親,又是臣。這種等級上的君臣關系體現在宗族內多重的親屬關系中。朱鳳瀚先生較早就西周貴族家族內部親屬等級關系的政治化進行過精彩的討論,曾舉例分析過其中的父子、兄弟之間的君臣關系。(1)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09頁。近年來,伴隨金文材料的不斷豐富和青銅銘文研究的日益深入,宗族內部親屬關系的政治化問題也表現得愈加豐富,筆者此處在朱鳳瀚先生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補充完善。試析如下:
一、父子關系
西周早中期“效尊”(《集成》6009)銘文記:
唯四月初吉甲午,王觀于嘗,公東宮納饗于王。王錫公貝五十朋,公錫厥世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用作寶尊彝。嗚呼,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亦其子子孫孫永寶。
銘文大意是說,四月初吉甲午這天,周王在嘗地游覽。事畢,公在東宮招待了周王。周王賞賜給公五十朋貝。公轉賜給自己的世子效二十朋。效很感謝公的賞賜,做了這件珍貴的器物。這件“效尊”傳出洛陽,現藏日本神戶白鶴美術館。與之同銘的還有一件“效卣”(《集成》5433),現藏上海博物館。朱鳳瀚先生曾指出,世子效(2)“世子”一詞當從楊樹達先生的考釋。見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中華書局,1997年,第85頁。在其父(公)賞賜了王所賜的貝后,要對揚其父之休,并且使用了“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的語句,而這些詞語在西周器銘中多適用于王臣對王、家臣對家主。由此可見,父子關系在西周貴族家族中是嚴格的等級化,類同于主臣關系。這是宗法性質的父家長權力的升華。(3)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第310頁。朱先生是從語句的對比上說明西周貴族家族中父子關系的政治化,結論可信。這里還想補充的是稱謂的角度。實際上“公”的稱謂也可以說明這一點,青銅銘文中的大部分“公”都應該訓為“君”。《爾雅·釋詁上》:“公,君也”。“公”就是“君長”的意思。“公”釋為“君”在金文中還有類似“公”“君”連用的情況,見后文。“世子效”稱自己的父親為“君長”,正說明了二者關系的政治化。


銘文中“諸子”指的是滕公的子輩,可能包括了滕公的兒子和侄子等,他們也包含在了“朕臣”的范圍內,一并受到滕公的賞賜。可見身為父輩的滕公和作為子輩的“諸子”之間不僅有親緣上的關系,同時更是有著君臣上的等級秩序。
二、兄弟關系
西周中期的“豦簋”(《集成》4167)銘文記:
豦拜稽首,休朕寶君公伯賜其臣弟豦井五糧,賜胄、干戈。豦弗敢望(忘)公伯休,對揚伯休,用作祖考寶尊彝。
朱鳳瀚先生指出,豦稱其兄為“君”,而豦又自稱“臣弟”,在接受公伯賞賜后“對揚伯休”,亦表明貴族家族內作為宗子的長兄對于作為小宗的諸兄弟之間的宗法等級關系,已采取了政治上的君臣隸屬關系的形式。(6)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10頁。這是很可信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除了“臣弟”以外,這里“寶君公伯”的稱呼很值得注意,“寶”,貴重之意。“君”“公”同義,是就其作為君長的政治地位而言的。“伯”,長也,是就其作為宗族首領的地位而言的。可見,豦和宗族長的關系依然是雙重的。身為宗族長的“公伯”既為君,又為宗;而作為族人的豦既是子弟,又是臣子。
三、夫妻關系
商代晚期的“麋婦觚”(《集成》7312)銘文記:

銘文大意指,在五月丁亥,“庚姬”受到“帝后”的賞賜,并因此做了珍貴器物來祭祀她日名為丁的丈夫。類似的銅器在西周時期也可以見到,如現藏國家博物館的西周早中期青銅器“南姞甗”(《銘圖》3355)記:
銘文大意是說,南姞為她的丈夫伯氏做了件珍貴的器物,用來祭祀祈福。


“辟”訓為“君”,訓為“長”,在商周時期往往也是臣子對自己上級君長的常用稱呼,完全能夠體現政治上的等級關系。這種情況無論是在出土文獻還是典籍材料中都是較為常見的,茲不贅引。作為妻子,商周時期的女性卻經常用“辟”(君也)這種尊稱來稱呼自己的丈夫,表現出夫婦之間在等級上的尊卑關系。
四、伯/叔侄關系
西周早期的“榮簋”(集成05997)銘文記:
唯正月甲申,榮格,王休賜厥臣父榮瓚、玉祼、貝百朋。對揚天子休,用作寶尊彝。
銘文大意是說,在正月甲申這天,榮來了,王賞賜給他瓚、玉祼和百朋貝等,榮因此做了這件珍貴的器物。在“榮簋”中,王稱榮為“臣父”,可見作器者榮當是周王的父輩,或為叔父,或為伯父。但他相對于王來說,又必須自稱臣。王雖是榮的侄兒,但同時也是他的君上。親緣關系之外籠罩著厚厚的君臣之間的等級關系。
五、在世者與其故去直系祖先的關系
西周晚期的“師克盨”(《集成》4467)銘文記:

本段銘文中,“經”,典范也。“克令臣先王”中的“克”不是器主“師克”,應當是“能夠”的意思,主語仍然是前文的“王”。“令”,善也。“王曰:克,余唯經乃先祖考,克令臣先王”這句話的大意指,王說:師克,我要以你的祖考們為典范,我要學習他們能夠很好的作先王的臣子。這句銘文中的“臣”字非常重要,它不僅體現出生前作為臣子的師克祖先們在死后仍然要和時王故去先祖之間保持這種君臣關系,同時也表明即便作為在世的“王”對于自己故去的祖考先王,仍然要俯首稱“臣”,所以“王”才會說自己要像師克的祖先們那樣,臣事自己的先王。對于自己故去的祖先來說,時王是子是孫。這也就是說,親屬之間這種生前的“君臣”關系,可以一直延續到死后。
六、宗族首領與宗族子弟的關系
商末時器“小子省卣”(《集成》05394)記:
甲寅,子賞小子省貝五朋,省揚君,用作父己寶彝。
“子”指的是宗族首領,“小子省”是他的宗族子弟。銘文大意是說,甲寅這天,作為宗族首領的“子”賞賜給身為宗族子弟的“小子省”五朋貝,“小子省”因此做這件器物,用來祭祀自己日名為己的父親。作為宗族子弟的“小子省”在受到宗主的賞賜后稱他的宗主為“君”。可見,對于宗主來說,族內的子弟既是其族人,又是其臣。反之,對于宗主子弟來說,他的族長既是宗,又是君。
以上材料包括了王室、諸侯和普通貴族的情況,上及商代,下到西周晚期,涉及到家族中多個方面的關系,為我們研究商周宗法的變遷提供了寶貴資料。(8)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材料主要體現的是宗主和其他家族成員之間的親緣關系和政治關系。除宗主以外,宗族內部其他成員之間的關系是否存在這種等級的政治關系,我們目前沒有發現明確的證據。以下筆者分普通家族(包括貴族家族)和王室家族兩個層次來討論。試析如下:
筆者以為,商周宗法制度的一個重要變遷就是君臣關系逐漸走出家族的范圍,(9)這里的“家族”主要是指普通家族(包括貴族家族),王室家族情況特殊,見后文。趨向為國君與其國人之間的等級稱謂。從上述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貴族宗族內部,宗統和君統是合二為一的。宗主和其他家族成員之間既有親緣關系,又有等級政治關系,二者是明顯共存的。君長沒有排斥自己作為家族首領的身份,而作為普通家族成員的臣子也可以積極標明自己和君主之間的親緣關系。親緣關系的政治化非常顯著。但在后世家族中,這種顯著的宗法關系逐漸發生轉變,親緣關系的政治化大為弱化,用于宗主與其家族成員之間的君臣稱謂逐漸消失。戰國以后,古代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劇烈變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游離于宗族之外,同時伴隨著戰國以后君權的日益強大,尤其是編戶齊民以后,國家逐漸取代宗族,對普通民眾的控制日益加強,君臣關系逐漸固化為國君與其他成員之間的等級稱謂。即便是在貴族家族,宗主和普通家族成員之間也不再像商周時候可以君臣相稱。君臣稱謂走出宗族的籓籬,逐漸固化為君王和其他成員之間的等級稱謂,這是后世君權發展的必然。后世宗族雖在,在某些特殊的歷史階段,甚至依然強大,但其間的宗法關系卻已經大大的弱化了。
與上述普通宗族不同的是,在王室家族內部,這種親緣關系的政治化卻變得更為強烈,形成了更為森嚴的等級秩序。晚出的《禮記·大傳》記:“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鄭玄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于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也。”孔穎達疏:“此一經明人君既尊,族人不以戚戚君,明君有絕宗之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屬上戚于君位,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上親君位也。”“不敢計己親戚,與君齒列,是尊君也。兄弟相屬,多有篡代之嫌,今遠自卑退,是別嫌疑也。”
這是說君主可以用親情對待自己的家族成員,但家族成員卻不能反過來以親情來對待宗主,而只能是以臣子侍奉君主之道來對待自己的宗主。所有的族人都是宗主的臣子。再如《榖梁傳》中多次談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這些觀念和前文所見商西周時候的情況顯然不同,親緣關系的等級政治化愈加森嚴。最為著名的例子見于《漢書·高帝紀》,其文記: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后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于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
劉邦奪得天下以后,最初仍然是以子侍其父,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臣就告訴太公說,皇帝雖然是兒子,但卻是人主。你雖然是他的父親,但也是人臣。應該是身為人臣的你朝拜身為皇帝的劉邦才是合理的。太公聽從了家臣的勸告,等到劉邦再來時,太公以人臣之禮拜見。劉邦在了解事情以后,就重重賞賜了勸告太公的家臣。可見,在帝王家中,所有人之于皇帝一人,無一例外都只能是臣子的身份,即便是身為劉邦父親的太公也不例外。
實際上,我們不難看出,無論是君臣關系走出宗族的籓籬,固化為君王和其他成員之間的等級稱謂,還是王室家族內部親緣關系政治化的顯著加強,都和后世君權的不斷強化密切相關。親緣關系與政治秩序的日益分離,無論是對于舊有宗族秩序還是舊有君臣關系來說,都是一種顯著的變革,都意味著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的再建構,而在這個新的秩序中,君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