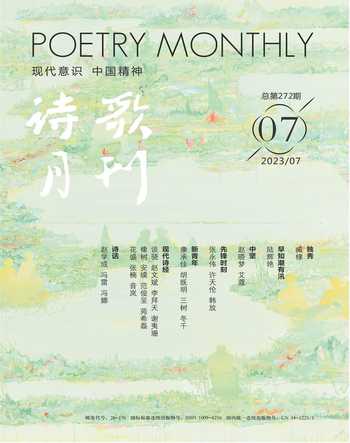植物現代性、主題性寫作及其他
馮雷 馮娜
馮雷:馮娜好,春回大地,萬物葳蕤,咱們就借機來聊聊“植物”的話題吧,當然這個想法不光是因為時令季節,還因為“植物”“風景”這樣的話題近來似乎也引起了小小的關注和討論。咱們還是先從你的創作談起吧,你的詩歌中也多次寫到各種各樣的植物,比如《松果》《杏樹》《宮粉紫荊》《苔蘚》《風吹銀杏》《橙子》,簡直不可勝數,而且你對植物的書寫也非常引人關注,有的研究者曾用“精神性植物視域”來加以概括,認為植物是跟你“整個的生命態度連在一起”的。你為何會注意到植物,植物和你的個人經歷之間有什么特殊關系嗎?你對植物是否抱有什么特殊的情感和寄托?有沒有什么特別衷情的植物?請先說說自己的情況吧。
杏樹
每一株杏樹體內都點著一盞燈
故人們,在春天飲酒
他們說起前年的太陽
實木打制出另一把躺椅,我睡著了——
杏花開的時候,我知道自己還擁有一把火柴
每擦亮一根,他們就忘記我的年紀
酒酣耳熱,有人念出屬于我的一句詩
杏樹也曾年輕,熱愛蜜汁和刀鋒
故人,我的襪子都走濕了
我怎么能甄別,哪一些枝丫可以砍下、烤火
我跟隨杏樹,學習扦插的技藝
慢慢在胸腔里點火
我的故人吶,請代我飲下多余的雨水吧
只要杏樹還在風中發芽,我
一個被歲月恩寵的詩人就不會放棄抒情
馮娜:馮雷兄好,在我所生活的嶺南,此刻已是初夏的風光,這也讓我感到古人以“物候”觀測的方法來認識時間和季節轉變,是非常智慧的。植物,可以說是人類的“近親”,是大自然的信使,我想這個世界上還沒有哪位詩人不喜歡植物吧(植物過敏癥者除外),在眾多詩歌書寫中植物的身影比比皆是。你提到的我所寫的植物,其實也涉及一個地域性的問題,譬如我寫到的松果、龍膽草、山茶花等植物明顯帶有高原的物候特征;而宮粉紫荊、橙子、勒杜鵑等植物是嶺南常見植物;銀杏、蘋果樹、桃李等在北方廣泛生長。所以,人們認識植物首先是認識一種地理特質,當然這些植物就像我們生命旅程中的過客,或與我們有故事的人。自《詩經》以來的中國文學傳統中植物就不僅是簡單的物象,而是寄寓了人類情感、情操的對象;我們今天看到桃花會想到“宜室宜家”、會想到“桃花依舊笑春風”,都是植物文化的積淀在起作用。人類與植物的故事是說也說不完,這也給我們創造了無數空間。在今天,我們認識植物的方式更多了,我們可以像博物學家一樣,通過互聯網技術迅速了解一種植物的生物特征,也會看到很多博物學著作翻譯到中國,比如《玫瑰圣經》《花神的女兒》《被遺忘的植物》《森林之花》等等,它們完全是以植物為主體的寫作,也為我們打開了很多認識植物的新視界。
馮雷:詩歌中的植物書寫古已有之。在我看來,植物進入詩歌,也可以看作是現代性的一種體現,或者干脆概括為“植物現代性”。剛才你也談到了《詩經》,據我所知,你對《詩經》尤其是《詩經》中的植物也很有研究。你覺得,古人的書寫對今人有何影響?今人對古人有何超越?可否談談你的心得?
馮娜:你提到“植物現代性”,我注意到有一些批評家提出“植物詩學”(譬如王凌云),將詩歌中的植物書寫作為研究主體。植物進入詩歌古已有之,從《詩經》時代“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到今天的“植物現代性”,其實包含的是人如何看待物的問題。作為“客體”的植物,很多都是這顆星球上的“活化石”,它們的生命比人類歷史久遠得多,從人類開始書寫它們開始,歷經幾千年,除了少數滅絕的種類,很多植物依舊還在地球上生機勃勃。當然,它們的名字隨著時代而更迭;比如,在《詩經》中的“舜華”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明媚的木槿花、“芣苢”是常見的車前子、“蝱”則指貝母……在這些植物名字的變遷中我們也可以窺見語言的變革,還可以體會到古人今人在用什么樣的心情和認知方式觀照這些植物。我對古代典籍中的植物也談不上研究,就是一種興趣式的“按圖索驥”。我出版過兩本隨筆小書——《顏如舜華——〈詩經〉植物記》《唯有梅花似故人——宋詞植物記》,是以植物視角進入《詩經》和宋詞的世界,去領略古人如何在天地山川植物中行走,又將怎樣的情思寄寓于植物。在很多研究者那里,比如你提到的“植物現代性”,更多的是通過現代視野把植物作為一種文學方法和參照;而在詩人和作家筆下,植物是與人類“共生”的一種生命載體,是人類與自然交互的一種“靈媒”。由此,我也想到生物學博士、華大基因CEO尹燁曾說過,生命具有“親生命性”,就是我們看到活的東西就會高興,因為看到活物,意味著我們也活著;生命也具有“親自然性”,我們說喜歡自然,其實說的是我們喜歡的是生機盎然、活潑潑的自然界。某種程度上,文學也是人類感知生命、通過與鮮活世界的鏈接、通過外界生命氣息確認自我存在的一種方式。我們看到在很多文學作品中,田園牧歌式的、作為風景和背景存在的自然比比皆是;帶著“人類中心主義”濾鏡的生態觀察不勝枚舉。但是,人類身處的真實環境并不完全是生機盎然、自然與人和諧共生的狀況;特別是在工業文明、商業文明洗禮過的現代社會,要看到我們所處時代的自然和生態是復雜的、多維的,充滿了不確定性。
如果要比較今人和古人對植物的凝視和書寫有何不同,我想最重要的是隨著時代的演進,植物與人類生活的交互方式極大地改變了。譬如,今天城市中的人要觀察植物,需要走進植物園或者到郊外、曠野中去,這和農耕時代“于以采■,南澗之濱”這樣的生活方式有了天壤之別。植物在古人那里是糧食、蔬菜、藥物,是良木莠草;更是重要的物候,用以判斷時令和節氣。而在現代人這里,植物的功用性得到極大的拓展,我們對植物的認知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植物學、博物學的興起也讓我們可以從微觀的科學角度來理解植物。但事實上,現代社會人與植物之間的關聯已經不那么密切了,很多人已經不再可能生活在植物的環抱中。由于人工技術的介入,植物的“應季性”也不再明顯,我們在冬天也能吃到大棚種植的“反季節”蔬菜水果,過去生長在深山老林的菌類或珍稀植物,我們現在都能在都市中見到。這種“物”的遷徙和變化不可能不影響人們對這些“物”的感知和情感鏈接,今天的人看到桃花都是種植在公園或作為行道樹,很難體會“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人與自然、與植物的故事又該如何在城市中續寫?最近幾年開始提倡的“生態文學”“自然詩歌”等,我想也是一種回應。而植物這種物象,它所凝聚的詩人的意象,向來都是我們努力尋找的心靈的“對等物”。
馮雷:你所提到的“植物詩學”,其實在植物書寫方面有特色的詩人不少,張二棍、宋曉杰、李元勝等等,這個名單可以開列很長。去年,臧棣的《詩歌植物學》獲得魯迅文學獎,這無疑使得詩歌中的植物更加顯眼了,同時或許也為當代詩歌在題材和方法方面提供了啟示。你怎么看?
馮娜:無論是生活中還是寫作中,我知道很多詩人對植物很感興趣,并有很多詩人對植物有深入的研究;比如詩人李元勝同時是一位生態攝影家,詩人沈葦寫過很多西域植物,詩人路也也寫過古代詩人與植物等。植物是詩人最容易攫取的自然界中最生動、活潑的意象,也是人格、情志的上佳載體。格物致知,中國詩歌傳統中就是如此,當代詩人的植物書寫更具現代意味和現代風格。說到植物作為一種題材進入詩歌,詩歌主題的整飭對于詩人而言,是創作整體結構性的統籌。很多詩人在實踐中也表現出來這種獨特的詩學追求和美學建構。臧棣的文本確實是一個較為獨特的樣本,他的寫作很早就呈現出一種題材遴選的自覺與籌謀;他的植物詩、動物詩,詩題“入門”“叢書”系列都體現了他對于自我詩學的整體性建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宏大敘事式微、日常生活與私人寫作凸顯的當代寫作中,“寫什么”這一命題又再次成為詩人關切的問題。寫植物,是一種探索,傳統詩歌中的植物書寫和植物意象已經有著悠久的積淀,如何超越和突破其實是對當代詩人的挑戰。但是,我們也要意識到碎片式、零散的單篇寫作,不足以支撐一個優秀詩人對世界、時代和自我的心靈世界做出整體性的觀察和描述,尋找主題依然是作家或詩人的核心命題。在這個問題上,前幾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露易絲·格麗克倒是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發,她將個體的生命體驗,融入西方文化的框架,每一首詩并非是單獨排布的獨立詩篇,而是一個有內在關聯和延伸性的整體,由此也可以看到一個詩人對于世界的觀察和理解所具備的那種穩定性和系統意識。對了,格麗克也寫過很多植物,野鳶尾、延齡草、寶蓋草等;所以植物題材不是哪位詩人的“發明”或“獨創”;而是植物在每個詩人那里都有不同的精神投射和心靈映照。不論是選擇植物還是選擇某個主題,能夠對自我創作進行一個整體性的審視我認為這是當下創作者最需要關注的問題,“怎么寫”“為何而寫”都將圍繞這個問題而展開。
馮雷:植物等自然意象在詩歌當中烘托了抒情氛圍,但顯然又不只是作為抒情的背景那么簡單。這個道理我覺得可以從小說中來借鑒。比如奧爾罕·帕慕克曾經說過:“景觀的布局是為了反映畫中人物的思想、情緒和感知的”,“小說里的景觀是小說主人公內心狀態的延伸和組成部分”,中國小說家很多也深諳此道。我注意到王干曾寫過一篇文章《為何現在的小說難見風景描寫》,王干的看法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共鳴,王春林、顏水生等做了跟進討論。不過我覺得有意思的是,王干是汪曾祺研究的專家,而汪曾祺曾在《說短》中明確認為“描寫過多”是小說的一大弊病,他認為“屠格涅夫的風景描寫、巴爾扎克的刻畫人物均不足取”。我知道你其實也寫過小說,對此你怎么看?
馮娜:我知道很多老師在上課的時候會講風景、風物,包括植物等自然意象的書寫是環境描寫的一部分,用以烘托故事背景和范圍等。但是難道我們沒有在描寫風物景致的優秀文學作品中單純體驗到自然之美嗎?沈從文的湘西、阿來的藏地、汪曾祺的人間草木、李娟的阿勒泰……我想如果當代小說中風景描寫的“消失”恰好對應的是人們故事發生的現場離自然風景已經遙遠,發生在“格子間”、高樓大廈、工地路橋的故事必然是現代景觀的描寫。當然,單純從小說的技術而言,風景描寫肯定不能大量鋪排以至于淹沒故事主體;任何一種題材都需要“恰到好處”的魅力;我想您所說的是一個寫作中“度”的把握問題。我們也可以看到張九齡的《感遇(其一)》,“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通篇都在寫植物、風景,但無一句不在講人心和情志。又比如阿來在小說《蘑菇圈》里寫了很多山地長蘑菇的景致,實際上也在寫人和山林之間的情愫。我想,現代城市生活與自然風景之間的關系無需贅言,但人們的寫作主題似乎更“精細”了;我們會看到大量分門別類的知識型書籍、類型化文藝作品涌現。說到這個,我聯想到另一個話題。就是近年來由于互聯網使文學的傳播方式發生了劇變,我們見證了“類型文學”的蓬勃興起。白燁等學者認為類型文學是從網絡到市場逐漸流行起來的,類型文學一般而言題材相近、受眾群體相對固定。毋庸置疑,“類型文學”產生的基礎是互聯網帶來的大眾傳播革命,受眾需求直接影響到創作者的創作,從而細分市場。小說這一題材首當其沖地置身于這樣的場域中,我們熟悉的科幻小說、穿越小說、懸疑小說、職場小說等門類越分越細,“越來越泛化、多樣化”(白燁語)。你提到的關于植物、動物等書寫的話題和研究我認為是跟這種題材的細分趨勢是密不可分的。但回過頭來,我們會發現,這種來自受眾和市場沖擊而形成的文學泛化和多樣化,并未過多地影響到詩歌寫作。一是因為詩歌本身屬于小眾藝術,不具備大眾通俗閱讀和傳播的要素(譬如缺乏故事和情節、影視化的空間較小等);二是詩歌直接介入市場和商業運作的可能性遠低于小說這種題材,使得詩歌一直處于大眾傳播的“低音區”。另一角度而言,也正是這種外部的喧囂和推力往往并不切身“摩擦”詩歌,使得詩歌的發展遵循著自身內在的節律。就像我書寫植物,在詩歌中我還沒有像詩人臧棣那樣把“植物”作為一種類型或系列的題材,可能就是自幼喜愛植物、經常與植物互動的性情使然。
馮雷:確實,或許是得益于科幻小說的強勢崛起,這些年“類型文學”討論越來越引起人們的興趣,就像你提到的一些研究者指出小說創作“越來越泛化、多樣化”,相比較于小說創作中“分化”出了科幻、穿越、懸疑、職場、校園小說,有的人認為詩歌創作中沒有出現類似的變化,乍看來也有一定道理。但正如我們前面所討論的,植物書寫,尤其是臧棣的《詩歌植物學》獲得魯迅文學獎給人以非常鮮明的印象,那你覺得類似于“植物書寫”可不可以算是某種類型化的詩歌寫作呢?
馮娜:“植物書寫”只是“主題性”書寫,還不能稱之為“類型化”的詩歌寫作吧?從類型文學的發展歷程,我們或可看出主題的選擇與創作、閱讀、傳播接受的關系非常密切。一個有意思的情形是,類型文學似乎率先讓創作者解決了“寫什么”的問題,也就是他們對主題的選擇是明確的,他們早早厘清了某類寫作主題的創作理念和基本模式。至于“怎么寫”“寫得怎么樣”,類型文學的評價標準也幾乎脫離了傳統文學的審美范式,直接面對受眾的選擇和市場的反饋。但就當代詩歌創作而言,創作者不可能認同同一套主題方法、基本模式以及相似的題材和藝術手段。學者吳承學曾在《論古詩制題制序史》中對中國古詩制題這一問題做了全面而精要的論述。他從“中國古代詩歌題目制作史”這個角度探討了“創作意識的進化以及古代詩歌藝術的發展”,中國古代詩歌經過從無題到有題,詩題從簡單到復雜,由質樸到講求藝術性的演變歷程,探討了中國古體詩歌題目與寫作之間的關系。對詩歌制題之“類”的考察,其實也是一種對詩歌內容的關切,如吳承學先生所說,詩題“積淀著審美歷史感的藝術形態,從中既可以考察詩人創作觀念的進化,也可以考察中國古代詩歌藝術風貌的歷史演變”。近百年來,在現代詩歌的發展史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們創作觀念、藝術風貌、主題選擇的新變。某種程度上,詩人們創作主題的選擇更加寬泛了;但就藝術創造性而言,新穎而紛繁復雜的主題涌現未必對應著更具活力和創造力的表達;而且對于前人已經涉足過的主題,要進行再創作的難度是上升的。
我們之前所說的主題先行的引導式寫作固然有建構一個整體大視野的意義,但主題性創作往往僭越了詩意的偶發性和詩人的經驗世界。就創作者個體而言,創作主題的選擇首先來源于對題材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再結合自身的創作興趣、學識積累和創作理念和雄心。當然,我們也會看到外部因素對創作者主題選擇所施加的影響。比如,在《西南聯大現代詩鈔》中,我們看到卞之琳、馮至、燕卜蓀、穆旦、王佐良、杜運燮、鄭敏等詩人的詩篇,不僅是個人生命體驗和詩學意識的求索,也是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民族危難之際,知識分子們歷經屈辱的南渡、西遷中一種公共經驗的集體呈現。歷史將時代的主題袒呈于詩人眼前,時代的語境如戰火的烈焰灼燒著詩人們的內心,寫還是不寫,這已然不是問題。另外一種對創作者主題選擇的外部影響則來自于文學制度的傾向性和引導,在現當代詩歌中這樣的例子很常見。最近幾年,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主題性的寫作,比如脫貧攻堅主題的詩集《花鹿坪手記》(王單單)、《春天的路線圖》(趙之逵),當代軍旅主題詩集《歲月青銅》(劉笑偉),展現改革開放成就的相關詩集如《藍光》(王學芯)、《新工業敘事》(龍小龍)等。雷兄對中國現代詩歌一直持續閱讀,我想你目之所及,應該有更多的發現。
馮雷:確實,“主題”“題材”不失為是觀察這些年詩歌創作的一個角度,遠的比如說世紀初的“底層經驗”寫作,近的比如說近幾年的“脫貧攻堅”詩歌。就我自己的閱讀感受來說,其中也不乏可圈可點之作。另外還有一些“行業詩”,比如“快遞詩”“高鐵詩”“石油勘探詩”“新工業詩”等等,這些實際上拓展了“主流”詩歌的題材范圍。當然還有一點,我覺得這些作品可能很難說是“主題先行”的,就像你所說的,是“對題材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再結合自身的創作興趣、學識積累和創作理念和雄心”。所以這倒或許啟示我們,大可不必挖空心思地去找題材、找主題,其實有詩意的題材、主題就像不知名的草木植物一樣散落在日常生活里。
馮娜:說到底,寫作還是一個人的孤旅,至于怎樣認知世界、怎么發掘題材、建構自己的詩學空間,還是需要一個詩人在實踐中去探索和創造。
馮雷,現就職于北方工業大學。
馮娜,現就職于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