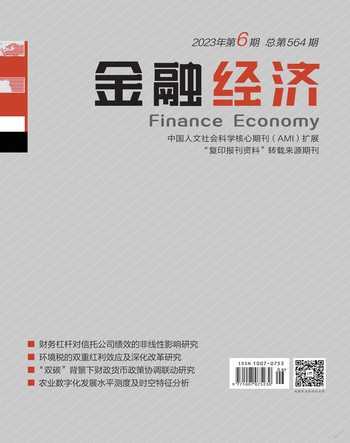基于系統觀念的農村產業發展極及金融支持路徑研究
摘要:實現鄉村振興,需要轉變傳統的生產方式,建立新型的集約化農業生產方式。考慮到農村資源的自然稟賦特點和發展的不均衡性,仍有必要在我國農村地區推行非均衡協同發展戰略。新形勢下,基于系統觀念建立農村產業發展極是實施這一戰略的有效方式。農村產業發展極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資源地理集聚,而是跨越地理空間的農村某一主導產業的資源集聚,進而有效形成農村地區的核心競爭力并成為鄉村振興的“火車頭”,帶動區域內相關產業發展。金融應為農村產業發展極提供系統性支持,通過支持主導產業發展、農業生產主體規模化經營、圍繞主導產業延伸農業產業鏈、主導產業與相關產業聯動發展、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與完善等推動農村產業發展極的形成和壯大。
關鍵詞:農村產業發展極;金融支持;系統觀念;鄉村振興;產業鏈
中圖分類號:F832.1?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1007-0753(2023)06-0073-8
收稿日期:2022-12-06
作者簡介:劉貴博,博士研究生,湖南大學金融與統計學院,研究方向為金融管理。
一、引言
隨著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的全面完成,我國農村的發展重點開始轉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為進一步解放農村生產力帶來了新的機遇。然而,大多數農村地區仍然采用落后的生產方式,導致農業生產水平低下,這是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根源之一。實現鄉村振興,需要改變農村傳統的生產方式,建立基于分工合作的新型農業產業化生產方式。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必須堅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創新、問題導向、系統觀念、胸懷天下,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其中,堅持系統觀念要求著眼于事物的系統整體性,正確把握整體與部分、事物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關注系統的整體優化、信息關聯和要素協同,這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原則,為農業生產及其金融支持的創新發展指明了方向。
為了更有效地推動農村建立基于分工合作的新型農業產業化生產方式,可以考慮在我國農村推行非均衡協同發展戰略。十多年前就有學者指出,為了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應實施非均衡協同發展戰略,而建立經濟發展極是實施這一發展戰略的有效手段(彭建剛和周行健,2005)。發展極既可以是空間概念,也可以是產業概念;發展極可以是大中城市,也可以是全國各地的小城市和縣域內的新興產業中心。發展極通過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能夠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并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從而達到促進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目的。發展極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的強弱取決于其核心競爭力的大小,這一核心競爭力實質上是把當地和周邊地區各類資源組織起來,達到特定經濟目標的整合能力。而金融是形成這一整合能力的激活劑和黏合劑,金融機構通過支持在農村地區建立發展極可以更好地發揮其在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中的作用。
考慮到農村地區的自然資源稟賦特點和地域廣闊性,通過建立基于生產要素地理空間集中布局的農村產業發展極(類似于工業園區)來帶動農業發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一般來講,農村產業發展極不能是空間集聚的,而應當通過農業產業鏈供應鏈進行產業集聚,把農村資源聚集到某一農產品的生產,優先發展、形成所謂的農業產業發展極。在農村產業發展極形成的過程中,主導產業和與主導產業相關聯的其他產業將形成一定的農業產業鏈,進而有可能形成農村產業集群。而金融機構重點支持農村主導產業及與其緊密相關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群,對農村產業發展極的形成極為有利。本文將運用系統觀念探討建立農村產業發展極及其金融支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發展極理論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適用性
發展極理論是由佩魯(1987)首先提出的,他認為在不同部門、行業或者地區經濟增長并非以同樣的速度實現,而是率先出現一些發展極,而后進一步推動其他部門、行業或者地區實現經濟增長。盡管佩魯的發展極理論涉及企業和產業的非平衡發展,但最終還是歸結為城市和區域的非平衡發展,并且強調吸引和擴散效應以及地理區位和中心優勢。與佩魯的發展極理論有所不同,赫希曼(1991)則重點關注經濟部門或者產業部門的非平衡發展,并著重強調產業關聯效應以及資源優化配置效應。在赫希曼看來,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應該集中有限的資源優先發展國民經濟產業體系中與其他產業關聯效應最大的產業,通過該產業的發展帶動后向聯系部門、前向聯系部門乃至整個產業部門的發展。
農村地區面臨經濟體量較小、較為封閉、資源相對短缺,以及不同區域或者產業部門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考慮運用發展極理論來推動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發展極理論在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中的適用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農村地區資源的稀缺性客觀上要求其通過打造發展極來打破資源瓶頸。資源稀缺和資本不足是農村地區面臨的現實難題,要在短期內籌集到大量資本解決農村地區資源稀缺的“中梗阻”問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與此同時,由于受到農村地區生產技術落后、企業家較少及其經營管理能力相對欠缺等因素的限制,齊頭并進的發展方式只會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最終只能在低水平均衡上進行貧困的惡性循環。倘若能夠集中農村有限的資源和資本優先發展某些地區或者產業部門,其他地區或者產業部門則通過產業之間的關聯效應和發展極的擴散效應而逐步得到發展,那么農村資源要素瓶頸才有可能打破,最終實現整個農村地區經濟的發展。
其次,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完整性以及不同地區之間資源稟賦的差異性決定了農村需要利用發展極來揚長避短。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完整性是指因農村自然資源和技術資源有限,和城市地區相比,農村地區經濟結構較為單一,無法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體系。資源稟賦的差異性是指由于受到歷史、區位條件等因素的影響,農村不同地區之間所擁有的自然資源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推動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時應該針對各個地區的實際情況,培育和發展不同的產業,比如,在旅游資源豐富的農村地區可以培育旅游產業,在水資源較為豐富的農村地區可以大力發展養殖產業等,然后再通過它們整合其他相關產業進而形成發展極。
最后,農村內部不同區域或者產業部門之間較大的發展差距為發展極的形成提供了現實基礎。當農村地區某些區域或者產業部門相對其他區域或者產業部門具有發展優勢時,可以引導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率先向該區域或者產業部門聚集,使其成長為發展極。發展極作為農村地區經濟、科技、人才、信息的中心,可以通過關鍵產業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有效輻射其他區域或者產業部門,形成不同區域或者產業部門之間的良性循環和共同促進的發展格局。
三、農村產業發展極及比較優勢的理論分析
(一)農村產業發展極的內涵
過去人們會將發展極和增長極當作同一個概念,就如同把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作為同一概念加以使用一樣,然而發展和增長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經濟增長代表著經濟產出和GDP的增加,但是若把增長作為唯一的經濟發展目標,將會帶來環境破壞、資源枯竭、分配不公等社會問題。而發展不僅意味著經濟產出和GDP的增加,還意味著產業結構的優化,資源的保護和節約,收入分配的公平化趨勢等。在發展內涵的基礎上,發展極所追求的是通過統籌規劃以及合理布局,充分利用自身與其他區域或者產業部門的比較優勢,破除市場和行政邊界,做到空間適當分割、產業適當分工、要素流動通暢,最終形成一體化經濟體系。發展極同時具有空間和產業兩層內涵,本文主要從產業角度對發展極的內涵進行界定,提出農村產業發展極的新理念。
農村產業發展極的內涵是選擇當地具有比較優勢的某一農產品及其產業鏈作為主導產業和發展極,集聚資源重點開發和發展,通過主導產業的重點發展帶動當地其他產業的發展,通過產業化發展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最終實現農村普遍富裕。從系統觀念來看,農村產業發展極通過優化生產要素組合,實行規模經營與分工協作相結合的生產模式,推動廣大農戶與農業龍頭企業的對接,讓廣大農戶與其他農業生產要素有機聯系起來,最終促進農業系統整體協調度和運行效率的提升。農村產業發展具有極鮮明的特征,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農村產業發展極并不是各生產主體的簡單集聚,而是由各生產主體組成的有機整體。農村產業發展極內的相關生產主體通過產業鏈結合起來,彼此之間分工協作程度很高,這種分工協作不僅實現了參與各方的互利共贏,而且提高了整個農村經濟系統的生產效率。其次,農村產業發展極不是空間集聚而是產業集聚,是以農村產業為紐帶跨地理空間的集聚。這是因為農業有其特殊性,農村種植業養殖業等第一產業與土地廣泛的耕耘利用直接相關,難以像工業園區那樣通過有限的地理空間集中來利用土地。農村必須充分利用現有的耕地、山林和水域資源,通過生物規律生產足夠多的乃至更多的農產品。
農村產業發展極的形成應至少具備以下幾方面的條件:首先,應當在農村地區培育農業龍頭企業。農業龍頭企業是指在資金、科技、人才、生產設施等方面具有相對優勢,主要承擔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以及農業生產性服務,使得農產品產前、產中、產后環節相互促進,在規模化和經營化等指標上滿足政府有關部門認定標準的企業(孟秋菊和徐曉宗,2021)。農業龍頭企業在農村產業發展極形成和壯大的過程中發揮著引領和帶動作用。第一,農業龍頭企業可以圍繞主導產業與特色產業來實現業務分離、合作與創新,不斷拓寬和延伸整個農業產業鏈條,并利用本企業在農業產業鏈中的核心地位,推動農業生產、加工、倉儲、物流等相關產業的融合化發展,進而在農村地區形成“產加銷一體化”的全產業鏈集群,從而為地方獲取產業發展優勢和經濟競爭優勢提供便利。第二,農業龍頭企業能夠引導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進行銜接,由于農業龍頭企業的主要業務是以農業或者農產品為基礎開展的,與小農戶具有緊密的利益聯結關系,其不僅可以為小農戶開展農業生產活動提供生產資料、技術指導等相關服務,而且可以引導和帶動小農戶進入農業產業鏈的不同環節,讓小農戶等更多農業生產主體享受到農業產業鏈延伸帶來的增值收益。第三,農業龍頭企業在生產能力、技術水平、資本運營能力以及規模經營等方面具有優勢,能夠借此從產業部門內部或者社會上引進技術、人才、資本等資源,推動自身不斷發展壯大。之后,農業龍頭企業也可以根據需要向農村產業發展極其他環節乃至發展極以外的其他產業部門輸出這些資源,以支持整個農村產業體系的發展。
其次,打破農村地區家庭分散經營格局,推動實現農業規模經營。隨著農業社會化和農村市場化的不斷發展,土地細碎化和家庭分散經營已成為阻礙我國農業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農業生產規模的限制使得各類具有規模效益的基礎設施很難有效發揮其最優效益,同時又無法有效提升農業技術推廣效率和農業機械化程度;另一方面,家庭分散經營使得農業勞動力成本相對較高,與大市場對接存在障礙(韓鵬云,2020)。推進農業規模經營的本質是通過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帶動農業生產成本的降低和生產效率的提升。農業規模經營的實現方式主要分為土地規模經營和服務規模經營兩種,前者主要通過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和集中來推動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后者主要通過統一和集中的社會化服務來推動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由于各種農業規模經營的實現方式均具有一定的地區適應性,加之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地形條件、人口特征等存在較大差異,很難用一種普適的方式來對我國各地的農業規模經營進行概括,需要針對各地區的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農業規模經營實現方式。農村各地區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應該將土地規模經營和服務規模經營二者有機結合和統一,以更加有效地推動當地農業規模經營的發展。
最后,為農村產業發展極營造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現階段我國農村地區普遍存在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問題,而農村產業發展極的形成和壯大需要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作為支撐。政府部門應當集中有限的資金著力完善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將財政資金重點投資于農村道路、水利設施、通信設施等對農村產業發展極的形成和壯大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項目,為投資者和廣大農村群眾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以及生產生活條件,以進一步吸引更多的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向農村產業發展極聚集。與此同時,政府部門還應優化農村地區營商環境,為農村地區產業發展提供稅收優惠,建立健全鄉村人才體系,為農村產業發展極的形成和壯大營造良好的外部發展軟環境。
(二)農村產業發展極的比較優勢
在發展中國家或者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為了使得經濟發展能更加有效地進行,出現非均衡發展是正常現象。這種非均衡發展既可能出現在不同產業和部門之間,也可能出現在不同地區之間。然而,為了實現公平目標,又不能任由這種非均衡狀態自由發展和無限擴大,必須注重不同產業之間和區域之間關系的協調,以先發展起來的產業和區域帶動后發展的產業和區域,以求在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前提下最終形成整個地區經濟系統良性協調發展的格局。非均衡協同發展戰略在強調非均衡發展的同時又注重采取有效措施來對非均衡進行調控。非均衡和協同都是該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中非均衡是提升經濟發展效率的有效手段,而協同是經濟發展最終要實現的目的。農村產業發展極采取的正是非均衡協同發展戰略,在選擇當地具有良好發展基礎的產業作為主導產業進行重點支持的同時,又注重協調主導產業與非主導產業之間的關系,并將廣大農民等弱勢生產群體引入產業發展軌道,帶動非主導產業乃至廣大農民等弱勢生產群體的發展。
農村產業發展極主要通過極化效應與擴散效應來實現非均衡協同發展戰略。極化效應是指主導產業的建立或者產品的增加會帶來原有區域范圍內不曾配置的其他產業活動的出現。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中具有趨利性,其在各產業部門之間的流動實際上是帕累托改進的過程,應用于農村產業發展極則表現為,農村產業發展極外部其他產業部門的生產要素在趨利性的驅使下會逐步流向更加具有競爭優勢的農村產業發展極內的產業部門,在極化效應的作用下農村產業發展極不斷壯大。擴散效應是指通過主導產業的建立和產業鏈的延伸來輻射其他相關產業,使得生產要素在農村各產業部門之間自由流動,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隨著生產要素向農村產業發展極的逐漸集中,其邊際產出和邊際報酬遞減的趨勢會降低生產要素向農村產業發展極流動的積極性。與此同時,隨著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及農村產業發展極形成以后主導產業部門與其他相關產業部門之間聯系的加強,部門之間的要素流動更為暢通,發展極內部的一些生產要素向發展極外部其他相關產業部門擴散,帶動其他產業發展。
農村產業發展極這種非均衡協同發展方式對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農村產業發展極可以有效形成農村地區的核心競爭力。農村產業發展極遵循了因地制宜的原則,是在具備獨特的資源稟賦、優越的自然條件和特色人文環境的區域范圍內,通過整合當地現有資源充分發揮區域比較優勢,以當地主導產業為基礎建立的,這些自然條件、資源稟賦和人文環境等不能為外界所簡單復制,對于發揮農村地區的核心競爭力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農村產業發展極可以有效降低農業生產成本。亞當·斯密(2014)提出了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觀點。農業由于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長期以來分工協作有限,不能像工業那樣通過迂回生產獲得報酬遞增的好處,這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長期存在和農民增收乏力的重要原因。隨著我國信息化進程的推進和農業機械化裝備的發展,通過勞動分工和生產規模擴張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彭建剛和胡月,2018)。在農村產業發展極內,各農業生產主體實行規模化經營,并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實現產業集聚,相互之間的分工協作程度很高,有助于降低農業生產成本。
再次,農村產業發展極具有一定的信息優勢,可以緩解農業生產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農村產業發展極內各農業生產主體聚集度相對較高,彼此之間能夠及時共享商業信息,從而使得信息傳遞相對更有效率。與此同時,各農業生產主體由于分工協作程度較高,彼此之間利益較為趨同,也更加有動力將信息分享給對方。
最后,農村產業發展極可以推動農業技術創新,從而實現農業技術水平的提升。農村產業發展極內有創新能力的龍頭企業會通過持續開展自我技術創新、引進最新的技術資源和人力資源等方式推動農村產業發展極內相關產業技術發展。與此同時,農村產業發展極內相關產業結構的升級會通過不斷向外擴散帶動產業層次和技術層次較低的農村產業實現技術進步,從而帶動農村產業整體的技術發展。
四、金融支持農村產業發展極的基本邏輯
農村產業發展極實現了農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升級,作為服務農村經濟發展的涉農金融體系需要適時做出調整,以便適應農村產業發展極的新要求。本文認為,構建適應農村產業發展極的涉農金融體系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金融應當支持農村主導產業的培育和壯大
實現農村產業興旺的前提條件是要明確并發展具備市場競爭優勢、增長率較高、經濟社會效益較好和輻射拉動作用較大的現代農業產業,因而首先需要確定哪些農業產業適合作為主導產業進行重點發展(童洪志等,2021)。金融機構應以農村各地的資源稟賦優勢為導向,選擇產業關聯效應較強且具備良好市場發展前景的產業作為主導產業并對其加以重點扶持,根據主導產業的特征有針對性地設計差異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通過為其提供持續性的金融要素供給,使其逐漸成長為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首先,農業具有自然屬性,農業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外部資源,而我國各地區自然條件等存在較大差異,這就決定了農業主導產業的選擇必須十分注重區域的資源稟賦,通過揚長避短發揮比較優勢。其次,農業主導產業只有具有較強的關聯效應,才能使農業產業鏈得到有效延伸,從而帶動相關農產品生產、加工、倉儲保險、物流運輸、技術研發等產業的發展。例如,湖南省中方縣將中藥材產業作為主導產業進行重點發展,不僅成為遠近聞名的中藥材供應基地,而且中藥材深加工、康養旅游以及中藥材交易集散等其他相關產業也逐漸被帶動起來(張家銑,2022)。最后,在市場經濟發展環境下,農業已經不再是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農業生產的目標是滿足市場需求,如果缺乏足夠的市場需求拉動,主導產業也就沒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二)金融應當支持農業生產主體規模化經營
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實現有賴于大量的資金投入,而農戶等農業生產主體的自有資金往往不足以負擔農業規模化經營所需要的資金投入,內源融資不足的農戶只能依賴銀行信貸等各種外部融資途徑。第一,一系列農村土地流轉政策的實施、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行以及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條件的放開等都為我國農業規模化經營創造了現實條件,金融機構應適時支持有長期務農意愿的農戶等農業生產主體擴大土地適度經營規模,緩解其承租流轉土地等所面臨的融資約束。除土地生產要素以外,農業生產過程需要資本、勞動力等各種生產要素的共同參與,金融機構應著力緩解農戶等農業生產主體雇傭農業勞動力以及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生產工具、管理方法等面臨的融資約束,通過新要素的引入以及要素的重新配置為農業規模化經營提供條件和可能。第二,金融機構還應支持各類農村經營主體建立具有土地托管、農機作業、統防統治、技術指導、信息服務等功能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如發放優惠貸款、建立和完善多種形式的貸款擔保模式等,通過為農戶等農業生產主體的生產經營提供統一的社會化服務助推其實現規模化經營。第三,金融機構通過聯合授信、提供優惠貸款等方式引導農村地區封閉分散的農戶等農業生產主體連接起來,支持其橫向聯合形成產業集聚效應和聚合規模,并且結合區域集群產業發展特點設計產業綜合性金融服務方案。
(三)金融應當支持圍繞主導產業延伸農業產業鏈
金融通過支持農村地區圍繞主導產業延伸農業產業鏈,將農業生產的各環節連接成完整的產業體系,實現不同生產環節之間的有效銜接。不同金融機構可以基于自身的功能定位和比較優勢,分別對接和滿足不同農業生產主體的融資需求。金融機構在為農業生產主體提供金融服務時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金融機構應支持農村地區孤立分散的農戶等農業生產主體根據各自比較優勢進入農業產業鏈的不同環節,通過農業產業鏈強化農戶等農業生產主體與產業鏈上其他生產主體的分工協作。第二,金融機構在為農戶等農業生產主體提供金融服務時應當具有系統性思維,避免采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局部療法”,而應更加關注整個農業產業鏈上各農業生產主體的融資需求,在滿足農業產業鏈上某一農業生產主體的融資需求時,還應關注產業鏈上與該經營主體有分工協作關系的其他農業生產主體的融資需求。第三,金融機構應重視金融與數字技術的融合,積極完善農村地區金融科技軟硬件設施建設,借助金融科技優勢,實現與農業產業鏈上農業生產主體的信息交換與共享,提高獲取有關客戶信息的能力;同時,這些信息能夠幫助金融機構準確判斷和分析產業鏈上相關產業的基本情況、現實風險和發展前景,并依據產業鏈上中下游產業的關聯性合理設計金融產品。
(四)金融應當支持主導產業與相關產業聯動發展
主導產業與相關產業聯動發展是指主導產業在由低級向高級轉變的過程中不僅自身發生正向變化,而且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發生聯合行動變化的過程,是產業間分工協作進一步泛化與深化的必然要求。主導產業與相關產業聯動發展意在突破區域分界線的限制,減少產業之間的惡性競爭與重復建設,加強產業之間的分工協作,在整個區域共同利益最大化目標的驅動下實現產業各自更大的發展。一方面,主導產業與相關產業聯動發展離不開科技的支撐,金融機構應支持農村產業發展極內有條件的農業生產主體開展產業技術研發,增強其自身創新能力;同時支持農業生產主體加強與高等院校、農業科研機構的合作,探索構建農業“產學研用”聯動機制,通過農業技術的不斷進步推動農村產業發展極內相關產業升級與迭代。另一方面,金融機構應引導主導產業與其他相關產業的生產主體加強戰略合作和相互滲透,使產業之間形成融合化發展態勢,產生較為明顯的范圍經濟效應,從而推動農業生產主體生產成本的降低;同時充分利用農業的多功能性支持新興關聯產業的開發,并引導其與農村產業發展極內現有相關產業進行銜接整合,從而吸引更多的勞動力、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流向農村產業發展極及其相關產業。
(五)金融應當支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與完善
農村基礎設施是為發展農村生產和滿足農民日常生活需求而提供的一系列公共服務設施的總稱(何翔,2021)。現階段我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滯后,最主要的原因是投資不足。農村基礎設施投資一般由各級政府部門承擔,但是由于投資額度較大,單純依靠政府財政投入并不能完全滿足其資金需求,需要依靠金融機構的支持來彌補這一資金缺口。一方面,金融機構應主動加強與政府部門、農村企業、農戶等主體的溝通與協調配合,了解并掌握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現狀和不足,將信貸資金重點配置于對農村產業發展極的形成和壯大具有關鍵作用的水利設施、農村道路、物流設施等項目。另一方面,金融機構應綜合分析不同農村基礎設施項目的收益與風險,優化其信貸組合,在完善信貸風險分散分擔機制的同時,創新支持農村基礎設施項目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有效發揮金融資本的杠桿效應,撬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農村基礎設施項目建設。
五、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系統性和整體性思維,從發展極理論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適用性、農村產業發展極的內涵、農村產業發展極的比較優勢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在我國農村地區建設農村產業發展極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并在此基礎上詳細闡釋了金融支持農村產業發展極的基本邏輯,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農村地區資源相對稀缺、經濟發展不完整、資源稟賦存在差異以及不同區域或產業部門之間發展不平衡,這些特征決定了發展極理論對農村經濟發展具有較好的適用性。
第二,農村產業發展極的內涵是選擇當地具有比較優勢的某一農產品及其產業鏈作為主導產業和發展極,集聚資源重點開發和發展,通過主導產業的重點發展帶動當地其他產業的發展,通過產業化發展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最終實現農村普遍富裕。農村產業發展極是以農村產業為紐帶跨地理空間的產業集聚,發展極內的不同生產部門通過產業化經營提高了自身的生產效率,通過產業鏈實現有效銜接。
第三,農村產業發展極實行的是非均衡協同發展戰略,在重點支持主導產業發展的同時也兼顧了非主導產業的發展,其比較優勢體現在可以有效增強農村地區的核心競爭力,降低農業生產成本,緩解農業生產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并推動農業技術創新。
第四,金融應為農村產業發展極提供系統性支持,通過支持農村主導產業發展、農業生產主體規模化經營、圍繞主導產業延伸農業產業鏈、主導產業與相關產業聯動發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與完善等,推動農村產業發展極不斷形成和壯大。
參考文獻:
[1]彭建剛,周行健. 雙重二元經濟結構視角下的經濟發展戰略——非均衡協同發展戰略[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5(06):108-112.
[2] 佩魯.新發展觀[M].張寧,豐子義,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3] 赫希曼.經濟發展戰略[M].曹征海,潘照東,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1.
[4]孟秋菊,徐曉宗.農業龍頭企業帶動小農戶銜接現代農業發展研究——四川省達州市例證[J].農村經濟,2021(02):125-136.
[5] 韓鵬云.農業規模經營的實踐邏輯及其反思[J].農村經濟,2020(04):17-25.
[6] 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全集:第2卷 [M].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7]彭建剛,胡月.基于分工理念的開發性普惠金融:功能定位與比較優勢[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8,39(06):8-14.
[8] 童洪志,冉建宇,管陳雷.鄉村振興背景下三峽庫區現代農業主導產業選擇研究 ——以重慶萬州區為例[J].農業現代化研究,2021,42(04):619-628.
[9]張家銑.推動三次產業融合發展,走出特色鄉村振興之路[N].懷化日報,2022-9-9(03).
[10] 何翔.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公平性與脫貧攻堅成果鞏固關系研究——基于2010—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宏觀經濟研究,2021(03):160-175.
(責任編輯:張艷妮)
Research on the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es and Financial Support Path Based on System Concept
Liu Guibo
(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 and establish a new 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Considering the natural endowment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ources an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unbalanc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s rural area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stablishing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es based on the system concep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lement this strategy.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es are not just the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general sense, but the agglomeration of resources for a dominant industry across geographical spaces in rural areas, which can effectively form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rural areas and become the "locomo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within the region. Finance should provide systematic support the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es, promote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es through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ominant industries, large-scale op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ain bodies, extend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around dominant industries, linkage development of dominant industries and related industries, and improving rural infrastructure.
Keywords: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es; Financial support; System concept;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ch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