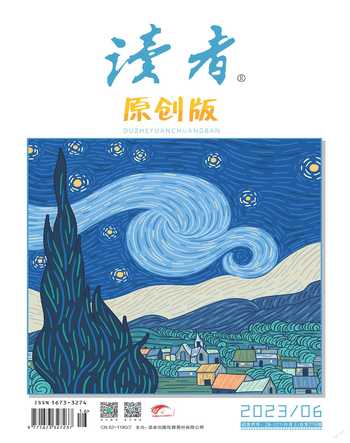徐醫生的喜宴
天凌
一
那年夏天,我回到媽媽當年參加送醫下鄉任務的村鎮,代表腿腳不便的媽媽參加她徒弟徐醫生嫁女兒的喜宴。
40年過去了,當年的“小徐醫生”變成了“老徐醫生”,但這座名為方橋的古鎮依舊“人家盡枕河”,處處行舟楫,醬菜店、竹器店、桿秤店、糕團店和榨油坊,早已由老店主的兒孫輩接手了,但依舊開著排門,像40年前那樣不緊不慢地等著四鄉八鎮的鄉鄰光顧。
徐醫生雖已謝頂,但他謙遜和藹的笑臉,與當年幫我治百日咳時一模一樣。40年前,我尚年幼,感冒后久咳不愈,徐醫生帶來了家里母雞下的雞蛋,每個雞蛋上都用鉛筆淡淡地寫著這只蛋的出生日期。他用力打散一個雞蛋,一直打到雞蛋液發起細膩的泡泡再去找鄉衛生院的食堂大師傅,舀一勺滾燙的粥湯沖到裝雞蛋的大瓷碗里。蛋花頃刻間像云朵一般鼓起,徐醫生遞給我勺子,催我快喝,說蛋花湯是清肺火的,只要堅持喝,咳嗽便會痊愈。
回到方橋古鎮,我先參觀了徐醫生坐診多年的小診所。他有一張“兩頭沉”木桌,打開兩側的柜門,里面滿滿當當放著的全是村民的病歷。防潮的塑料膜里夾著的,是病人十年甚至數十年的病情記錄。在城里,社區醫院都已使用網絡信息系統了,但徐醫生的病歷管理依舊如此原始與質樸,讓我吃驚。徐醫生解釋說:“電腦上的東西,這里的老年人看不明白。紙質的病歷雖然原始些,可他們能夠戴上老花鏡來看,瞧著放心呀。”
為了說服節儉的村民舍得吃藥,徐醫生會反復比較藥品的單價,選擇那種一瓶能裝上30粒、50粒甚至100粒的常見藥。每次看過病人,他會用潔凈的小藥袋將各種藥分揀出來,少的只包四五粒,多的也只有十來粒,村民花個幾塊錢、十幾塊錢,便能治好病。
二
徐醫生見到我十分激動,還說起一件往事,他的父親40多年前被毒蛇咬,就是我媽媽竭力救回來的,這也是他立志學醫的一個契機。
我想起來了,徐醫生父親遇險,是在一個炎熱的夏日,農民都在田里抽水抗旱。半夜,早已睡下的媽媽和我被一陣焦急的擂門聲驚醒,外面人聲鼎沸,趕來的農民高聲呼救。他們用門板將一個小腿腫脹的中年漢子抬進了媽媽任職的衛生院,每個人身上都像被大雨潑了一遍,大汗淋漓。但此時,雪上加霜的是,鄉里的用電負荷太大,突然跳閘斷電了。萬般無奈之下,媽媽讓病人的兒子舉起手電筒,她俯下身子,用醫用橡皮筋將病人的膝蓋上方牢牢扎緊,又讓病人的侄兒迅速到鎮上去,把能借到的手電筒都借來。
很快,擂門聲響徹整個小鎮,借來了8只強光手電筒。接著,我媽媽讓8位個子高的村民在她周圍圍成一圈,舉起手電筒,組成一臺“無影燈”。我媽媽用手術刀迅速切開病人被蛇咬的傷口,俯下身去,用力吸出含有蛇毒的血液。她一邊將污血吐出,一邊漱口,身子微微發抖……
隔了好一會兒,再吸出來的血液終于變紅了,抗蛇毒的血清也已經注射下去,病人神志漸漸清醒。當天晚上,鄉鄰四散。因為不放心病人,媽媽就睡在鄉衛生院的手術室里。
中年漢子被救回來之后,他的長子堅定了學醫之心。徐醫生18歲從當地醫學中專畢業,19歲就被分到了鄉衛生院,跟著我媽媽學習如何處理刀割傷、灼燒傷,學習針灸、拔火罐與耳針之法,以及做一些常見的小手術。記得那時小徐醫生為了學習耳針,經常學著媽媽的樣子在自己的耳朵上按壓綠豆,而調皮的我會伸手去捏他耳朵上的綠豆,令他猝不及防地痛叫出聲。
20世紀80年代初,我媽媽因為要解決夫妻分居兩地的問題,離開了鄉衛生院,調往南京。彼時,她的徒弟徐醫生已經可以獨當一面了。
徐醫生就是方橋古鎮周邊的農家子弟,他比我媽媽更懂得如何以最小的代價讓農民獲得醫治與安慰。他在這里一干就是40年,組建家庭,養育兒女。
可就在他女兒結婚那天,一位老農過來求助,說他弟弟在田間打藥時突然暈倒了。此時,徐醫生正穿著紅綢子的衣服、黑綢子的長褲,皮鞋刷得锃亮,衣襟上別著的飄帶上寫著“父親”二字。一聽說有人暈倒,他立刻披上白大褂,帶上他的小藥箱和聽診器出門。他跑了幾十步,折回來,在辦公桌的抽屜里摸了一把糖,又跟著病人的大哥狂奔了出去。
過了不到一小時,喜宴即將開席,徐醫生就回來了。病人的問題已經解決,不出他所料,暈倒的農民是因為沒吃早飯就下地干活兒,加上有點兒中暑,出現了低血糖、眩暈。吃了徐醫生帶去的奶糖,喝了徐醫生保溫杯里的紅棗水,這會兒已經好多了。
三
看得出,徐醫生在這里的人緣很好,女兒的婚宴在這個小鎮上居然擺了25桌,幾乎所有的人家都來了。在過去的40年里,他們多多少少都得到過徐醫生的治療和關照。當地有風俗,給新婚夫婦的小紅包是不可以謝絕的,為了答謝來參加婚宴的人,徐醫生特地請來了最好的鄉間廚師,還準備了一個類似游園會的環節。
他與老伴兒在自家院子里準備了套圈、弓箭射氣球、踢毽子等有獎游戲。他為得獎的村民準備了罐裝肉松、盒裝牛奶、核桃露,以及塑料水桶與臉盆。徐醫生笑著對我說:“在村鎮上,罐裝肉松或者盒裝牛奶是人情往來的硬通貨,兒女送給父母,父母轉送給爺爺奶奶,爺爺奶奶又可能轉送給侄孫……轉來轉去,這些食品臨近保質期了,人們才會下決心吃掉。”
徐醫生曉得,這里大部分的年輕男人都去城里打工了,留在村鎮上的都是婦女、孩子與老人,平時生活十分寂寞。有人辦喜事,那簡直是他們難得的節日。在為喜宴搭建的舞臺上,不管是唱歌、唱戲還是其他表演,徐醫生都會為表演者遞上一只印著喜慶圖案的塑料臉盆,村民們都十分高興。
尤其是那些六七十歲的老人,他們因為踢毽子的功夫了得而得到獎品,笑得比過年還開心。他們到了這把年紀,除了帶孫子,還要在地里勞作,他們堅信,一日不流汗、不使勁兒,肌肉就會萎縮,力氣就會離他們而去。他們的臉龐、胳膊與小腿都被曬成了醬油色,伸出手臂來,70歲的人仍然擁有銅澆鐵鑄一般的肌肉。正是這些勤勞又不服老的人,種出了大家一日也離不開的稻米、蔬菜和水果。徐醫生說:“我自己的醫術有限,但我想一直陪伴著他們。當我與村里看門的狗和鵝都混熟了時,村民們就會放心地把貼滿膏藥的后背,把在水田里受傷的腳都交給我。”
喜宴到達了高潮,幾乎所有的人都喝到微醺。一位70來歲的老漢站起來,沒有伴奏,唱著自己編的歌謠。蒼老的他聲音嘶啞,就像一只老去的鷹在自己出生的山谷半空緩緩盤旋、鳴叫。他唱道:“醫生的關照山高水長,河里的烏篷船載不動你的牽掛。女兒今日出嫁,你可也要跟著離開?”
作為村醫,老徐已經在這里服務了整整40年。一開始,他在鄉衛生院工作,后來,因為學歷不夠,他不得不從鄉衛生院離職,開了一家私人診所。他的命運與這塊土地上的兄弟姐妹融合在一起。他老了,他的病人也老了。他說,自己如今還看得動病,就一定不會離開。
為了讓鄉鄰們放心,在女兒的喜宴結束后,徐醫生帶著女兒女婿,在診所的院落里種下了一棵棗樹和一棵櫻桃樹,他們又為老葡萄藤編了一個寬綽的攀爬藤架,藤架下安設了石桌與石椅。這樣,以后候診的病人就能在葡萄藤濃蔭下,吹著微風,喝著金銀花茶,安心等著老徐為他們看病開藥了。
這些在原野上勞作的農民,能安心留在故鄉,留在熟悉的山水間,除了故土難離,也是因為有“徐醫生們”一直陪伴在他們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