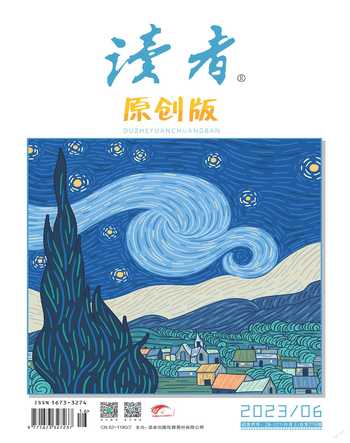“社恐”的我是如何打開局面的
閆紅
一
前兩天我家暖氣壞了,我很驚慌。倒不是怕冷,怕的是要請師傅來修。
上次我請師傅來疏通馬桶,事前談好價格為80元,師傅進屋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倒了兩包粉末進去,然后說:“不行,這馬桶得拆掉。”我問他:“這一拆一裝多少錢?”他說到時候再看,我心想算了。然而,他要我把兩包粉末的錢給他,一包400元,兩包800元。
我作勢要報警,他便趕緊找我要了100元走了。臨走時他很厲害地說:“你家馬桶就永遠堵著吧!”
之后我去樓下超市花了14元買了一瓶管道疏通劑,回家倒進馬桶,半個小時后聽見“轟隆”一聲,如冰消雪融,師傅的詛咒就這么被解開了。
有朋友說,從入戶門上塞的小卡片上找的師傅會更靠譜,我覺得有道理。能跑來塞小卡片,活動軌跡應該就在這附近,說不定啥時候就迎面碰上,多少會有點兒忌憚。若真是一期一會,人就可能無所顧忌。

疏通馬桶的技術含量不高,眼看有可能被坑,還可以“揮一揮衣袖”,讓他“不帶走一片云彩”。暖氣設備的維修要復雜得多,雖然鄰居給我介紹了一個師傅,把價錢也告訴我了,我心里還是有點兒遲疑—到時候人家把攤子支開再獅子大張口,可就不像撒一包粉末進去那么簡單了。
加上修暖氣師傅的微信后,我發現他回復的語氣很好,其實就是有來有回。有人會不回你的信息,刻意制造一種短缺感和壓迫感。而且這位師傅姓馮,我莫名覺得這個姓有一種老派的敦厚和可靠感。
等到師傅上門了,發現他是個和顏悅色的人,這又讓我放松了點兒。我見過有的師傅一來就咂嘴嘆氣,顯得一籌莫展,營造一種事情很難辦的氣氛,等到你快崩潰了,覺得自家這狀況神仙來了都搞不定,他就可以坐地起價了。
我家有兩個房間的暖氣不熱,師傅判斷是暖氣水管堵住了,需要清洗一下。清洗過程比我想象中漫長,他站在設備間里操作,我在一旁表示關心。
有“社恐”心理的我常常會表現得更加熱情,以掩飾自己與人交往時的不自在。我臉上堆著硬擠出來的笑容與師傅客套,心想—怎么還沒修完啊?只盼著結束后我就能開始休假,好幾天不用再進行社交了。
這時,我家孩子從臥室出來,探個頭后又進屋了。師傅問:“你家孩子上高幾?”我隨口答“高一”,然后本能地感到他之所以會問我這個,是因為他家應該也有個高中生,便順勢又問他家孩子讀幾年級,他說高三了。
我突然福至心靈,他愿意提起這個話題,可能是希望我問更多—我認識的一個人有個很優秀的兒子,你問他今天星期幾,他都能把話題轉到他兒子在哈佛讀博士這件事上。這位師傅極可能也在拋磚引玉。
果然,幾番對話下來,我知道了他女兒在本市最好的高中就讀,而聊天的話題也層出不窮—我們詳細地討論了分科、補課、各校的升學率;上大學的話,是學校重要還是專業重要……在寒風瑟瑟的設備間門口,兩個學生家長真是有說不完的話。
二
我想起上次這種場景發生,還是在十幾年前。那次,也是全靠“寶媽”這個身份化解了尷尬。
當時單位樓下有一家洗腳房,我和同事常去按摩放松。雖說勞動不分貴賤,但讓別人給自己洗腳還是很別扭的。我繼續發揮“社恐”人士專長,努力沒話找話;按摩師是位年輕女士,也在努力回答,大家都有點兒辛苦。
不知怎的聊到了自家的孩子,對話頓時順暢了起來。單是娃的吃飯、睡覺,就有無數苦水可以互相倒,什么時候斷奶?加什么輔食?好像可以聊到地老天荒。
“寶媽”不只是一種身份,還是一種處境。在負一樓昏暗的洗腳房里,兩個萍水相逢的女人,因為共同的處境,瞬間成為莫逆之交。
那次經歷使我獲得了一個社交小秘訣—和別人沒話聊時就聊孩子,再內向的人,一說起這個話題都會打開話匣子。這其實挺有意思的,曾幾何時,張嘴閉嘴談孩子的人會被定義為“俗氣”,被認為沒有自己的人生,為什么不聊點兒更有格調的話題呢?
而現在,孩子成為熱門話題,我想,一方面是因為人們更著意于愛“具體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從詩詞歌賦聊到人生哲學”未必就比聊孩子更顯高級。另一方面,育兒也是一場漫長的游戲,各種成敗得失讓人孜孜不倦。如果你見過兩個游戲愛好者如醉如癡討論游戲時的模樣,也就能理解為人父母者為何“志同道合”了。
說回修暖氣這事兒。全程總共3個小時,但有“高中生家長”這個身份加持,我并沒有感到特別漫長。結束后,師傅說要給我打個折,我堅持不要他的優惠,我們拉扯了幾個回合,當然是掃碼付錢的人占據了主動。
按照師傅的囑咐,暖氣溫度升上來后我給他發了條短信,告訴他已經搞定,并發自肺腑地祝他新年快樂,祝愿他的女兒事事順利、金榜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