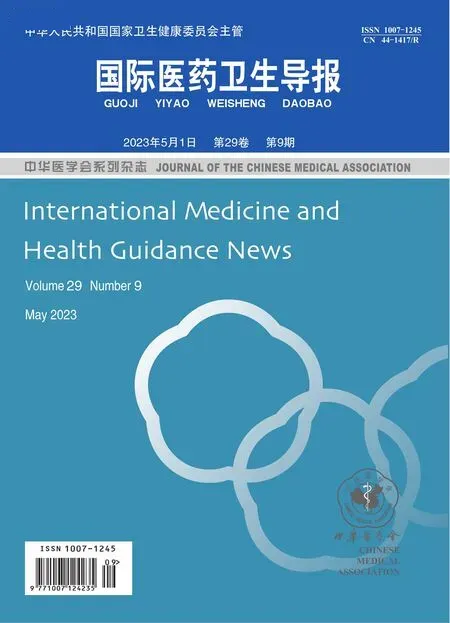骨肉瘤臨床治療現狀與創新療法研究進展
詹澤宇 林思恩 魏波
廣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骨科中心,湛江 524001
骨肉瘤(osteosarcoma,OS)是骨骼系統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起源于間葉組織,最易發生的部位是血供豐富的干骺端,具有雙峰年齡分布等特點。發病率最高的是兒童和青少年,其次是老年人(>60歲)[1]。OS常發生于長骨骨骺附近的生長板,大約2/3的腫瘤出現在膝關節周圍的股骨遠端。近期研究中診斷為OS的患者中有10%~15%已經有轉移[2-3]。在轉移性OS患者中,肺轉移最為常見(約74%),其次為單純骨轉移(約9%),約8%的患者同時存在骨和肺轉移[4]。大多數OS標準治療是在1980年代建立的,包括手術和化療在內的這些治療可以使大約60%的局部OS患者實現長期生存[5]。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OS治療一直沒有新的突破。隨著OS的生物學特性得到更好的理解,它的異質性和潛在的分子畸變也被揭示出來。然而,面對無法進行外科手術干預,對于化療藥物不敏感或不耐受的OS患者,我們能做的仍然有限。對化療藥物的耐藥性也是阻礙OS治療取得突破的一個重要問題[6]。OS分子機制研究的停滯也阻礙了我們取得新的突破。隨著OS分子譜分析技術的最新進展,我們可以尋找靶向藥物來提高生存率。在這篇綜述中,我們概述了目前可用于治療OS的手術、化療方法、免疫療法和干細胞療法,以及一些OS治療的新技術等,我們探討了OS治療突破的障礙,重點關注流行的OS靶向通路及其相關藥物。
OS的手術治療
手術切除對于OS患者的生存仍然很重要。雖然目標必須是完全切除腫瘤,但切除的范圍也很關鍵。OS的生長方式呈放射狀,形成球形腫塊。當它穿透骨皮質時,它會產生一個稱為“反應區”的假包膜層,這是由OS周圍的肌肉壓縮形成的。侵入反應區的腫瘤結節稱為“衛星”,代表原發腫塊的微延伸。手術治療時,必須完全切除整個腫瘤組織,包括反應區(衛星)。Enneking等[7]從1980年開始的一項經典研究包括手術切緣的定義和特征:病灶內、邊緣、廣泛或激進等。在OS切除過程中,當任何一點進入腫瘤時,就會形成病灶內邊緣。當手術過程中剝離延伸到或穿過腫瘤周圍的反應區時,就會形成新得的邊緣。當無法進入反應區并且整個解剖穿過健康組織時,會產生較大的邊緣。其關鍵是通過腫瘤與周圍組織的關系闡明了手術切緣的概念,Enneking等[7]的手術切緣概念是其手術分期系統發展的基礎,該系統隨后被美國肌肉骨骼腫瘤學會(MSTS)采用,目的是去除腫瘤以保留肢體功能。無論患者的OS分型如何,足夠的手術切緣對于實現腫瘤的完全切除和優化預后至關重要[8]。當患者接受術前化療已獲得足夠的手術切緣時,保肢和截肢之間的結果沒有顯著差異[9-10]。如果OS患者僅接受手術治療,盡管采用了截肢和關節脫位,其結果并不令人滿意[11]。因此,化療藥物對OS患者的生存起著重要作用。
OS的化療
近年來,OS的臨床治療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化療的進步。隨著保肢手術、新輔助化療和免疫治療的發展,其5年生存率明顯提高[12]。然而,惡性骨腫瘤仍然有極高的病死率和致殘率,因此多學科治療策略非常重要。手術和新輔助化療已被廣泛認為是治療OS的標準模式[13]。先前傳統化學療法是基于Rosen等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幾種方案,但目前在療效上沒有突破[14]。由于OS腫瘤相對耐藥,單藥化療的療效一直不理想,只有少數藥物能產生15%以上的有效率[15]。目前用于OS化療的主要藥物包括甲氨蝶呤(MTX)、阿霉素(ADM)、順鉑(DDP)、異環磷酰胺、長春新堿、表柔比星、環磷酰胺和依托泊苷等[16]。MTX、ADM、DDP和異環磷酰胺是最常用的藥物,它們以不同的方式組合使用。目前,由大劑量MTX、ADM、DDP組成的MAP方案是歐美大部分治療中心的標準方案。重要的是,化療對OS細胞的敏感性直接影響患者的生存率[6]。為消除單藥化療耐藥的特點,發展了聯合化療方案,主要目的是協同聯合抗腫瘤藥物的作用,降低單一藥物的毒性,降低耐藥性。與此同時,利用天然化合物治療癌癥近年來也備受關注[17]。另外,手術輔以化療并不是簡單的“術前化療+手術+術后化療”。新的方法是根據術后組織病理學的病理分級,根據術前化療后腫瘤壞死率調整術后化療方案[17]。新輔助化療已成為OS的標準方案,治療早期微轉移和原發灶可提高保肢手術的術后成功率。
OS的免疫療法
當William Coley首次發現使用細菌毒素可以導致腫瘤消退時,免疫療法就誕生了[18]。在人體免疫系統中,免疫細胞、細胞因子、外來威脅、自身抗原和抗體之間存在高度復雜的反應和相互作用,以實現免疫防御、免疫監視和免疫動態平衡等功能[19-20]。通過自身免疫途徑清除腫瘤細胞是免疫治療的關鍵。腫瘤的免疫反應以細胞免疫為主,自然殺傷(NK)細胞和自然殺傷T(NKT)細胞對腫瘤細胞的殺傷是重要途徑。NK細胞以外的先天免疫細胞,包括嗜酸性粒細胞、嗜堿性粒細胞和吞噬細胞,也參與腫瘤抑制[21]。對OS的腫瘤微環境(TME)的分析表明免疫細胞浸潤含有巨噬細胞和T細胞[22]。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s)的存在也為OS的免疫治療提供了新的方向。在使用體外細胞系和體內小鼠模型的實驗中,表明抗程序性死亡受體1(PD-1)抗體可以通過抑制Treg來抑制OS腫瘤體積的增加并延長總體生存時間[23]。免疫療法也渴望在其他方向取得突破,例如過繼細胞療法、溶瘤病毒、腫瘤疫苗和樹突狀細胞以及檢查點抑制劑[24]。盡管越來越多的OS患者受益,但對復發和轉移性OS患者的免疫治療仍然有限。免疫治療作用于大范圍的細胞,由此產生的細胞毒性是一個重要的限制因素,對OS患者的傷害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通過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的聯合應用,我們可能會取得更好的療效。
OS的干細胞療法
當遺傳或其他因素干擾間充質干細胞分化為骨細胞的正常過程時,就會發生OS。由于間充質干細胞可以轉化為腫瘤干細胞(TSCs),因此有機會研究TSCs與OS之間的關系。TSCs與腫瘤的發生、增殖、復發和化療耐藥密切相關[25]。因此,對TSCs的研究有助于從源頭上解決OS的復發和轉移問題。基于分離TSCs和鑒定OS干細胞表達的不同特異性表面抗原,研究人員可以創建靶向中和抗體來滅活TSCs并阻斷OS的發展。有研究發現,在缺氧環境中,TSCs可以通過上調缺氧誘導因子的表達并促進轉移性腫瘤的形成來激活賴氨酸氧化酶[26]。這表明改變TSCs生存的微環境可能是治療OS的另一種方法。綜上所述,TSCs研究的引入將OS治療的多元化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OS的新療法
OS的治療并不局限于上述治療方法,如手術、化療、免疫治療、靶向治療等,仍有新的治療方法正在研發中。光動力療法是一種新型的癌癥療法,已被證明對乳腺癌、黑色素瘤和軟組織肉瘤等淺表腫瘤有效[27]。光敏劑、光源和氧氣是能夠產生抗腫瘤作用的光動力療法的3個關鍵方面。光動力療法在OS的細胞毒性機制中發揮作用,例如細胞凋亡、自噬、壞死、細胞周期停滯、腫瘤血管損傷和免疫原性細胞死亡[28]。根據體外實驗和動物模型實驗對OS光動力療法的研究,光動力療法不僅可以根除細胞培養物中的OS細胞,而且在OS動物模型實驗中也有證據表明它具有一定的療效[29]。此外,基于納米技術的進步促進了OS的發展,并提供了克服傳統療法的新方法。納米技術的發展使得更多的納米材料被用于OS的靶向治療,例如氧化石墨烯納米材料的應用。用于治療OS的納米材料也在不斷研發中。目前,流行的納米藥物系統是聚合物納米載體、脂質體、金屬納米顆粒、氧化還原反應納米顆粒、雜化納米顆粒、介孔二氧化硅納米載體和磷酸鈣納米載體[30]。納米粒子作為優良的載體,不僅可以將各種小分子或藥物輸送至靶點,還可以與光敏劑結合制備用于光動力治療的納米藥物遞送系統。間充質基質細胞可以內化和遞送載有治療藥物的納米顆粒。這些新技術為OS治療的方向開辟了新的途徑。
小 結
OS的臨床治療經歷了長期的探索和發展,迄今為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治療技術也已經走向成熟。大劑量化療藥物的應用,增加了對腫瘤組織的作用強度,使患者的預后大大改善。新輔助化療聯合廣泛切除腫瘤,不僅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而且更好地保留了肢體功能。MRI、放射性核素掃描儀等大型醫學檢測儀器的普及,使OS的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成為可能。適用于骨腫瘤保全手術的骨材料重建已取得重大進展。腫瘤的廣泛切除已成為可能,從而顯著延長了局部無腫瘤期,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質量,并延長了患者的預期壽命。最后,化療、免疫治療、干細胞治療等新技術的研究和應用,為控制OS的局部復發和遠處轉移帶來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