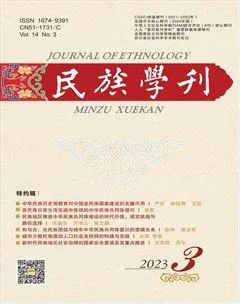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對中國多民族國家建設的關鍵作用
嚴慶 孫銘晨 王躍
[摘要]
歷史觀是記憶的出發點和認同的基石,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建設中發揮關鍵作用。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強調“四個與共”的結構一體性和“四個共同”的過程延續性,為中國歷史政治基因的延續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維護,為多民族國家整合、建設提供了思想基礎和意識形態素材,也是對外部挑戰的理念回應。問題史觀通過修改歷史認知坐標系和思維方式,銷蝕政治認同與意識形態合法性,而二元史觀、多元文化主義史觀等問題史觀沖擊了中國歷史主流話語的延續性、一體性、主體性和本土性。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以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為價值立場,以強化中華民族史觀認知、凝聚“五個認同”歷史情感、堅定歷史自信為關切,引導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求的歷史認知和歷史評價標準。
[關鍵詞]國家建設;中華民族;史觀;教育
中圖分類號:C9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391(2023)03-0001-10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族歷史觀研究”(22&ZD210)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嚴慶(1970-),男,河北樂亭人,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多民族國家建設與民族事務治理、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民族教育;
孫銘晨(1989-),女,江蘇徐州人,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多民族國家建設與民族事務治理;
王躍(1988-),男,江蘇徐州人,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多民族國家建設與民族事務治理。北京 100081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必須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增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1]歷史觀是人們對社會歷史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是哲學基本問題在社會歷史領域的延伸,體現出人們對歷史作出兼顧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解釋。有什么樣的歷史觀,就會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對歷史人物、歷史現象、歷史事件的褒貶,直接影響到對當今相關人物、現象和事件的價值判斷[2]。對歷史觀的教育可以理解為教育者通過特定的歷史教育活動,引導受教育者形成一定的歷史認知和歷史評價標準、立場,培育受教育者的特定社會歷史意識和政治實踐自覺。歷史觀教育必然與國家建設產生密切的關聯。
作為一個歷史資源豐富的國家,歷史觀教育對于現代中國的國家建設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王文光等(2022)論及中華民族史觀教育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3];海路、楊柄(2022)闡發了“認知-情感-自信”的中華民族史觀教育的實踐進路[4];趙天曉、彭豐文(2022)[5]、王延中(2022)[6]、青覺(2022)[7]等研究均注意到了中華民族史觀在歷史進程中的延續連貫的生長性、在結構上的多元一體整合性等特性。總的來看,已有研究成果為“中華民族史觀教育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這一議題做了堅實的鋪墊,但這一議題之中尚有不少討論的余地。本文嘗試在整合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史觀的意涵、價值及其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系出發,結合對問題史觀的機理、表現與危害的梳理,對中華民族史觀教育予以闡釋與解析。
一、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及其意義
歷史是一種敘事方式,敘事是一種知識的傳遞,它基于以理解為樞紐的“獲取-理解-表述”進程。人文社會領域知識的傳播其實是要產生意識和觀念的轉化,歷史敘事不能僅僅依賴實證主義的方法,重要的是建立解釋體系。有新意的歷史闡釋及其意義結構,往往不依賴于史料,而是來自于一種新的世界觀、新理念的邏輯體系。[8]因此,歷史觀的支撐,對于歷史敘事的形成和傳播,是比豐富史料更為關鍵的要素。
由于社會歷史實踐的主客觀交互性,以及受主觀活動影響而客觀存在的利益滲透性和價值滲透性,中華民族歷史觀既是關于中華民族歷史的科學認識,也是關于中華民族歷史的價值取向。[9]深入闡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抵制錯誤史觀、加強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是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共同要求。
(一)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的內涵
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歷史理論為指導,同時繼承和弘揚了中國傳統民族歷史觀的精華。中國傳統民族歷史觀為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提供了豐富資源和歷史依據;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歷史理論,為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提供了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10]
中華民族不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而是一個有著共同歷史事實、歷史敘事和命運關聯的歷史命運共同體。
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要深刻把握中華民族“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結構一體性。在相對穩定封閉的中國版圖內,各民族先民經過上千年互動、交融形成有機文明系統、文化體系、社會結構、價值信念,形成從未間斷的歷史進程與敘事,具體呈現為:各民族在政治上受到“大一統”傳統的浸潤和中央王朝的長期整合,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內聚;在經濟上互補共濟,培塑了統一性的重要物質基礎;在文化上的長期交流、互鑒、融合為中華民族的團結與鞏固提供了強大的文化紐帶和共同的向心認同。在社會結構上互嵌依存并伴隨著社會成員的不斷流動,歷史敘事成為歷史感積淀、歷史觀淬煉的素材與依據。
近代以來,各族人民在反對內外敵人的斗爭中,形成了福禍與共、前途相關的思想認知,“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自強、自新,成為各民族的普遍認同。在革命建國、發展改革的歷史轉折中,在中國共產黨的團結帶領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得以建立,各民族的共同性不斷增強,向心力、內聚力進一步強化。中國共產黨將各民族凝聚為人民政治共同體,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超越多元文化的共性認同素材和價值內核,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聚合了各民族的情感和認同。
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還要深入領會各民族“共同開拓遼闊疆域、共同書寫悠久歷史、共同創造燦爛文化、共同培育偉大精神”的過程延續性。首先,就延續性看,中華民族從起源到壯大、從自在到自覺,都是以各民族豐富的多樣性為內在肌理,將多元性與差異性匯流、融入中華民族的共同性之中。其次,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與調適性,賦予了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完善的能力,而中華文明在思想底蘊與政治文化結構上的穩定性與傳承性,又使得中華民族在不斷吸收借鑒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同時,形成一個代代相傳、生生不息的有機實體。再次,人民是歷史發展的主體,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進程的根本動力,推動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書寫了團結御侮的不朽史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而且也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7]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恒久不墜決定了中華民族歷史演進的延續性。中華民族歷史觀的核心內容,是結構的“四個與共”與過程的“四個共同”的交織互映,揭示了中華民族的命運一體性。
(二)堅持正確中華民族歷史觀的意義
共同歷史觀念在塑造民族特色的過程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歷史觀它是什么意思、如何形成、如何使用——在民族主義的構成和維持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1]277多民族國家的認同源于各民族共同歷史成就的自豪感,需要有選擇地記住過去。[12]267-268史觀就是一種選擇記憶的出發點,并成為認同的一塊基石。就當下中國的實踐來說,史觀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存在密不可分的價值共生性。[4]樹立科學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內容。
其一,中華民族歷史觀為中國歷史政治基因延續性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正當性提供了理念維護。中國的文明史包含著與長期的歷史延續性密切相關的政治文化基因,今日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就是對中國這樣一個長期延續的政治文明體的正統性的轉述,以現代性話語重申了現代中國對歷史中國的政統與國祚的接續。與這種政治上的正統性、延續性所對應的人類共同體即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華民族歷史觀也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精神動力,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能不斷鞏固中華民族共同的歷史文化記憶和歷史認同,引領各族人民牢固樹立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5]
其二,中華民族歷史觀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思想基石。從理論發展角度來看,首先,中華民族歷史觀是對百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傳承、發展與創新,揭示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性特征和各民族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辯證關系。[5]從更深遠的視角來說,建設超越族際藩籬的命運共同體始終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關切,而中華民族歷史觀代表了以歷史資源助力現代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實踐方略,為人類政治文明的遠景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借鑒。從實踐角度來看,中華民族歷史觀回應了新時代民族工作的現實需要,為正確認識中國的民族國情、制定民族政策和開展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導,也為民族工作的展開提供了應然的期許和目標。在新的歷史時期,人心歸屬與文化認同對社會政治的穩定發展起著“壓艙石”的作用,而中華民族歷史觀恰恰就是產生這種歸屬感和認同感的思想母體。
其三,中華民族歷史觀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中不可或缺的意識形態素材。歷史學科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學科,它的政治性非常強,政治觀點往往成為開展歷史教育所遵循的首要原則。[13]34就現代國家建構的普遍實踐來說,通過國民教育等途徑向公民灌輸國家意識形態,借助歷史素材強調國家權力的政治合法性與國民“我們”的身份特性,這是國家能力在意識形態領域對社會進行“濡化”的基本內容,它闡釋、解析了政治合法性的社會基礎,因而是民族建設的有力手段。這樣的政治路徑在世界各國被反復地實踐,即便僅有數十年歷史的國家,都能夠從自身短暫的歷史中為國家意識形態析出無可辯駁的“論據”,而內化于“論據”之中的歷史觀則凸顯出鮮明的情感意志的指向。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深厚歷史積淀的國家,現代國家的建構更是離不開前現代各民族的共同性所蘊含的歷史與文化認同觀念,中華民族歷史觀以歷史中的同一性、延續性要素作為多民族國家凝心鑄魂的黏合劑,形成本土性的歷史認知與集體記憶,增進各民族人民對國家的共同認同與歷史延續性的理性關照。
其四,中華民族歷史觀是對國際變局挑戰的重要回應。在歷史變局的當下,中國正處在民族復興大業爬坡過坎的關鍵性階段,激烈的國際斗爭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建設造成了不小的挑戰,但客觀上也促進了中國人民共同命運體認的明晰。中華民族歷史觀為各族人民強化內聚力、進行自我動員提供了思想工具,它重溫了近現代各族人民團結御侮的心理建設歷程,以身份自信慰藉了“爬坡過坎”中的心理落差,賦予了自身正當權利期許以合法性,構筑了抵御外部意識形態分化、貶低、否定的理念長城。
樹立正確的史觀對一個國家來講至關緊要。史觀較量是意識形態斗爭的重要形式,這在蘇聯解體的個案中得到了深刻的印證。在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消除歷史空白”改革中,針對蘇聯歷史的系統性歪曲對蘇聯改革議程造成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從“列寧是德國的間諜”到“卓婭因燒毀群眾房屋而被殺”,從“美國是反法西斯主力”到承認“蘇聯占領波羅的海三國非法”……“改革派”通過貶損革命領袖、英雄模范,埋沒蘇聯的成就、功績,放大蘇聯的挫折、“污點”,消除了蘇聯人的思想免疫力,令其引頸受戮。可以說,忘記歷史、歪曲歷史無異于抽離或扭曲一個國家的魂魄。
二、問題史觀銷蝕政治認同與合法性
歷史觀是哲學基本問題在社會歷史領域的延伸,任何史觀均有其鮮明的意識形態指向、價值觀色彩與社會政治立場,受到其所產生的社會歷史環境的深刻影響。具體到本文的語境中,“問題史觀”指的是在社會歷史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上與我國主流社會政治思想相悖的史觀,在歷史認知、敘事上具有片面、機械的特點,其理論根源是唯心史觀。自近代以來,不斷有一些來自國內外的政界、學界乃至民間的問題史觀,通過歪曲史實、移花接木、斷章取義、偷換概念等手段,解構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歷史敘事,否定社會主義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合法性,給中國的民族事務治理和共同體建設帶來挑戰。[6]
(一)問題史觀為何能操縱政治
歷史在19世紀的歐洲成為一個專門的現代學科,與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思潮的勃興有密切的關系,史觀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中,又以德國近代史學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最具代表性,[11]277曾為德意志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開辟了一條有別于英、法的等先發國家的國家意識形態建構路徑,也為“史觀操縱政治”這樣一個命題提供了有力的證成。
從歷史政治學的視角來看,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政治史悠久的國家來說,歷史本身就是政治,可以視為現代中國政治的“源代碼”。問題史觀對中國歷史的解構、重構,很大程度上會沿著貫穿歷史進程的脈絡“波及”今日,對現代中國政治的合法性闡發、維護與國家意識形態功能的運作造成消極影響。
作為敘事的學科,歷史的終極目的在于政治,政治價值是歷史觀的首要原則,意識形態對歷史敘事的影響極大,其主要目的在于通過塑造和改變民眾的思維方式,獲得他們對意識形態價值輸送者的合法性的自愿認同。[14]91誰能成功運用歷史敘事說服受眾,誰就能塑造受眾的史觀,讓受眾成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擁躉,最終獲得受眾的政治認同。
問題史觀操作政治的機理并不復雜,具體來說,就是迎合受眾獲取新知的常見心理,改寫受眾腦海中的既有歷史認知,對受眾的意識形態進行鳩占鵲巢的替換,最終讓受眾否定原有歷史認知所服務的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并接納問題史觀背后的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并作出后者希望的政治價值判斷,進而影響相關的政治議程。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理念系統,其生命力在于合法性訴求,意識形態的目的在于維護意識形態發布者的合法性,并取得受眾對這種合法性的信仰。[15]103意識形態通過以歷史傳統為原點的坐標系進行的對比,得出一個足以證明政治規則具有合法性的“數值”。因此,對歷史傳統中某些信息進行有目的性的改寫,就能夠改變坐標原點,而原有政治規則在坐標系中的合法性數值隨之降低,與新坐標原點更匹配的“新政治規則”就可以獲得更高的合法性數值,其所對應的意識形態就將取得優勢。[15]104問題史觀也遵循著同樣的路徑,以“重新評價”“重新發現”“再思考”“挖掘細節”等為名,通過用支流否定主流、用主觀分析否定客觀規律、用個別現象否定本質趨向、用碎片化不成體系的史料否定既有的深厚成體系的史料,以及混淆是非、裁剪事實、曲解真相等手段,實現對原有歷史敘事的否定和新歷史敘事的替換,修改受眾心目中的歷史傳統“坐標原點”,使原有的意識形態及其政治規則偏離原點,失去合法性,而與新“坐標原點”更匹配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規則得以成功獲得受眾的接納與信服,形成從解構、重構,到說服、塑造、俘獲的政治操縱路徑。
(二)問題史觀諸相及其存在的“問題”
談論問題史觀,以內亞史觀、新清史、征服王朝論等為代表的“二元史觀”是繞不過去的內容。這些史觀將長城內外的農牧文明對立分割,以農牧文化張力作為切口,解構中國的政統傳承,質疑甚至否定多民族共同推動中國文明發展的歷史主流。
農牧對立的“二元史觀”,其核心議題可上溯至近代日本,沿襲了江戶時代一批日本文人對中國明清鼎革的偏頗認知和幸災樂禍心理,出現了所謂“內亞史觀”,最有代表性的主張是“清朝不是中華民族的帝制國家,而是內亞的帝國”;被視為“中國”的漢人政治體是清朝這個內亞帝國的附屬部分、殖民地,而滿、蒙皆非中國,是故“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這套歷史敘事還認為,歷史上的中國文化(即漢人文化)形成后,自身文化積淀日久而衰頹“中毒”,周邊地區新生的、樸素的、強大的勢力入主中原,使陳腐的、頹廢的、飽和的、內卷的“中國”獲得新生而“解毒”,強調“外來民族的侵入”是維系中國悠久歷史的原因。結合明清鼎革之后東亞朝貢體制變化以及日本近代對華擴張的咄咄逼人之勢,不難發現此學說對華用心之險惡。“征服王朝論”源出于20世紀30年代德國漢學家魏特夫,強調立足亞洲內陸草原民族的本位視角重構文明敘事方式,認為遼、金、元、清等入主中原的同時刻意保持自身文化,與十六國、北朝、五代時被漢化的“滲透王朝”有所區別。這樣,在20世紀上半葉這個民族主義勃興的多事之秋,“征服王朝論”不僅壓縮了歷史中國的空間范圍,也解構了遼金以降中國的多元一體結構,否定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傳承。新清史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的北美,以標榜使用非漢文史料作為研究基礎而著稱,同時還十分強調清朝的內亞屬性以解構傳統“漢化”命題。新清史承襲了內亞史觀、征服王朝論中的農牧對立、“中心-邊緣”沖突等“二元史觀”的核心命題,在碎片化不成體系的非漢文獻中尋覓單方面敘述,再將其與漢文文獻中的沖突放大,形成了“標新立異”的“一家之言”。
針對“二元史觀”的主要論點,應當認識到,我國歷史上一些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之所以能比漢族王朝有效管理更為廣闊的版圖、統合更多元的民族,其深層原因絕非許多“二元史觀”所認為的“對內亞資源的繼承”“游牧優于農耕”和“主觀上對全盤漢化的拒絕”。恰恰相反,這些少數民族王朝更善于將中原帝制國家的一體性治轄的內核因子注入各種本土性治理的具體形式之中。例如,元朝破天荒地將中原王朝的科層制結構推行到了前所未有的廣袤空間,把長期游離于帝制國家一體化治轄之外的少數民族社會囊括在大一統的區域之內。又如,清代雖以多元化治理見長,其成功之處也恰恰在于根據大一統國家建設理念來改造“因俗而治”[16]:在南疆維吾爾族地區保留了伯克制,但進行了政教分離的革新,并將伯克官職由世襲制改為有層級、成體系、重績效的任免制;以系統嚴密的蒙旗制度管理各部,并進一步實行包括比丁、劃界在內的人口、土地管理措施,使蒙古族地區治理向“編戶齊民”的方向發展;在青藏高原的政教合一制度中加入了中央政權對宗教組織事務的決定性干預機制,并通過多元復合的官僚體系和多民族嵌入的政治結構、空間結構對藏地宗教權力進行制衡;在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延續明朝政策,大力推行改土歸流。從這個意義上說,元清不僅是中國,甚至可稱得上是“用夏變夷”的典范,他們的統治者深諳“多元”的關節筋絡,因而在灌注“一體”精髓和延續中華政統與“漢制”的具體操作中,其策略、手法遠比漢族王朝統治者熟稔精當,這是中華文明內聚力和進取性的重要體現。
多元文化主義史觀是現當代西方民族理論的產物。它們在追求文化平等及存寡恤弱等方面存在不可忽視的正當性,其價值主要在于通過對“多元”或“多樣性”的強調,反對普遍主義之下對于異質文化身份價值的否定和正當權利壓制。因此,其理論的開口缺乏約束,多元化或多樣性主張易于和文化保守主義、“新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及后現代“身份政治”產生聯系,存在一種與現代國家建構的主旨相悖斥的內部張力[15]。
近年來,在國內輿論場乃至部分學術討論中,上述兩類問題史觀又出現了一些合流演化的跡象,其代表者如所謂“姨學”及港臺等地“本土史觀”“原住民史觀”等。這些史觀本身漏洞百出,但充分利用了轉型、變局時代兩岸社會的焦慮、緊張、無助情緒,拿捏社會“痛點”、流毒網絡空間,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反映出主流社會的關注空白和理論防范的不足。以“姨學”為例,就中國多民族國家建設的議題來說,這種史觀拼貼了二元史觀的主要理論主張,否定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貶低中央王朝治轄傳統深度浸淫之下的社會“費拉(農夫、沒落、低劣、被閹割之義)”、缺乏“武德”,贊賞游牧文明、海權文明的侵入對狹義中國文明的淘汰和“更新”,粘連著濃厚的“河殤”余續和種族主義氣息。同時,“姨學”又摘引多元文化主義史觀的經典話術,不僅否認多民族國家的一體性,甚至進一步以漢族內部的地域、文化差異為切口,謀求對中國政治文化結構和國家建設的主體性的進一步碎片化解構,詆毀所謂“秦制”(現代中國所繼承的政治文化一體性建構傳統),完全背離了歷史主流,當引起警惕。
(三)“問題”帶來的危害
問題史觀對中國歷史的攻訐、“修正”,沖擊了中國歷史主流話語,給中國的共同體建設和國家建設帶來了不利的影響。[14]
其一,否認中國的延續性。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載體和依托的“中國”,兩千多年來未曾改變。帝制王朝的興替、政權的變遷,并不與“中國”的延續性相悖。而“新清史”等問題史觀試圖挑戰上述觀點,僅把“漢人”稱為“中國人”,把少數民族建立的遼、金、元、清稱為征服王朝、“非中國”,把兩晉南北朝等時期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治元素視為對中國的文明中斷而非接續。這種對中國歷史進程延續性的否認,必然影響現代中國的政治合法性,消解各族人民的共同歷史文化記憶與命運與共理念。
其二,解構中國的結構一體性。中國的歷史是由中國的各個民族共同書寫的,歷史上中國境內各民族群體在長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文明結構。問題史觀難以解讀中國的文明國家形態,就生搬硬套西方近代民族國家模板,削中國文明之“足”以適“一族一國”之“履”,把“中國”等同于“漢族”的國家、把漢人君主的王朝視為“中國”政權、把漢人聚居之處稱為“中國”,壓縮“中國”的地理范圍,制造“中國”概念與中國少數民族的二元對立,片面強調多元一體結構中的張力、界限和沖突,忽視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部關聯與有機整合。
其三,沖擊中央政權統續的主體性。從中國歷史發展的縱向視角來看,中央王朝的演進是中華文明體系的主流和綱繩,歷代中央政權對前代政治統續的繼承,是政權合法性與統治權威性的重要依據。從中華文明結構的橫向視角來看,在政治和文化上,歷代中央王朝相較于各周邊地方及民族,均享有無可非議的主干、核心地位。這種中央王朝統續的主體性,維系了中國作為一個政治文化共同體的長期穩態發展不輟。然而“多元文化主義”等史觀以反對文化中心主義為要義,進而把“多元文化主義”解讀為不同類型文化的“絕對平等”,混淆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間的關系,否認中華文化的國家主流文化屬性,把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局部與整體割裂、對立起來,意在顛覆中華文明共同體長期存續發展的核心結構與整合機理。
其四,挑戰中國歷史的本土性。任何史觀都是政治的體現,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相關政治理念生發之地的本土基點、立場,都必然接納某一種文明中心性而拒斥其他的文明中心性。中國受限于相對孤立的地理空間環境,前現代的文明歷史進程較為“遺世獨立”;近代以來,中國卷入全球化的時間最晚,面對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中國把握自身命運的抗爭態度又最為堅決。這種歷史客觀條件和文化意識主觀自覺,是中國百年來能夠蕩滌邪穢、涅槃重生的關鍵。因此,不論是前現代還是近現代,中國的歷史都較其他文明更具本土性的歷史脈絡,既超然于世、又堅貞不屈。而一些問題史觀標榜“價值中立”、反對“文化中心主義”、強調“全球視野”,實則是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鮮明本土特性的刻意抹殺,將中國打入“文明另冊”,置于一族一國的“普世倫理”中進行“去特殊化”,最終解構中國的一體性。
綜上,問題史觀著力于對中國社會、歷史、政治發展的否定、歪曲與解構,否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歷史理論的哲學基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問題史觀基于抽象人性論等理論前提,割裂現象與本質、必然與偶然的關聯,以歷史的相對主義否定歷史的客觀性、方向性,又基于解構、“創新”、求異的立意,追求對中國傳統民族歷史觀的重構和對厚重歷史依據的曲解。
三、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的關切與面向
歷史觀教育所要做的就是將歷史事實進行教育知識化的再生產,將其中所蘊含的歷史觀傳遞給一定社會的人,形成歷史認同的情感與意志,并激勵一定社會歷史實踐的開展。[4]青覺等學者指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包括認知體驗、價值信念、行為意愿等要素,[17]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核心的中華民族歷史觀的培育也應遵循“外在知識內化—認知轉化成為情感—情感升華生成深層意志—意志向行為外化”的心理建構過程。因此,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認知、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情感、增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自信是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的核心要義。[4]
(一)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的三維關切
培育歷史認知之維——懂得。歷史凝聚著民族的共同認知與情感期許,是民族團結凝聚的精神紐帶。民族歷史文化的傳承,將共同體與個體的命運連為一體。歷史觀教育承擔著以民族歷史記憶為素材,生成受教育者個人歷史情感的功能。這個教育過程也是受教育者通過史觀教育,從民族歷史中獲得身份認同,進而促成其社會屬性豐富完善的過程。在當前,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首先要著眼于培育受教育者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認知,具體來說,要讓受教育者正確認識與理解中華民族“一體”與“多元”的層級結構關系和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的歷史脈絡;同時,還要培養受教育者正確的歷史判斷能力,使受教育者基于科學認知,對歷史議題作出有歷史貫通感的正確價值判斷。
凝聚歷史情感之維——忠實。認知是情感的基礎,情感是認知的升華。一個人獲得了關于國家的知識,并不等于國家認同感的形成以及必然能外化于行為,國家認同行為的持續表現需要個體積極、真實體驗的強化。[18]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需要將受教育者所獲得的知識性歷史認知升華為受教育者對中華民族共同體主動的認同情感,[4]具體來說,形成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認同。
堅定歷史自信之維——有我。培養各民族成員形成整體性的中華民族歷史觀,促進中華民族歷史自信的生成與強化,是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的重要使命。樹立科學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就是要以歷史為底氣,從歷史中擷取中華民族共同體自信。在文化自覺的作用下,歷史記憶流變能夠始終指向自我認同。[19]基于共同歷史記憶的歷史自信往往經由歷史自覺確立起來,而這種歷史文化自覺意識的喚醒需要通過教育來實現[4]。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通過引導受教育者形成高度的歷史自信和認同情感,在受教育者的心靈深處構筑起防范問題史觀解構、沖擊的思想之盾,并激勵其生成參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實踐的信念之矛。
(二)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三重面向
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是指通過特定的歷史教育活動,引導受教育者形成科學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認知與中華民族歷史評價,培育受教育者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實踐自覺。[4]在對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的實踐關切進行梳理之后,筆者側重提出教育行動中的三重面向。
其一,強化中華民族史觀認知。當下的歷史教育,應增強受教育者對中華民族“四個與共”結構一體性和“四個共同”過程延續性的認知。
首先,要重視基于“四個與共”的各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基因教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強調政治歸屬與認同的各民族的命運共同體,從長期的歷史發展來看,各個民族所生活的制度環境,是各民族政治制度交流、互鑒的產物,具有共同要素逐漸增多、日益趨同的趨勢,盡管有分裂、紛爭,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始終是各民族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經濟上的互補共生,成為中國統一性的重要物質基礎,不同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農、牧、工、商多元互補共濟的經濟紐帶,物質文化交流、互鑒、融合是中華民族發展演變的歷史主流。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中崇尚“和合”“與共”的內容鋪就了中華民族休戚與共、命運與共的文化底色。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引領下,歷史教育中應正確處理“多元”與“一體”的辯證統一關系,正確把握差異性與共同性的關系,突出共同性的主導、方向和根本地位。
其次,要重視基于“四個共同”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記憶教育。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在締造和捍衛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長期歷史過程中,不斷交流、交往、交融,共同推動中國的歷史演進和社會進步。“四個共同”的落腳點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共同疆域、共同歷史、共同文化和共同精神,本意即在于立足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與現實,以中華各民族共同性特征、表現為起點和歸宿。各民族“共同”基礎上的歷史進程,強調的是“共同”思想理念和理論視野。[20]“四個共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堅實的歷史依據,在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中要讓受教育者牢記“四個共同”這一中華民族上下數千年的血脈傳承線索,形成對各民族共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真摯情感。
其二,增進“五個認同”歷史情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正確把握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在實際工作中,要搞清楚哪些方面必須“同”,哪些方面可以“異”——各族干部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高度認同。[21]中華民族歷史情感教育應聚焦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凝聚起來的共同歷史情感,不斷增進“五個認同”。五個認同是中國人民在漫長的文明發展進程中不斷摸索總結出的思想成果,是由近現代中國人民以巨大犧牲為代價,于數十年政治流變中篩選出的理念精華,順應了歷史和時代的要求,也得到了歷史和實踐的檢驗。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進程中,應當堅持以五個認同引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首先,以各民族在共同締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所形成的共同歷史文化為重點,增進受教育者對中華文化的深層次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共同性,離不開前現代社會各民族共同性所蘊含的歷史與文化認同觀念,古代中國的歷史經驗與文明傳統對于現代國家認同的形成具有持續性影響,是塑造現代國家集體認同的重要元素。[22]
其次,以近代各民族爭取民族解放的歷史經歷為重點,增進受教育者對偉大祖國和中華民族的自覺認同。費孝通先生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中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23]17近代中國歷史既是一部民族屈辱史、民族抗爭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的自覺形成史。內憂外患的深刻危機使各民族在團結御侮的過程中真正團結起來,從自在走向自覺。中華民族近代史的教育,應使受教育者真正體會到中華民族是一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再次,以現代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革命、建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為重點,增進受教育者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覺認同。20世紀以來,各民族的聚合不是社會的自發秩序,不是西方現代性單向的沖擊,而是來自政治力量及其主導的社會運動的積極建構,政治理性化建制主導著社會規模的凝聚形態與機制。也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在傳統國家瓦解、大一統秩序瀕于顛覆、中央集權消解的危險情況下,以中國共產黨的政黨中心主義路徑完成的。中國共產黨把人民主權的現代性內容注入了國家重組過程,將傳統中國完整轉型為現代國家,黨的領導構成了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的政治紐帶。[24]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換言之,現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建設,從根本上說就是由中國共產黨推動和實施的,是黨將民族凝聚為政治共同體的政治整合。[25]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合法性在黨領導的現代中國得到延續,各民族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整合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從歷史文化復雜多元的各民族的群眾凝聚為具有共同政治認同的人民。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華民族歷史性自覺的卓越產物,是中國歷史本土性的延續,是中國人民長期艱苦奮斗而來的政治果實,呼應了人民民主理念的核心訴求。
其三,堅定歷史自信。歷史自信根植于社會主體對民族、國家歷史的正確認知、理性理解和科學審視,是民族、國家理性精神成熟的表現,能促進人們正確認識和理解國家、民族的歷史與現實,并對其未來發展前途產生堅定的信念。[4]各民族千年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締造偉大祖國的歷史,將兩千多年以來多元一體、向心凝聚的文明演進主線深埋于受教育者的內心,產生對中華民族歷史與文化的充分肯定。各民族在近現代團結御侮的歷史教育,夯實了受教育者對中華民族的身份自覺與認同歸屬,激發了受教育者對中華民族歷史及自身身份的敬重與欽佩。革命、建國、發展、改革的現當代史為受教育者搭建起審視歷史、當下與未來的坐標系,凝結為對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體認,使受教育者內心升騰起以歷史主體身份把握、見證百年變局過程的共情與自豪。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既有獨特的優勢和基礎,又有超越其他現代民族國家的普適性意義。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復興為歷史使命,黨的領導是傳承多民族統一國家歷史合法性的根本保證,是實現現代化進程、滿足現代國家治理的必要條件,也是國家建設的核心動力。中國人民百年來的奮斗歷程與績效證明,圍繞中國共產黨的團結與凝聚,是中華民族在當下克服一切困難險阻的制勝法寶。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是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的最高體現。[26]對黨的領導的信奉與堅守,應成為堅定歷史自信的核心內容。
四、結語
中華民族史教育以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為其價值立場,通過歷史教育引導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求的歷史認知和歷史評價標準、立場,這是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和多民族國家建設的共同要求。在總結上述歷史教育建議的基礎上,本文認為,當下中華民族史教育應把握:第一,講得對,要站對立場。要深入挖掘中華民族深厚的歷史底蘊,以堅實的史料體系、話語體系為支撐,講清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發展脈絡,增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讓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入心入魂。第二,講得活,要有效發力。中華民族史教育應體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形成中華民族的重要條件,也是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重要條件,更是各民族發展的必要前提。應當闡釋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等方面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第三,講得實,要增強信度。講清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進程,用歷史事實正確回答中華民族從何處來、向何處去,充分運用史料,生動、有力地呈現“四個共同”的事實與史實。第四,講得準,突出問題導向,回應社會各界關切。中華民族史教育應針對問題史觀和錯誤的歷史認知,明辨大是大非、堅定立場,旗幟鮮明地公開批駁錯誤史觀言論、澄清認知、充分揭露。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民族建設的意涵日益被國家建設所包容,從歷史的角度研究國家建設的理念和實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建設中,歷史資源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華民族史觀、中華民族史教育則深刻影響著我們怎樣回看歷史,又怎樣翹首未來,進而選擇命運。
參考文獻:
[1]本報評論員.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N].人民日報,2021-08-29(001).
[2]李捷.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歷史觀[J].高校理論戰線,2008(10):6-8.
[3]王文光,胡明,馬宜果.中華民族歷史觀與“四個共同”研究論綱[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39(03):17-23.DOI:10.13727/j.cnki.53-1191/c.20220505.015.
[4]海路,楊柄.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內涵、價值與實踐路徑[J].民族研究,2022(04):13-24+139.
[5]趙天曉,彭豐文.新時代黨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及其重大意義[J].民族研究,2022(02):36-47+139.
[6]王延中.正確認識中華民族歷史觀[J].歷史研究,2022(03):22-32.
[7]青覺.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J].前線,2022(08):47-51.
[8]陳衛星.傳播學敘事的歷史學技藝[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8(01):84-94.
[9]陳新夏.歷史觀的價值維度及其與認識維度的關系[J].哲學研究,2021(04):16-25.
[10]程春華.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N].人民日報,2021-11-30(009).
[11]坎迪斯·古切爾,琳達·沃爾頓.全球文明史[M].陳桓,等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2]威爾·金利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M].馬莉,張耀昌,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
[13]臧嶸,周瑞祥.歷史教材學和史學論叢[M].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06.
[14]王海洲.合法性的爭奪——政治記憶的多重刻寫[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15]王希恩.多元文化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兩點比較[J].科學社會主義,2010(02):8-12.
[16]馬大正.中國古代的邊疆政策與邊疆治理[J].西域研究,2002(04):1-15.
[17]青覺,徐欣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概念內涵、要素分析與實踐邏輯[J].民族研究,2018(06):1-14+123.
[18]歐陽常青,蘇德.學校教育視閾中的國家認同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12,23(05):10-14.
[19]宣朝慶,葛珊.歷史記憶與自我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自覺[J].人文雜志,2021(12):16-25.
[20]于玉慧,周傳斌.“四個共同”: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闡釋的新向度[J].貴州民族研究,2021,42(06):35-41.
[21]尤權.做好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科學指引——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J].求是,2021(21):42-49.
[22]朱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共同性的現代性轉化及發展[J].民族研究,2021(03):23-38+139-140.
[23]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版)[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
[24]汪仕凱.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度的歷史政治學分析[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0,34(01):28-38.
[25]周平.多民族國家的政黨與族際政治整合[J].比較政治學研究,2011(01):34-49.
[26]郎維偉,陳瑛,張寧.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五個認同”關系研究[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03):12-21.
收稿日期:2023-01-07 責任編輯:王 玨
- 民族學刊的其它文章
- On the Building and Practice of a Social Support Network for the Urban Ethnic 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A Case Study of “Ethnic Homes” in Guangzhou
- The Early Practice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Visual Ethnodanceology
- Core Issues in the Philological Study of Ethnic Literary Integration History in Ancient Southwest China
-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Trend of Red Revolutionary Tourism Symbiosis Atlas in Sichuan Province
- A Development Model for the Homestay Industry in Qiang Area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Based on a Survey in Wenchuan County, Aba Prefecture
- “Multi-leve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Ethnic Areas:Structural Features and Internal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