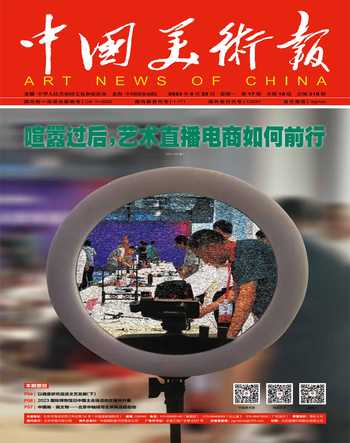不斷流動書寫的當代藝術
楊宏鵬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每一個生活在時間中的人們,構成這個世界無數存在者的出場序列。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寄蜉蝣于天地的時光旅行,讓人格外珍惜有限的生命,既然不能永生,那就要制造出一些超越性的存在,去探尋彼岸、通達無限、映射永恒。這些無數人類智慧的結晶,不僅有早期的宗教,還有科學、哲學和藝術。
歷來關于藝術的定義眾說紛紜。如果我們考察不同歷史時期被人們指稱為“藝術”或“藝術品”的那些對象就會明白,企圖為藝術下一個固定而明晰的定義注定只是捕風捉影。我們很難說明,維倫多夫的原始小石雕、馬王堆的戰國帛畫與安迪·沃霍爾的罐頭盒、草間彌生的無限鏡室之間究竟有何共同性,但它們卻分別在各自的時代為人們提供了精神的寄托和超越性的遐思。只因它們各自誕生的時代之間相距太過久遠,以致失去了輕易在其間找到關聯的可能。然而在時光的連續之流中考察相鄰或相近歷史時期的藝術,我們卻可以看出彼此之間的脈絡:承襲與演進。演進過程中微小的差異性,經過時間的放大,就會慢慢變得面目全非。這在科學學說中,叫做“蝴蝶效應”;在哲學學說中,叫做“家族相似性”。
那么,于藝術本身呢?無它,這就是藝術的自性,是其與生俱來的宿命。
在關于藝術的種種提法中,“當代藝術”永遠是一個最具爭議的命題。因為每一代使用這個術語、討論這個話題的人,都是“當代”人,都認為自己站在可以回望全部歷史的哨塔之上。他們自然而然地以來到這個世界上的那一刻劃分古今,以自己的藝術創作、理論思考來為“當代藝術”命名。
當代的藝術家和批評家一次次地劃定“當代”的起點:1917年、1945年、1960年、1989年……不斷游移的邊界其實折射出這種切割的彈性,逐漸退行的趨勢則再一次成為“當代永遠距當下不遠”的證明。于是藝術家和史論家們又開始思考“當代藝術”不同于“現代藝術”“古代藝術”或“傳統藝術”的內在和外在的特征——雖然許多人也承認,“當代藝術”和“現代藝術”有許多交集,而“傳統藝術”在當代仍有著旺盛的生命。
“當代藝術”的特征終于還是被一點點總結提煉了出來:突破前人的創作手法、探索新材料新表現的可能性、解構經典的結構模式、反叛傳統的藝術觀念、顛覆既有的審美習慣等。而這些不是所有偉大藝術的共同表現么?不是所有時代有著遠大抱負的藝術家共同的追求么?不是真正藝術的本質特征嗎?
人類的文化具有歷史層積性,我們站在此刻回望過往,總會歸納提煉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而且,這種回望點越靠后,沉積越豐厚,甚至會出現幾何性的遞增。因此賴以分析的樣本越大,其特征的置信度也越高,在資訊爆炸的今天我們似乎比過去的任何時刻更有資格做出回顧和論斷。然而,如果將來的將來,有站在時間之維上更靠后的“當代人”再來做考察做總結,則今天的觀念、結論、范疇是否又會被改寫?
“當代藝術”就是這樣一個范疇。“當代藝術”也只是便于我們研究藝術史、理解藝術現象的一個紐結,一種現階段的臨時界定而已。
創新是藝術發展的核心動力,這其實是一切時代藝術的共有特質,正如每一代人都曾是他們那個歷史時期的“當代人”。藝術不斷地與“當代”遭遇,因此藝術始終在不斷地推陳出新、超越過去。但無論是藝術的傳統還是藝術家的修養又都根植于歷史、承襲于過去,所以,藝術家們都有一種深深的焦慮:如何掙脫傳統的裹挾,創造出屬于自己的風格與時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藝術體認。當塞尚用幾何的筆觸在平面上涂以色彩堆砌成風景,畢加索趕緊把筆下的女郎疊加上正面側面的兩只眼睛;莫奈的睡蓮變幻出晨昏午旦的光影,梵高的向日葵溫暖了每一顆寂寞的靈魂;當杜尚把小便器搬進美術館,博伊斯開始費力地向死兔子解釋圖畫的構成;羅伯特·史密森用螺旋形的防波堤阻擋了后來者的前進,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決定藝術家親自上陣;瑪麗蓮·夢露的頭像被安迪·沃霍爾用絲網漏印,一條倒霉的鯊魚被達米恩·赫斯特永久封存。如果約翰·凱奇4分33秒的沉默讓人學會了傾聽,徐冰的有字天書是否增長了觀者的學問?
一代代的藝術家們前赴后繼地與“當代”迎面相遇,他們殫精竭慮地創作、創造、創新,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表達、表現、表征。他們通過藝術與“當代”的相互糾纏,探索了藝術的各種可能。
或許,本來就沒有所謂的“當代藝術”,有的只是永遠的“當代”、永恒的“藝術”。正如月映萬川,萬川的月影,都不過是共相與殊相的辯證;所謂“古代”“現代”“當代”的藝術,也只不過是“藝術”在當下視域的無窮分身。
(作者系河南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