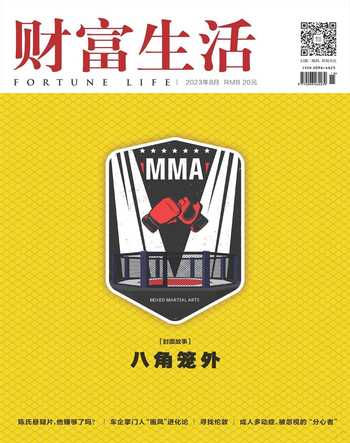成人多動癥被忽視的“分心者”
游星

研究表明,高達三分之二的ADHD患者在成年期仍會保留部分甚至全部的ADHD特征
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俗稱“多動癥”,是兒童最為常見的精神行為障礙之一,表現為注意力不集中、多動和沖動等特征。公共衛生數據顯示,ADHD在全世界范圍內的發病率為3.4%,在中國青少年群體內的發病率約為6.3%,其中60%~80%的患兒疾病癥狀會持續到成年。2017年的一項研究表明,盡管ADHD通常發病于兒童時期,但不會隨著年齡增長自動消失,通過對ADHD兒童長達15年的追蹤研究發現,高達三分之二的ADHD患者在成年期仍會保留部分甚至全部的ADHD特征,而成人ADHD患者的發病率為2%~5%。
由于大腦發育的特殊性,ADHD患者的行為與情緒表現與家庭和社會期待不符。ADHD兒童患者通常表現出注意缺陷、多動、沖動、情緒失控甚至暴力行為,男童與女童的患病比率約為3∶1,這可能是因為ADHD男童表現出的沖動與情緒失控使得他們比以分心、回避和拖延為主要特征的患病女童更容易受到重視,并因此確診。隨著精神衛生知識的普及與各種兒童ADHD救助與診療機構的成立,許多原本被認為是頑劣、愚笨的表現被確診為ADHD,得到了及時的干預和治療,對兒童本身及家庭而言都是莫大的安慰。
盡管兒童ADHD越來越受重視,但成人ADHD卻少有人問津,仿佛ADHD到成年后便會不藥而愈。這些“隱身”的成人ADHD患者忍受著分心、拖延、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和行為障礙的折磨,卻很難為自己亂麻般的生活找到根源,只能將問題歸結到自己身上——自己是不是太軟弱?意志力不堅定?太容易分心走神?——被迫承擔起這種“錯誤”的后果。

ADHD是一種神經系統發育障礙,圖為神經元結構示意圖
事實上,ADHD是一種神經系統發育障礙,這部分患者的大腦發育和神經遞質水平和普通人群不同。目前造成ADHD的確切原因尚且沒有定論,但科學研究公認ADHD是神經生理和高度遺傳的疾病。基因、環境、不同人生階段、外部刺激等等都是影響ADHD癥狀輕重的因素。為了消除對ADHD患者的偏見,目前學界和醫療機構正在嘗試用“分心者”來替代原本的“ADHD患者”一詞。香港的專注力促進會將ADHD翻譯為“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癥”,并且呼吁患者不要將失敗歸因于自身,而是對這種失調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認知。盡管ADHD無法完全治愈,但有辦法運用各種手段控制這種障礙,分心者們同樣可以過上成功、健康、幸福的生活。
ADHD依據臨床表現的不同被劃分為三個亞型:ADHD-I(注意力障礙型)、ADHD-HI(多動沖動型)和ADHD-C(混合型)。注意力障礙型的ADHD表現為很容易分心、難以集中注意力、愛做白日夢、健忘、丟三落四、難以完成結構性任務等,在患者總數中占比30%;多動沖動型ADHD的主要表現為躁動不安、難以等待、難以靜坐、話多容易打斷他人、行為沖動甚至帶有一定暴力傾向,這部分患者大概占比10%;混合型的ADHD則兩者兼而有之,約占總患者群體的50%。同時,ADHD經常和其他精神障礙共存,它本身就是孤獨癥譜系(ASD)的共現障礙之一,成人ADHD患者中常見有焦慮障礙、抑郁障礙和藥物濫用問題伴生。
對ADHD的確診目前主要是通過量表篩查實現的,但篩查量表并不等于確診,需要結合訪談、神經心理測驗、發育史和日常生活表現來做臨床上的評估。成人ADHD自評量表(Adult ADHD Self-Report Scale, ASRS)由世界衛生組織和來自紐約大學醫學院及哈佛醫學院的成人ADHD工作組基于《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第4版中的ADHD診斷標準聯合開發,是針對成人 ADHD 篩查的自我報告量表。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人員根據《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的第5版中對ADHD診斷標準的更新,形成了新版的ASRS。ASRS中包含18個問題,分別從注意力障礙和多動/沖動控制障礙兩方面對ADHD水平進行評估,這兩者有任何一項的單項總分超過17分就說明極有可能存在ADHD。
在碎片化閱讀和短視頻的沖擊下,注意力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稀缺資源,這也是為什么以注意力缺陷為主要表現的ADHD會逐漸為公眾所關注。
注意力缺陷在過去可能不會對個人生活和社會發展造成太多困擾,但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和現代生活節奏的加速使得給予成人ADHD患者的空間越來越少,容易分心拖延、難以專注完成任務、社交困難、低自尊和自信不足會被貼上“失敗者”的標簽,從而陷入自我懷疑和厭惡,加劇拖延和情緒障礙,形成惡性循環。
ADHD患者通常控制能力較弱,工作記憶不足。工作記憶指的是在解決認知任務的過程中,用于信息加工并同時保持與當前任務信息相關的、能量有限的短時記憶系統,它是人類認知活動的核心,對人們進行學習、記憶、思維及問題解決等高級認知活動起到重要作用。一項來自北京大學的研究表明,成人ADHD患者工作記憶能力受損與其學業和職業困難密切相關。他們可能存在語言工作記憶能力損害,在中等記憶負荷任務上受損最嚴重,反應慢且其注意力波動大。成人ADHD患者的注意力缺失可能與其工作記憶容量下降、整體輸出不足及注意力維持能力差相關。
一個常見的誤區是,ADHD患者在任何事情上都缺乏注意力。然而,ADHD患者的注意力缺陷問題本質上是注意力資源分配和維持的問題——
他們對不感興趣的領域無法集中注意力,盡管這些領域可能非常重要;而對于他們感興趣的領域,他們的專注力甚至可能超越常人,即便這些領域可能無關痛癢。ADHD患者在某一方面擁有高能量,對感興趣的領域高度集中,可能在某些領域內非常成功,但應付生活其他方面的能力較差,從而在婚姻、學業和事業等方面備受挫折,成為他人眼中“非常聰明但一事無成的人”。
學者們對于這種注意力缺陷進行溯源,發現神經發育因素、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都可能作用于ADHD患者的注意力危機。ADHD患者的大腦前額葉發育緩慢,人腦中有主管學習、自我抑制、產生動機等的網狀活化系統,在這種網狀活化系統內,存在主管注意力的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色胺酸等神經遞質。缺乏這些物質或者神經遞質異常時,可能會誘發ADHD。
同時,ADHD與遺傳高度相關。1972年便有研究表明,ADHD兒童的父親當中有較高的ADHD患病率,ADHD兒童的親生父母比起養父母,其精神病理學癥狀更為明顯。2002年的一項研究指出,多動癥和精神病并發癥家族史的存在,可能導致兒童ADHD癥狀延續到成人期。目前學界流行以神經影像學來研究ADHD的遺傳因素,神經影像學的手段可以詳細檢查基因對于人類行為的影響,從而尋找ADHD的遺傳基礎。2005年,一項基于神經影像學的研究證明了有兩個多巴胺基因會影響到ADHD患者的大腦。ADHD的生物學研究如今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具體發病原因仍未能完全明確,約有半數研究者支持遺傳影響的假說。
不過,環境的影響仍舊無法被忽視。比如父親的酗酒行為和后代罹患ADHD呈現相關關系,父母的失職以及家庭功能失調同樣導致兒童ADHD行為的惡化和繼續發展。統計發現,在ADHD兒童的父親中反社會人格障礙的患病率較高,而母親中軀體人格障礙的患病率較高。總而言之,成人ADHD既受到神經發育和遺傳等生物學因素影響,同時也受到環境和外界刺激的影響。

ADHD患者的注意力缺陷問題本質上是注意力資源分配和維持的問題
與大眾認知不同,ADHD人士也可以表現出眾,他們往往會成為改革者、創新者、探索者、思想家、詩人和出色的藝術家。換個角度看ADHD帶來的注意力和沖動問題,ADHD人士容易分心正是因為他們對于一切都有好奇心,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充滿了精力、專注力和創造力,并且興趣點非常容易轉換。
ADHD患者因為注意力缺陷和沖動問題會遇到很多挫折與麻煩,甚至感到人生處處受阻,但他們也有長處:靈活跳躍的思維、能夠快速切換任務的能力、獨特的創造力和審美感知。雖然他們對枯燥和重復的勞動深感疲憊,但有挑戰性和創造性的活動卻能夠激發他們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和專注力。《哈佛商業評論》曾經推薦過一些適合ADHD人士從事的職業,包括企業家、體育運動員、咨詢顧問、媒體記者和公關等等,這些工作往往要求快速反應、多任務切換和創新意識,正是ADHD人士特有的長處。
萊昂納多·達·芬奇是文藝復興時期最負盛名的藝術家、科學家、建筑師以及發明家,他為后世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藝術品和科學資料,同時他也可能是最出名的ADHD患者之一。根據他自己留存的資料和同時代人的記錄,達·芬奇有嚴重的閱讀障礙,在書寫方面存在困難,常常在畫到一半時突然放棄手頭的畫作,轉而投入新的研究。他花了整整十六年才完成著名的《蒙娜麗莎》,較為順利的《最后的晚餐》也花了三年時間,并且因為種種原因延期。在為資助人工作時,他坦言自己沒有完成任何完整的作品,他也是同時代藝術家中較為貧困的一位,原因就是他很難專注于創作某件藝術品。ADHD常被誤會是行為不端、智力低下,但ADHD跳躍式的思維可以激發創造力,而興趣點的快速切換可以被引導成對創新和變革的追求,事實上,許多領域內取得非凡成就的人士都面臨著ADHD的困擾,比如愛迪生、莫扎特、愛因斯坦等人,他們同樣聰明敏銳,有些甚至未曾經過治療。

對ADHD的認知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大腦的先天特征和影響,增加洞察力,卸下心理負擔
美國的愛德華·哈洛韋爾博士多年來專注于ADHD科普和治療領域,他的“分心四部曲”里記錄了他長期以來追蹤和治療的ADHD病例。這些ADHD患者來自不同的階級與背景,從事各行各業,曾經面臨嚴重的注意力缺陷和多動障礙困擾,但都通過藥物或者行為認知治療等手段重新找回了自我。愛德華·哈洛韋爾博士在書中討論了信息超負荷、責任超負荷、高速運轉的生活以及處處可見的干擾和機會怎樣加重了ADHD患者的孤獨,并且提出了他著名的觀點——“分心不是我的錯”,旨在消除公眾對于ADHD的歧視、偏見和恐慌,鼓勵和支持ADHD患者及家屬克服障礙、發揮長處、實現自我價值,同時用開放的心態看待藥物治療和行為認知治療等手段,用科學合理的手段提高生活質量。
患有ADHD絕不意味著“智商低下”“個性軟弱”或者“反社會”,就像近視的人需要眼鏡來輔助他們看清東西,ADHD患者也可以借助一些手段過上正常的生活。有時候,備忘錄、代辦清單和日程表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家人和朋友的監督、支持和鼓舞對于容易分心和喪氣的ADHD患者來說非常重要。藥物現在也被普遍應用于ADHD的治療中,興奮劑藥物如利他林、優選安非他命和匹莫林以及抗抑郁劑如地昔帕明等都是常見藥物,確診患者需要遵醫囑用藥。
藥物效果和副作用因人而異,但醫學界呼吁不必將藥物治療視作洪水猛獸。還有一個經常被忽略卻非常重要的事實,那就是ADHD患者應當盡量減少屏幕使用時間,我們的大腦還沒有演化到位,無法應付來自虛擬世界的視覺刺激和即時滿足的猛烈沖擊,每天屏幕使用時間較長被研究證實會損害大腦的主動注意能力。
對ADHD的認知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大腦的先天特征和影響,增加洞察力,卸下心理負擔。即便真的罹患了ADHD,我們也應當有勇氣說出“這不是我的錯”,然后用更合適的方式提升自我,找回生活的尊嚴與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