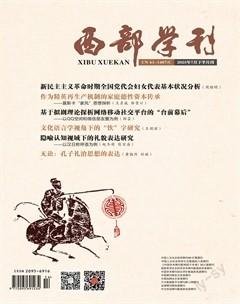馬爾庫塞“異化”理論視域下的人類困境和超越向度
摘要:馬爾庫塞以批判性的視角指出“后工業化社會”表現為以技術控制實現對人的統治,因技術混淆了人內心的真實需求,其根源在于人的“異化”,實質是“科學至上”“技術至上”成為整個社會自覺的價值追求,無產階級淪落為勞動工具和等價物,陷入“單向度”的桎梏。基于動態變化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馬爾庫塞以馬克思“自由個性”思想為指引,提出了“異化”理論。他在闡述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生態五大領域人異化為“工具理性”并研究其內在聯系的基礎上得出結論,認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必須引導人們樹立健康向上、理性發展的價值理念。科技帶給人們的負面效應,要在技術運用過程中加以有效規范和控制,把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程度。
關鍵詞:后工業化社會;異化理論;馬爾庫塞;人類困境
中圖分類號:B712.59;F09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3)14-0038-05
The Human Dilemma and Transcendence Dim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cuses “Alienation” Theory
Zhou Tianyu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Marcuse pointed out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hat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omination of humans through technological control. Technology confuses the real needs of human beings, the root of which lies in the “alienation” of humans. The essence is that “supremacy of science” and “supremacy of technology” have become the conscious value pursuit of the whole society, while the proletariat has been reduced to a tool and equivalent of labor, and has fallen into the shackles of “one-way”. Based on the dynamically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capitalism, Marcuse proposed the theory of “alienation” guided by Marxs idea of “free individuality”. On the basis of his elaboration of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beings into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the five major fields of culture, society, politics, economy and ecology, as well as his study of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he concluded that people must be guided to establish the value of healthy and ration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echnology on people should be effectively regulated and controlled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effects.
Keywords: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lienation theory; Marcuse; human dilemma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陣營中的各工業國從戰爭廢墟中崛起,在物質生產和精神生活等方面表現出與戰前工業社會不同的時代特征。以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為代表的社會學家,將冷戰時期以西歐、北美為主的資本主義國家概括為“后工業社會”[1]。簡言之,后工業社會“包含著舊可能性的連續統一體發展所達到的最完整階段”[2],親身經歷時代巨變的法蘭克福學派巨擘赫伯特·馬爾庫塞(Marcuse)通過“否定之否定”馬克思的勞動異化、黑格爾辯證法的否定性、弗洛伊德的文明觀、盧卡奇的物化思想及韋伯的工具理性,在結合自身經歷的基礎上,得出批判性極強的后工業化社會“異化”理論,旨在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內耗和縱欲過度問題,實現人的真正意義上的自我實現和全面發展,進而構建一個公正、自由、和諧的社會。
一、國內馬爾庫塞“異化”理論研究概述
20世紀80年代,我國掀起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熱潮。因學者們發現該學派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質及其弊端的思辨性和批判性達到了新高度,開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境界。本文首先回顧學界就馬爾庫塞“異化”理論衍生出的物化意識形態和技術異化兩方面的內容。
(一)關于物化意識形態的探討
我國多數學者認為馬爾庫塞“異化”學說所包含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物化意識形態。如陳振明提出,馬爾庫塞關注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批判,但并未觸及發達工業社會的實質,因為它本質上與馬克思主義是完全剝離的[3]。蘇平富認為,馬爾庫塞看到技術理性是一種欺騙性和控制力超過傳統統治形式的統治,其實質是維護現存統治的正當性,而“新感性”則是反抗技術理性的一種力量[4]。張成崗從三個維度比較馬爾庫塞技術批判與意識形態批判的關系,認為意識形態已經滲透到生產過程中,沒有絕對不變的客觀理性,而是隨著經濟基礎的演變不斷重構組合,技術合理性是衍生而來附屬品,并在后工業化社會成為新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5]。王曉東以馬爾庫塞“永恒化的生存斗爭”為論據,提出發達國家政治架構的變革,使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傳統界限被超越,日常生活中的經濟行為既是經濟基礎,又是意識形態[6]。張秀琴則強調,馬爾庫塞以“技術意識形態理論”闡明“面對社會的極權主義特征,技術‘中立的傳統觀念不能再維持下去了”,進而構建前哈貝馬斯時期技術意識形態論的大廈[7]。
(二)關于技術異化的探討
20世紀80年代初期,馬爾庫塞“技術異化”理論的價值在學界交流碰撞間獲得了再發現。如江天驥對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社會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并首先向國內介紹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內涵[8],而馬爾庫塞的“科技異化”給我國學者帶來了反省科技發展對社會負面沖擊的新視野,發展了對技術異化這一命題的探索與爭鳴。徐崇溫首次完整闡述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各個流派的主要觀點和師承關系[9]。張峰在1988年譯介的《單向度的人》,對國內闡述技術異化本質的“單向度理論”提供研究的文本基礎[10]314。進入21世紀,衣俊卿指出“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人類社會的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人類展示出過去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力量,徹底而不可逆地改造了自然界,彰顯了個人與社會集團的創造性和自由性,但隨之而來異化現象越來越普遍,即人類逐漸被自己再加工、再生產的有形物或無形物所控制,一種隱含于物質之中的精神力量控制著所有的人”[11],故而對當代社會的本質判斷更為清晰。范曉麗將后工業化社會的技術理性和相應的感性損失作為評介對象,抓住觀念史和真實史運動的內在統一性,梳理馬爾庫塞批判理性和新感性的內容、價值和啟示[12]。
二、“異化”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
發端于英國的工業革命,使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遍布全球。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馬克思和他的追隨者從不同層面探討資產階級為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剝削工人階級的方法,撕去一切虛偽的面具[13]。盡管由于科技的迭代升級,剝削的殘酷程度有所提高,但“科技成為統治整個人類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人們渾然不知地走向資本主義安排的囚籠”[14]。這一新的后工業化社會特征,使“異化”成為學界關注的中心,馬爾庫塞基于動態變化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對“異化”理論的各個層面進行了提煉。
(一)政治背景
20世紀后半期,資本主義社會壟斷程度加深,法律在政治上擴大了工人階級的參與權,但權力掌握在少數精英集團手中的現實未能改變[15]。尼爾·波茲曼指出:“當代工業設備的組織技術基礎并不完善,長此以往必然形成技術壟斷,成為極權主義”[16],其特征是技術合理性統治取代了過去赤裸裸的人身剝削,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隱性統治得以穩固。馬爾庫塞認為,“技術和資本的高度壟斷改變了原有的政治局面,取而代之的是在資本和權力控制下的全新政治局面”[17]91。消費的意義已經從簡單化的社會經濟行為被賦予新的社會權利,不再單純歸納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彰顯出一種符號性的意蘊[18];鮑德里亞談到“消費由過去單純占有和消耗各種商品和服務,逐漸被賦予主流文化領導下一種全新的消費意識形態,而這種嬗變恰恰滿足了資本主義新生產力的發展需求,也是重新構建社會價值體系,最大限度地滿足生產力發展的壟斷需求”[19]63。
(二)經濟背景
科技革命一方面使人在物質層面得到空前的享受,但主體性正在喪失,權力和資本代替語言成為人與人交往的媒介[20]。自動化程度的加深推動了流水線式的生產方式,先進的科學技術通過各種傳播媒介的力量,引導人們沉浸在對物質的渴求中無法自拔。馬爾庫塞對生產者被商品奴役的現實如此解釋——勞動者渴望消費的自主,但可供消費的范圍被限制框定,不得已被虛假選擇性消費所麻醉;他們希望通過消費來強調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從而被周圍的人和群體所認同[21]56-57。
(三)文化背景
資本主義后工業社會是生產力、生產方式空前發達的富裕社會,但文化的商品化使統治者的意志侵入私人領域,人們在接受文化商品的滋養時,加劇了追求更強烈滿足感的欲望,而局限于購買力的相對匱乏,其焦慮和痛苦不減反增,以至于露骨的物質享樂主義追求成為一種時尚。更少的人愿意冒險創新,當心中只有物欲的時候,人們的想象力也被削弱,并且因為理性人的價值觀深入人心,國家精神、批判意識、審美意識、關懷意識被拋到九霄云外,進而依附于資本的存在、生存、發展和自我實現之中。
三、“異化”理論的表現形式及其聯系
基于后工業化社會技術日益復雜的現實,在分析技術理性的基礎上,馬爾庫塞異化理論對濫用技術優勢、泯滅人性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提出批評。批判的角度包括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生態等各個方面,其中作為回答問題之鑰的是“單向度的人”[10]315。所謂“單向度”,是指只有肯定性而沒有否定性(批判性)。馬爾庫塞在闡述五大領域人如何異化為“工具理性”的過程并研究其內在聯系的基礎上得出結論,認為必須經過通盤考慮,才能解決異化問題。
(一)文化異化
西方資產階級依靠相對先進的生產力創造出豐富的文化產品并投入市場,人們的思想層次較以前有了很大的變化,作為革命主力的工人階級在這種畸形的社會意識中沉溺其中,理性的、革命性的意識淡化了。在對馬克思的異化理論進行消化吸收,并具體分析當代社會文化異化現象后,馬爾庫塞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異化理論體系,其核心觀點為:后工業化社會的新型極權主義特征(即對社會具有絕對權威、上層建筑滲透到人民生活各個角落的社會政體)取代了舊社會直接而殘酷的專制政體,將對人民的控制和壓迫隱藏在潛流之下,其最突出的表現是當代工業社會精神壓力不減反增、“單向度”思維同意識形態客觀上給人群帶來極大壓迫[10]413。這一觀點在《愛欲與文明》中有詳細論述:“快樂原則吞并現實原則:性欲以對社會有利的形式解放出來”[22],暗示了兩性的張揚是與精神的貧乏一體兩面的存在,人的精神越來越處于壓抑的條件下,文化異化實質上是文化作為人所演繹的產物,但又反過來支配人自己,成為潛移默化地束縛人精神世界和日常表征的潛在力量。人們創造文化的目的是滿足自身更高層次的需求,但因資本主義的控制,當代流行文化成為背離人類社會生活的力量,文化在被資本主義控制的后工業社會中淪為商品的附庸,與人類生活完全脫離,成為獨立的外化存在。
(二)社會異化
由于壟斷資本的急劇膨脹,后工業化社會上層統治的基礎更加牢固,以至于似乎化解了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而現實卻處處暴露出上層通過專利保護、法律契約等冠冕堂皇的“體面外衣”削弱受壓迫的階級。由于科學技術的跨越式發展,社會交往方式及其關系發生急劇變化,人類無法將行動的瞬間和體驗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生命,于是人與空間、時間、行動、體驗、物品、產品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23]。在這樣的情況下,人與社會的關系出現問題不可避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非人性化,技術的進步無孔不入地取消個人在創造財富和提供服務的主動性和個人偏好,個人的創造越來越受到壓抑,并且壓抑和敵視的情緒得不到宣泄。
2.嘈雜擁擠的社會使人產生各種癥狀的行為和反應,包括各種排斥、回避、攻擊、恐懼。
3.掌握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大力推動軍事工業的發展,進行戰爭冒險,國家軍事壟斷日益取代社會的自由競爭。而且這種控制超越了國界,往往是通過對技術、文化和政治的整體統籌考慮達到[24]。
(三)政治異化
后工業化社會的“政治集合體”基于技術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逐漸壯大,在政治參與上人不僅行動上選擇范圍有限,而且在思想上也被規訓為高度統一的社會價值,這種“同一性”將利益集團的所有主體對象綁在同一輛“戰車”上,造成表面趨同的穩固。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斗爭的現實,使馬爾庫塞認為統治者通過消費意識形態讓強大的壟斷資本主義進行自我再生產,也說明馬克思時代賴以生存的生產勞動領域已經轉變為消費領域,生產和再生產的重要性已被充斥著整個商業市場的欲望和消費行為所取代[17]204-205。通過消費這一行為實踐,人民的自主探索精神被禁錮,占據上層職位,操縱政治選舉的壟斷資本家以不斷迭代的消費形式和體驗創新繼續引導人民的關注點。鮑德里亞針對這種現象,論述道“消費社會作為一種特定化的新社會模式,通過將消費導向的思維傳達給人們,從而達到社會馴化的目的,使壟斷進一步優化,將高度發達的生產力與社會中新興的生產力相結合”[19]124-126。作為人們日常必不可少的社會活動,越是沉溺于消費,越是在捍衛具有某種文化霸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人們在消費這一物質或信息的交換中,以虛假的幻想掩蓋了其剝削統治、灌輸意識形態的真實面目,由此引發的政治異化和集權主義思潮更加嚴重。
(四)經濟異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方資本主義弘揚的私有制經濟為主的市場經濟模式得到修復和完善。但隨著信息科技的廣泛使用,經濟和社會結構隨之改變,中產階層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階級躍升機會,“消費型社會”順勢而出,成為后工業社會新的代名詞。對于這一現象,馬爾庫塞從人的本質、社會本質的范疇進行分析,得出“后工業化社會從單純的生產型社會過渡到消費型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系迎來了大變革,消費社會不斷消解人們的自主性,成為資本主義的附庸”[21]136-137。他從資本增值的角度對消費進行了分析,提出了真實需求和虛假的需求這一組相對的概念。
之所以人們自愿在消費中投入“虛假需求”,馬爾庫塞認為,是因為人們將從事經濟各領域的活動作為緩解社會異化造成壓抑的主要方式,但事實是人們已經置身于“虛假需求”之中,在潛移默化間改變了自身原有的必要消費取向。對此他分析不同時段的各類消費傾向,最后得出區分真假需求的標準——即“真正的需要”是人的本質需要,而“虛假的需要”是與人的生存無關系的需要。不同形態的資本主義社會通過為人們提供各種消遣方式,暫時滿足人們的需求,客觀上削弱了人們的反思與批判精神,使其自愿接受統治階級的控制,把物質需求作為價值追求的唯一指向,走向“商品拜物教”的深淵。生產和消費的關系被扭曲,如盧卡奇所言,在“虛假需求”的驅使下,人們的經濟生活朝著不良、畸形的方向發展,失去了真正需要的“必需品”,轉而成為生產流水線上的“活產品”,不斷產生著剩余價值[25]。
(五)生態異化
人所處的生態是人類生存之基,人這一物種在生態系統中不可避免地會與自然界產生相互影響的關系。馬爾庫塞提出,資本主義以占有資源的方式進行利益爭奪,造成破壞生態環境、產生生態危機。自然比人類更早產生并自主演化,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環境,而后工業化社會則認為資本的利益比自然的維系更重要,人們在獲得資本的同時也在嚴重破壞自然,因為短期利益驅使它沒有真正認識到周圍生態系統的重要性,而只是把生態資源的利用當作資本主義發展的材料和工具。
馬爾庫塞通過分析當時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長期以來引發的生態問題,特別是第二產業過度發展和人口爆炸增長的最新情況,不無憂慮地指出人與自然的矛盾已經十分尖銳,人們不斷索取甚至榨取自然資源,使自然界在追求物質利益的過程中淪為商業生產的附庸。他認為,這一問題的關鍵仍在于科學技術的發展,盡管他提高了生產力,增加了物質財富,但割裂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使人與生態系統發生了異化。
(六)五種異化間的聯系
馬爾庫塞在馬克思“勞動異化”的基礎上,針對后工業化社會的現狀,提出了涵蓋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異化命題,在異化無處不在、不斷疊加、潛藏于既有生存狀態又改變人的命運的社會中,人是單向度的、片面發展的人,放棄了對自身解放途徑進一步探索的努力[10]415。因為從經濟領域到政治領域,從文化領域到意識形態領域,從腦力勞動者到體力勞動者,技術異化的現實使人與自然、人與集體、人與人乃至人與自身的關系,變成了一種零和博弈的壓抑狀態,人必然會為了暫時超越現有經濟實力的滿足,而墮入絕對的奴役之路,毀損他人,毀滅自然進而走向末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后工業化社會生活的復制和推廣,人與人之間不再是情真意切的鮮活關系,而是機械物內部相互配合的零部件之間的關系,它的區別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當然,馬爾庫塞整體異化理論分析的是二戰后少數發達國家的后工業化社會,存在著將現象視為本質的疏漏,即馬爾庫塞將人的本質的異化視為絕對化的存在,這種異化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微觀的量化分析。
四、結論
21世紀已經步入第三個十年,科學技術尤其是數字技術的發展現實告訴世人,第四次科技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后工業社會人與人的關系發展方向,但社會的需求傾向早已改變,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使暴露在每個個體面前的困難并不單純體現為物質匱乏所引發的矛盾,更凸顯出由于科技、消費觀等意識形態領域的異化所帶來的詬病。通過分析馬爾庫塞后工業社會異化理論,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資本主義統治下人類社會所產生的異化問題,對我國的借鑒意義自然不必多說。
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在滿足人的基本物質需求的同時,更應注重充實人的精神生活,必須與物質文明協調發展。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們的生活節奏在技術和市場經濟的作用下逐漸加快,心理負擔與日俱增,異化現象不可能完全消除,被壓抑扭曲的人性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國家既要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又要滿足一定的精神需求,因此在價值觀的建構中,要非常重視人的價值,反對用物化的、異化的價值來壓制人的價值,反對用膨脹的物欲來擠壓人的精神空間。個人角度追求正當的物質利益,進行合理的消費是生存所需,但如果物欲膨脹,導致道德淪喪,必然使人喪失自我,淪為物欲橫流思想的奴隸,然后喪失人生的真正意義。因此,要避免物質需求與精神追求脫節的現象,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必須引導人們樹立健康向上、理性發展的價值理念。
對于技術問題,應該辯證客觀地看待,它雖然能極大地提高生產力,豐富人們的物質生活,但是不恰當的濫用會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科技帶給人們的負面效應,要在技術運用過程中加以有效規范和控制,把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程度,使科技發揮效用,合理完成人類的夙愿,擴大人類的生存空間。例如,對于發展中產生的一家獨大、寡頭壟斷等典型資本主義發展特征的數據型高科技企業,需要健全主管部門和監管機構的職責,在研究對照、消化吸收的前提下,實現科學高效的事后監管;同時將技術治理貫穿于數字技術從立項研發到推廣應用的全過程,明確技術使用主體的權責利三方面關系。參考文獻:
[1]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M].高铦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5-6.
[2]張慧珍,胡建蘭.發達工業社會人的生存困境和出路:基于馬爾庫塞科技異化理論的思考[J].現代交際,2022(3):17-24,121.
[3]陳振明.評馬爾庫塞對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的批判[J].學習與探索,1991(4):42-49,99.
[4]蘇平富.技術理性: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馬爾庫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研究[J].江漢論壇,2006(9):72-75.
[5]張成崗.從意識形態批判到“后技術理性”建構:馬爾庫塞技術批判理論的現代性詮釋[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7):43-48.
[6]王曉升.意識形態的“物”化與“物”的意識形態化:資本主義后現代社會意識形態狀況分析[J].哲學動態,2016(12):5-11.
[7]張秀琴.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概念理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28.
[8]江天驥.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社會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15.
[9]徐崇溫.“西方馬克思主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123.
[10]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張峰,呂世平,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
[11]衣俊卿.現代性焦慮與文化批判[M].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7:267.
[12]范曉麗.馬爾庫塞批判的理性與新感性思想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07.
[13]彭海峰.馬爾庫塞后工業社會異化思想研究[D].西安:西安科技大學,2022.
[14]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M].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221-222.
[15]王曉升.發達工業社會中的現代性問題:評馬爾庫塞對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的批判[J].南京社會科學,2018(12):9-17,30.
[16]尼爾·波斯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M].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32-33.
[17]馬爾庫塞.工業社會和新左派[M].任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18]張雄,劉倩.馬爾庫塞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思想探析[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2):108-116.
[19]鮑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20]梅景輝,周泊然.哈貝馬斯生活世界理論的意識形態之維[J].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19(6):1-7.
[21]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M].黃勇,薛民,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22]蔡垚.加速社會中的“超真實”體驗:鮑德里亞、羅薩對資本主義規訓秘密的揭示[J].內蒙古社會科學,2020(5):52-58.
[23]辛向陽.馬爾庫塞的工業民主理論評析[J].國外社會科學,2011(1):40-46.
[24]卓承芳.現實的消失和人類的未來:鮑德里亞和維希留的激進技術批判哲學[J].哲學動態,2017(12):28-33.
[25]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M].王偉光,張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324-325.作者簡介:周天宇(1995—),男,土家族,湖南張家界人,單位為湖南師范大學,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國際金融。
(責任編輯:趙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