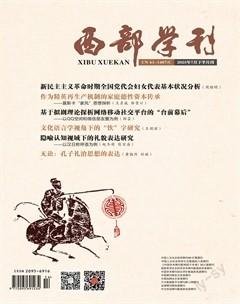淺析公安機關偵查人員較少出庭作證的原因及對策
楊金城 張士棟
摘要:在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大背景下,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已然轉變為服務于審判的訴訟準備活動。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偵查人員較少出庭作證,在一定程度上顯現出對相關法律規則的規避。究其原因,主要存在庭審未完全實質化、運行模式掣肘、公安機關的被動應付、偵查人員的抵觸情緒和現實制約等因素。通過樹立現代文明司法理念、公檢法的有效銜接運行、公安機關的全力保障和偵查人員專業有效參與,逐步完善和強化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保證庭審對證據的認定和裁判公正,進而促進庭審的實質化。
關鍵詞: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庭審實質化;審判中心
中圖分類號:D92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3)14-0096-04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Fewer Detectives of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o Testify in Court
Yang Jincheng1Zhang Shidong2
(1. Tibet University, Lhasa? 850000; 2. The Peoples Court of Baiyin District of Baiyin, Baiyin? 730900)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of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 with trial as the center, the detective activities of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litigation preparatory activities for trial. In judicial practice, detectives of public security organs rarely testify in court, which shows their evasion of relevant legal rul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are the absence of fully substantive trial, the constraints of the operation mode, the passive response of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he resistance of the detectives and the practical constraint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civilized concept of justic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court,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and the professional and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detectives, we can gradually improve and strengthen the testimony of the detectives in court to ensure the justice of the evidence identification and the trial,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substantive trial.
Keywords: detectives; testify in court; substantive trial; trial center
刑事訴訟主要包括五個階段:立案、偵查、公訴、審判、執行。在大多數公訴案件中,公安機關主要負責偵查,檢察院主要負責公訴,法院主要負責審判。在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下,我國的刑事訴訟模式由傳統的以偵查為中心的公檢法三角關系轉變為控辯審三方互動參與的訴訟構造。這意味著在刑事訴訟中,審判將居于主導地位,立案、偵查、公訴和執行都將圍繞著審判而展開。以審判為中心,旨在強調庭審的實質化,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完善證人出庭制度。在此背景下,對于公安機關來說,不僅從宏觀層面要求自身職能定位的轉變,更對偵查人員的偵查行為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求偵查階段對各種證據的合法收集,又強化了起訴階段對各種證據材料合法、客觀的法庭調查和控辯方質證,從而更好地排除非法證據[1]。這對于防止冤假錯案、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推進司法文明具有重大意義,不僅順應了時代潮流,更是現代法治的普遍要求。但在司法實踐中,由于種種原因的掣肘,公安機關的偵查人員較少出庭作證,在出庭率、出庭方式和作證內容等方面仍表現出與這一制度設計上的不盡如人意[2]。基于此,本文從公安機關自身角度出發,對偵查人員較少出庭作證的原因進行簡要分析,并試圖提出相應對策措施。
一、作為偵查主體公安機關的抵觸情緒
在刑事訴訟中,公安機關作為公訴案件最主要的偵查主體,是整個偵查活動的組織和實施者。因此,在分析偵查人員較少出庭作證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在宏觀層面對偵查主體公安機關的抵觸情緒進行梳理。
第一,公安機關出庭作證會降低偵查效能。預防和打擊犯罪是公安機關的重要職能之一,在以審判為中心的模式下,公安機關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不僅要承擔刑事案件偵辦任務,還要在偵查終結以后的起訴過程中承擔作為控方的出庭作證任務。這勢必大大增加了公安機關的案件偵辦成本和工作任務,在當前公安機關警力不足的掣肘條件下,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公安機關打擊犯罪的能力,不利于偵查效能的提升。
第二,公安機關出庭作證將增加偵查難度。眾所周知,偵查與犯罪的對抗,決定了偵查行為的秘密性特征,公安機關出庭作證,在接受質問時需要將一定的案件偵辦過程進行“如實”說明,在庭審中存在泄露各種偵查方法和偵查措施秘密的可能。甚至在某些公開審理的案件中,對公安機關出庭作證和接受質問的細節和內容要求得更嚴更細,無論是訴訟參與人,還是社會公眾,都將對此一一知曉。這樣就使得公安機關的偵查行為沒有秘密可言,從而加大了偵查工作難度,不利于今后刑事案件的偵破。
第三,公安機關出庭作證導致訴訟邏輯不清。根據《刑訴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擔任過本案證人的偵查人員要實行回避。按照這一訴訟邏輯,承辦案件的偵查人員就不能再成為此案的證人,否則就違背了這一規定背后的法律邏輯。刑事訴訟程序是按照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的先后順序進行的,如果偵查人員只是出庭說明案件的相關情況,則不存在上述問題。但如果公安機關偵查人員就相關問題進行作證,其身份便具有證人屬性,顯然與這一規定的法律立意相違背。那么,從這一角度來看,只能將偵查人員的出庭行為理解成對案件事實和取證過程進行“說明情況”的述職行為,而非作證行為。
二、偵查人員較少出庭作證的具體原因分析
偵查人員較少出庭作證的具體原因可以從刑事訴訟、公安機關、偵查個體的三個層面予以說明。
第一,刑事訴訟中庭審存在未完全實質化表現。現階段,人民法院在庭審中主要還是以案卷審判為主,庭審的調查方式主要是宣讀筆錄,無論是控辯雙方,還是法庭,都很少提請和通知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即使是有個別出庭作證,法庭問偵查人員是否有刑訊逼供[3]?偵查人員予以否認之后,作證就結束了,并沒有再做調查。再比如,辨認筆錄的制作過程中,可能存在偵查人員間接暗示、甚至明示告知現象,法庭調查幾乎從未問及此類問題,即使有,在偵查人員否認后,作證結束。可見,習慣于案卷調查為主的法庭調查并未真正進入實質。久而久之,對于這種慣于形式的出庭作證,控方和法庭也不愿意主動申請或通知偵查人員出庭作證。
第二,公檢法三機關的體制和運行模式掣肘。從體制上來說,公安機關屬于行政機關,隸屬于當地人民政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是獨立的司法機關,三者并不存在行政上的隸屬關系。但現實中,一些地方公安機關的主要負責人往往還兼任當地政法委的領導職務,從宏觀層面上對檢察院和法院的工作具有統籌協調的指導作用。在刑事訴訟中,我國的公、檢、法三機關按照“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執行法律規范,公安機關負責偵查、檢察院負責起訴、法院負責審判,但實際當中的情況是“互相配合”多,“互相制約”少,三機關的慣性思維依然反映在“配合打擊和懲治犯罪”上。這兩個影響因素,也導致檢察院和法院在一般情形下很少要求公安機關偵查人員出庭作證。
第三,公安機關的消極態度引起的被動應付現象。首先,公安機關內部對于刑事案件的偵辦,長期存在一種“公安做飯,檢察院端飯,法院吃飯”的思想認識,案件在偵查終結移送起訴以后就視為已經完成了本職,起訴和審判是檢法兩院的事,不屬于自己的主業,因而不愿再參與訴訟中的其他環節。其次,公安機關認為自己本身和檢察院、法院是平級單位,在庭審中讓其所屬偵查人員出庭作證,接受法庭調查和質問,似乎顯得在檢法兩院面前“低人一等”。最后,偵查過程中,公安機關主導各種偵查活動,從某種層面上來說,嫌疑人接受公安機關的刑事調查,其行為是被動的,從而使公安機關在與嫌疑人的關系上顯得“高高在上”。公安機關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在庭審中要接受控、辯方的問話,這就使得偵查人員與嫌疑人的關系上又顯得“平起平坐”。種種因素造成公安機關在大多時候都對出庭作證持消極態度。
第四,公安機關自身繁重工作任務的現實影響。公安機關承擔著維護社會治安和懲治違法犯罪的多重職責,隨著社會發展和轉型的不斷深入,公安機關不僅要完成大量的社會矛盾糾紛排查化解、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防范打擊、流動人員的管理、禁毒、消防、安保等本職業務工作任務,還要承擔大量的如扶貧、維穩等其他任務,甚至許多屢禁不止的非警務活動。在警力緊缺的前提下,公安機關本身就已經在“超負荷運轉”,部分基層公安機關甚至顯現出“疲于應付”的工作局面。這些現實因素導致公安機關不可能做到要求偵查人員都普遍出庭作證。
第五,偵查人員思想和心理上表現出的抵觸情緒。在刑事案件的偵辦過程中,嫌疑人一般是按照偵查人員的“指令”行事,這使得偵查人員在心理上具有某種“特權思想”。而在審判階段,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可能會面臨接受嫌疑人的質問,這將會嚴重沖擊偵查人員之前形成的“特權思想”。同時,在整個訴訟過程中,由于部分偵查人員因個人或其他原因,會出現不愿出庭作證或擔心出庭作證效果不佳的為難心理。從上述角度考慮出發,偵查人員對于出庭作證一般都會產生抵觸和抗拒情緒[4]。實踐中也表明,很少有偵查人員主動申請出庭作證接受質問的。
第六,偵查人員自身的現實制約和相關制度有待完善。公安機關偵查人員的工作任務尤為繁重,幾乎不可能專門抽出時間來應對大多數的出庭作證。而且,偵查人員在工作中需要頻繁出差,經常不在工作地,若要求普遍出庭作證,在時空條件上也存在一定困難。比如,近年來高發的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僅偵辦一起案件,偵查人員異地工作的時間少則幾周,多則以月計。同時,目前對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規定也較為籠統,缺乏能達到普遍出庭作證具體操作制度,如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范圍和身份的界定、公檢法三機關具體銜接機制、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時間和經濟保障等。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約著偵查人員普遍出庭作證目標的實現。
三、實現公安機關偵查人員普遍出庭作證的對策暢想
基于對公安機關偵查人員較少出庭作證具體原因的分析,可以“對癥下藥”提出相關對策,以期真正意義上推進刑事訴訟庭審的實質化。
第一,轉變思想,真正樹立現代文明司法理念。首先,這不僅要求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的整個過程中,真正樹立“以審判中心”的思想,果斷摒棄傳統的偵查中心主義[5],更多的是強調公安機關在案件偵破過程中,要提高偵查法治化意識和水平,注意證據的合法、規范收集,避免出現各種瑕疵,堅決杜絕刑訊逼供;注意各種偵查措施的合法、規范使用,將程序正義理念與實體正義理念并重,甚至置前。檢察機關要樹立“偵查是為了更好地起訴”的理念,強化起訴前對各種偵查行為活動的監督,及時提出檢察建議,堅決排除非法證據。法院審判要改變“案卷中心主義”,庭審中注重推動法庭調查的深度和實質化,強化對傳聞證據和直接言詞證據的引進使用;克服怕麻煩思想,及時通知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不斷提高偵查人員的出庭率。其次,注重克服各種“特權思想”,包括偵查人員相對于嫌疑人地位的“特權思想”和偵查人員相對于公訴人和審判人地位的“不平等思想”,真正做到“分工負責”“相互配合”,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實際上只是服務于刑事訴訟,是支持其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的應有之義,并不存在所謂的“高低貴賤”之分。最后,偵查人員要將出庭作證視為偵查工作的一部分,即出庭作證也是對自身偵查行為活動的后期檢視,有助于不斷提高偵查行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偵查成本的增加相較于司法文明的推進,是現代法治理念下的偵查效能的綜合提升。
第二,完善機制,推進公檢法運行的有效銜接。首先,相對于刑訴法和司法解釋的框架規定,相關部門還應及時制定出臺有關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具體法規,明確銜接機制,提高可操作性。規定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具體情形,出庭人員范圍和資格界定,如參與案件偵破的輔警人員可否出庭作證?在非法證據的排除中,雙方質證一比一言詞證據的認定原則和再次深入調查等。其次,公檢法三機關應依照相關法律法規及時完善有關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聯系機制,明確三機關的具體責任和義務,如檢察院和法院是通過公安機關通知相關偵查人員到場,抑或直接通知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以及相關的責任問題,如某些冤假錯案中,檢察院和法院缺少必要的提請和通知相關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責任、公安機關消極應付的責任等。
第三,強化措施,確保公安機關內部的全力保障。近些年,出現過公安機關被當事人提起的行政訴訟,甚至某些冤假錯案,這就要求公安機關應從提高案件偵辦質量的角度出發,強化和完善相關措施,全力保障其所屬偵查人員出庭作證。首先,應當建立公安機關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具體辦法,明確出庭作證人員,并給予較充足的準備和出庭時間、一定的經濟補償或交通補貼,形成操作性較強的保障機制。其次,建立內部硬性考核機制,積極探索以定罪率代替以破案率和破案數為定量的考核方式,明確規定不出庭或消極出庭的責任,及時進行獎懲。最后,加強內部培訓。包括提高偵查人員在案件偵查取證過程中的專業、規范操作水準,以及偵查人員在出庭作證時的專業法律知識和技巧培養,積極組織偵查人員參加庭審旁聽和參與模擬庭審[6]。
第四,積極應對,實現偵查人員的專業有效參與。從案件偵辦的角度來考慮,偵查人員在立案之時,就應當確立出庭作證也是案件偵辦應有部分的思想認識,樹立出庭作證與前期偵辦并重的理念。強化在獲取案件線索時偵查手段的合法運用,規范、標準的進行勘驗檢查等偵查措施,注意偵查的程序性問題,避免證據瑕疵,堅決杜絕刑訊逼供。不斷提高專業法律知識素養,在出庭作證時做到規范、標準應答和說明,在接受質問時理性、如實陳述,實現良好的出庭效果。同時,加強自身心理素質培養,避免出現“心慌嘴亂”的臨場效果。在證明案件事實和偵查合法合規的同時,展現偵查人員的良好形象。出庭作證也促使偵查人員發現前期偵查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注重對前期偵查活動的檢視,從而更好地指導今后偵查工作,避免“閉門造車”之弊端。
四、結論
庭審實質化包含有很多方面的內容,有司法禮儀行為的形式規范,也包括有關法庭調查和證據認定、裁判的實質規范。各個方面并不存在孰輕孰重的邏輯問題,都顯現出對“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成敗的重要性。窺一斑而知全豹,從公安機關參與刑事訴訟的自身角度出發,以公安機關偵查人員較少出庭作證為切入點,通過簡要分析其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對策假設,意圖能夠改變公安機關偵查人員較少出庭現象。從而強化證據裁判規則,保證庭審對證據的認定和裁判公正,推動庭審的實質化進程,在真正意義上促進以審判為中心的現代文明法治目標的盡早實現。
參考文獻:
[1]李儲信,連洋.以審判為中心訴訟改革背景下警察出庭作證研究[J].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20(6):28-34.
[2]徐宏濤.關于公安機關民警出庭問題的實證研究:以天津市公安局實證調查為例[J].河北公安警察職業學院學報,2020(4):41-44.
[3]宋克政.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J].法制與社會,2021(9):77-78,160.
[4]戴鵬.論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制度的困境與破解[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21(3):46-52.
[5]劉航穎.警察出庭作證制度研究[J].河北公安警察職業學院學報,2019(2):40-44.
[6]趙錫睿,韓云昱.審判中心視野下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問題研究[J].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20(2):122-128.
作者簡介:楊金城(1986—),男,土族,甘肅天祝人,單位為西藏大學,研究方向為民族法學。
張士棟(1983—),男,壯族,山東梁山人,甘肅省白銀市白銀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一級法官,研究方向為刑事司法實踐。
(責任編輯: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