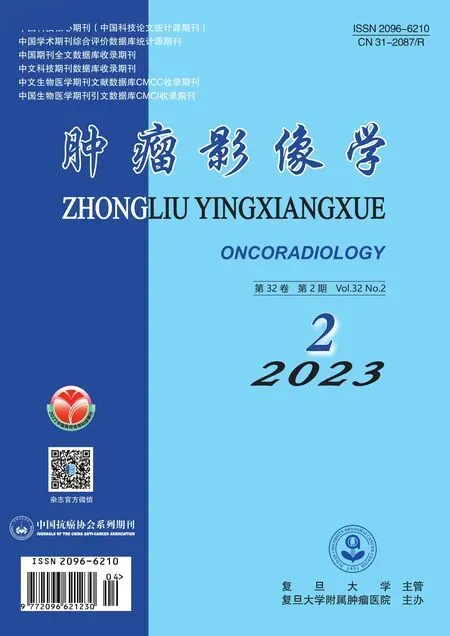T細胞效應功能核醫學顯像:邁向精準腫瘤免疫治療
周昊毅,劉昭飛,
1. 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放射醫學系醫學同位素研究中心,北京 100191;
2.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核醫學科,北京 100191;
3.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核醫學科,北京 100142
自從2013年美國The New York Times、Science將腫瘤免疫治療評為腫瘤研究領域的“重大突破”以來,免疫治療的熱度不斷攀升,被認為是目前有可能根治腫瘤的治療方法之一[1]。免疫治療通過調動人體自身的免疫系統來對抗腫瘤,在T細胞、自然殺傷(natural killer,NK)細胞、樹突狀細胞、巨噬細胞等免疫細胞的聯合作用下,對腫瘤細胞進行監視和清除[2]。除了對原發腫瘤的有效抑制,多項臨床試驗[3]結果表明,激活的免疫系統也能夠有效地清除微小的轉移病灶。因此,免疫治療是重要的治療腫瘤及防止腫瘤轉移和復發的方式之一。
目前,以免疫檢查點如程序性死亡受體1(programmed death-1,PD-1)、程序性死亡受體配體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以及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CTLA-4)阻斷性抗體為代表的腫瘤免疫治療在腫瘤治療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4-6]。迄今為止,已經有多種針對免疫檢查點的單克隆抗體獲批上市用于不可切除或轉移性黑色素瘤[7]、非小細胞肺癌[8]、肝癌[9]等的治療。
盡管免疫檢查點阻斷療法在臨床上實現了階段性成功(部分腫瘤患者的客觀緩解率、無進展生存期及總體生存率均顯著提高),但其有效性仍然有限。臨床數據顯示,在使用CTLA-4抗體進行治療的腫瘤患者中,緩解率僅有15%[10];而使用PD-1/PD-L1抗體治療的患者響應率也僅能達到30%[11-12]。此外,由于免疫檢查點阻斷療法對免疫系統的激活作用是全身性的,因此在給藥方案不恰當的情況下,激活的免疫細胞在殺傷腫瘤的同時也會對正常的組織或器官造成損傷,進而出現免疫相關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如免疫性心肌炎、肺炎、結直腸炎等[13-14]。因此,如何提高腫瘤免疫治療的響應率和有效性,以及在免疫治療早期對患者的響應情況進行精準監測是目前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基于傳統的計算機體層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的實體瘤臨床療效評價標準(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RECIST)及實體瘤免疫療效評價標準(immune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iRECIST)是目前評估腫瘤患者預后的通用臨床標準。RECIST和iRECIST與基于創傷性的活檢和只能提供有限信息的血液學指標相比,具有無創、實時動態和可連續監測的優點。然而,兩者在評價腫瘤的免疫治療時均存在局限性。首先,基于CT和MRI的顯像方法只能從解剖學的角度判斷腫瘤的體積大小改變,很難判斷大量淋巴細胞浸潤(通常預示著良好的預后)導致的腫瘤體積暫時增大(腫瘤假性進展),并且無法提供在腫瘤免疫應答中更為關鍵的分子水平的信息[15]。其次,基于以上標準的療效評價通常需要在治療4周以后才能確認疾病是否進展,將導致患者治療有效性的信息獲取存在嚴重的滯后性并可能錯過最佳的調整治療策略窗口期[16-17]。因此,迫切需要一種在體、無創、實時動態、精準可靠的手段,能夠準確地監測免疫治療過程并精準地預測治療效果,從而在治療的早期準確篩選可能的獲益群體,指導臨床醫師及時調整給藥方案。
作為精準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正電子發射體層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為代表的核醫學分子影像能夠在分子水平上對疾病的關鍵分子進行實時、動態和定量的監測,從而為疾病的早期精確診斷、治療精準監測、復發和轉移預警以及指導個體化治療提供嶄新的技術手段,因此在腫瘤的精準診治及患者分層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18]。本文將對目前應用于腫瘤免疫治療效果評價的核醫學分子影像研究動態及進展進行述評。
1 18F-FDG PET在免疫療效評價中的局限性
18F-FDG是目前臨床上應用最廣泛的PET顯像劑。作為一種葡萄糖類似物,18F-FDG能夠被糖代謝旺盛的腫瘤細胞攝取,可根據18F-FDG的攝取變化分析腫瘤的進展狀況[19]。雖然18F-FDG在腫瘤治療監測領域得到了非常廣泛的應用,但其在免疫治療評價方面卻存在著局限性,即18F-FDG的攝取并非腫瘤特異性,無法區分腫瘤細胞和在免疫治療中糖代謝同樣旺盛的免疫細胞[19]。因此,無法準確判斷腫瘤部位18F-FDG攝取增高是由于腫瘤細胞持續增殖引起的腫瘤進展,還是由于免疫治療后大量免疫細胞在腫瘤部位的浸潤引起的假性進展[20],這無疑會妨礙精準評估患者對免疫治療的實際響應狀況。因此,針對免疫治療過程中腫瘤微環境關鍵免疫相關生物標志物設計構建特異性核醫學探針,通過在體動態可視化顯像免疫治療過程中關鍵免疫細胞或分子的變化,將使免疫治療的精準監測及療效判斷成為可能。
2 基于免疫相關生物標志物的核醫學分子影像
為了特異性地捕捉腫瘤免疫微環境的信息變化,基于免疫相關生物標志物的PET被陸續應用于腫瘤免疫治療的效果監測中。這些顯像所關注的靶點大體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關鍵的免疫檢查點,本文將以PD-1/PD-L1為例進行介紹;第二類是T淋巴細胞相關的生物標志物,如CD8、可誘導共刺激分子(ICOS)、顆粒酶B等。
2.1 針對PD-1/PD-L1的顯像策略
荷蘭de Vries課題組于2018年首次在Nature Medicine上報道了將89Zr標記的抗PD-L1抗體用于預測抗PD-L1療法對患者的治療效果,結果顯示,治療前的顯像探針攝取與患者生存率密切相關[21]。隨后,該課題組也報道了免疫治療前PD-1靶向PET對于患者抗PD-1治療效果的預測價值[22]。這些相關的研究開創了通過核醫學在體顯像腫瘤免疫相關分子標志物以動態監測臨床免疫治療效果的先河。然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腫瘤內PD-1/PD-L1的表達具有異質性和不穩定性的特點,因此通過其表達水平來對PD-1/PD-L1阻斷療法進行療效有效性的預測僅局限在部分患者中,并非所有患者腫瘤中PD-1/PD-L1的表達量均與后續的治療效果相關[23]。
2.2 針對CD8+ T細胞數量的顯像策略
由于目前多數免疫治療策略最終發揮抗腫瘤作用依賴于CD8+T細胞在腫瘤內的浸潤和發揮效應功能[24],因此動態監測腫瘤微環境中CD8+T細胞的浸潤對于預測免疫治療的效果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國內外陸續開展了CD8+T細胞特異性顯像的研究,如采用放射性核素標記的CD8抗體片段[25]、小分子抗體[26-27]、納米抗體[28-30]等進行的核醫學顯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同樣由de Vries課題組于2022年在Nature Medicine上發表,該工作使用89Zr標記的抗CD8單臂抗體,用于預測腫瘤患者的免疫治療效果[31]。相比于PD-1/PD-L1,針對CD8分子的在體顯像可以更加直觀地觀察免疫治療后CD8+T細胞在腫瘤微環境中的數量變化。然而,該策略存在兩點局限性:一是無法區分CD8+T細胞的來源。有研究[32]表明,腫瘤固有的和從外周浸潤來的CD8+T細胞在抗腫瘤免疫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并不相同,免疫檢查點阻斷療法往往依賴于外周T細胞在腫瘤內的浸潤,而非腫瘤內固有的T細胞。因此,這種對所有來源CD8+T細胞數量的顯像策略顯然不夠精準;二是CD8靶向顯像無法判斷CD8+T細胞的激活狀態。腫瘤內的CD8+T細胞包含多種亞群,如初始CD8+T細胞、旁觀者CD8+T細胞、功能失調CD8+T細胞、激活CD8+T細胞等[33];只有經過抗原提呈細胞(如樹突狀細胞)呈遞腫瘤抗原并激活后的CD8+T細胞才具有殺傷腫瘤細胞的能力。因此,單純地顯像CD8+T細胞的數量無法區分這類激活的CD8+T細胞亞群。基于CD8分子的顯像策略僅能夠從CD8+T細胞的數量出發進行療效評價,而無法對CD8+T細胞的功能進行更精準的評估。一項對于TCGA數據庫的回顧性分析[34]也指出,單純的CD8表達水平與患者生存率之間并沒有顯著相關性。這些前期的研究工作表明,尚需進一步發掘CD8+T細胞在腫瘤免疫應答中的新靶點,實現對活化后發揮效應功能的CD8+T細胞的精準顯像。
2.3 針對T細胞激活相關標志物的顯像策略
ICOS和OX40等在激活型T細胞上呈現特異性高表達,為激活型T細胞的核醫學顯像探針的制備提供了重要靶點。近年來,已有研究將放射性核素標記的ICOS抗體和OX40抗體用于顯像激活的T細胞,進而監測免疫檢查點阻斷[35]、嵌合抗原受體(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AR)-T細胞療法[36]、腫瘤疫苗[37]等多種免疫療法的治療效果。上述策略成功實現了對激活型T細胞的在體可視化,然而,這些分子例如ICOS在激活后的免疫抑制性T細胞(如調節性T細胞,Treg)同樣呈現高表達[38]。因此,無法通過PET對免疫抑制性T細胞的激活或細胞毒性T細胞(CD8+T細胞)的激活進行有效區分,從而使免疫治療早期效果的判斷變得困難。同時,OX40通常高表達在CD4+T細胞上[37],因此以OX40為靶點的PET對于以CD8+T細胞發揮主導作用的免疫治療策略的監測價值有限。此外,目前靶向ICOS和OX40的核醫學顯像探針均為放射性核素標記的抗體,其在體內的清除時間較慢,往往需要多天才能達到最佳的靶/非靶比,嚴重限制了其臨床應用。
2.4 針對CD8+ T細胞效應功能的顯像策略
初始CD8+T細胞在經過抗原提呈細胞的抗原提呈刺激后激活,通過分泌顆粒酶B、γ干擾素(interferon-γ,IFN-γ)等效應分子來殺傷腫瘤細胞。這類效應分子的分泌代表了多重免疫調控通路下的最終信號,因此對它們的顯像可以更直接地反映激活型CD8+T細胞的殺傷能力,從而更準確地評估免疫治療的效果。已有研究[39]探索了以IFN-γ為靶點的PET在腫瘤免疫應答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該研究將放射性標記的抗IFN-γ抗體用于腫瘤疫苗療效的預測。而針對顆粒酶B的PET策略首次于2017年提出,Mahmood課題組基于鼠顆粒酶B底物線性多肽序列研制了PET顯像探針68Ga-NOTA-GZP,并在動物實驗中證實了其在免疫治療效果預測中的價值[40-41],由于線性多肽在體內的不穩定性,目前尚未有68Ga-NOTA-GZP在臨床上進一步應用的報道。2022年,我們團隊基于人顆粒酶B底物序列設計并優化出新型小分子PET顯像探針68Ga-grazytracer,其相比于68Ga-NOTA-GZP具有更好的體內穩定性,且在臨床患者中實現了對CD8+T細胞效應功能的在體可視化顯像[20]。然而,由于顆粒酶B作為分泌蛋白的固有特性,僅有細胞外的顆粒酶B才能夠被PET顯像探針捕獲[42],這意味著尚需大量的臨床試驗來明確顆粒酶B PET在患者免疫治療后的最佳窗口期。
3 總結與展望
相較于傳統的18F-FDG PET,靶向直接發揮抗腫瘤效應的CD8+T細胞的在體可視化核醫學分子影像能夠更加精準地預測和評價包括免疫檢查點阻斷療法、CAR-T細胞療法等CD8+T細胞所介導的免疫治療的效果。同時,亦能為腫瘤免疫學的基礎研究提供基于在體動態可視化的新視角。基于CD8+T細胞數量的核醫學顯像由于無法有效區分免疫細胞的效應功能,在直接判斷免疫治療效果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其在免疫治療之前通過在體剖析CD8+T細胞在腫瘤的浸潤狀況或許在區分免疫“冷”腫瘤或“熱”腫瘤方面具有一定的臨床價值。相較于基于CD8+T細胞數量的在體顯像,基于CD8+T細胞效應功能的核醫學分子影像在理論上能夠更加精準有效地判斷免疫治療的抗腫瘤效果。然而,目前能夠應用于臨床的CD8+T細胞效應功能顯像探針的種類有限。對現有CD8+T細胞效應功能核醫學顯像探針的優化,以及基于前瞻性臨床試驗明確顯像窗口期和治療監測效果,將會進一步驗證其臨床價值。另外,通過加強對腫瘤免疫的基礎研究,基于新靶點的發掘從源頭和底層設計面向T細胞激活及發揮效應功能的創新性核醫學分子影像探針,將會為腫瘤精準免疫治療帶來新的機遇。經臨床驗證有效的基于在體核醫學分子影像的腫瘤免疫治療監測手段將會為免疫治療的精準引導、及早提示更換治療策略、制訂新型聯合治療方案、指導腫瘤患者分層及臨床決策提供有力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