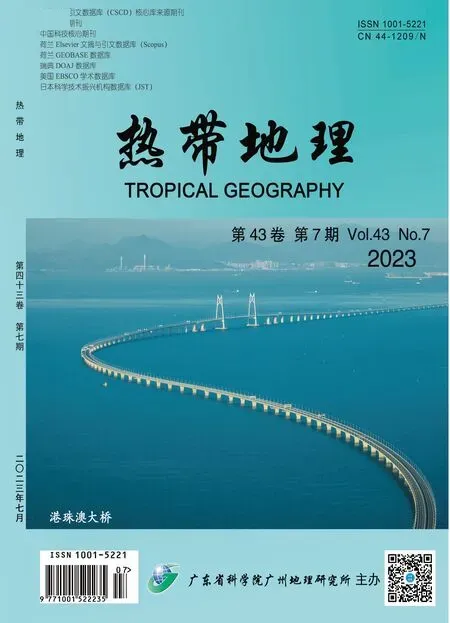廣州市荔枝主產區荔農綠色生產行為影響因素研究
楊遠萍,布買日也木·買買提,陳桂明,李 丹,賈 凱,姜 浩,陳水森
(1.新疆農業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烏魯木齊 830052;2.廣東省科學院廣州地理研究所,廣東省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應用實驗室,廣東省地理空間信息技術與應用公共實驗室,廣東省遙感大數據應用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廣州 510070;3.廣州市增城區仙村鎮鄉村振興辦,廣州 511335)
農業作為中國的基礎產業,是確保“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關鍵,是保障糧食安全的重要基石,也是保證鄉村生態宜居的根本所在。但是,中國農業長期以來“高耗能、高投入、高廢物”的生產方式,致使農業成為最大的面源污染產業(高春雨 等,2011;梁流濤 等,2013)。農業面源污染不僅引發了國內的一系列食品安全與環境污染問題,還使得中國農產品出口遭遇“綠色壁壘”(羅丹 等,2000)。在此背景下,中國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文件推動農業綠色轉型。然而,當前中國農業綠色發展仍存在諸多問題,主要原因之一是作為農業生產主體的農戶綠色生產理念淡薄,綠色生產技術采納程度低(張云華 等,2004;張復宏 等,2017)。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農業綠色發展技術導則(2018—2030年)》等文件也都強調了農民主體性的重要作用,這充分說明農戶是中國實現農業綠色轉型的基礎。因此,立足于農戶的微觀角度,厘清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至關重要。
綠色生產行為是指農戶在生產的各個環節中采取“高產出、低污染”的可持續生產方式進行農業生產活動(余威震 等,2017;李明月 等,2020)。國內外諸多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對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展開研究,其范圍可概括為內部影響因素和外部影響因素,前者主要指農戶自身特征,后者指外界環境的影響。農戶的性別、年齡等個人特征決定農業人力資本水平的高低,進而影響農業綠色發展(楊志海,2018)。國內外學者在性別(黃武等,2012;Wang et al., 2017)和年齡(Jallow et al., 2017;羅磊 等,2022)對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研究方面暫無統一定論,但普遍認為受教育程度與綠色生產技術的采納程度呈正相關關系(Nazarian et al., 2013;彭斯 等,2022)。理性經濟人假設認為每個人都期望于追逐利潤最大化(Schultz, 1964),而中國的農村家庭不僅是一個社會單元,也是一個經營主體。因此,農戶會根據自身的家庭情況、生產經營情況選擇最優生產方式。一般地,家庭人口越多,勞動力人口占比越小,生計壓力越大,農戶在種植時會更偏向追求經濟效益而選擇過量施肥施藥(張云華 等,2004;Khan et al., 2015;宋鳳仙等,2021);農業勞動力的大量轉移使得農村兼業情況越來越常見,很多農戶由傳統的專職農民轉變為兼職農民,這不僅改變了農民的收入結構,也降低了農民的土地依賴度(Zheng et al., 2020)。計劃行為理論認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決定個人的行為和意愿(Ajzen, 1991),因此,除了這些外在特征,農戶的內在特征也影響其綠色生產行為。已有研究也引入心理認知概念來剖析農戶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如一些國內研究通過Logis‐tic 模型驗證了農戶的綠色行為認知(余麗燕 等,2023)和生態認知(張紅麗 等,2021)能促進其減量施肥施藥的行為。農戶是農作物的供給方,同時也是各種農資用品的消費者,其行為也會受到外界各方因素的影響。部分研究表明,政府的推廣培訓(Goodhue et al., 2010; Khan et al., 2015)、財政激勵(Shumway et al., 1994)、政策規制(蓋豪 等,2020;于艷麗 等,2020)都能有效促進農戶減少殺蟲劑和其他農藥的使用。作為農產品及農業生產資料的流通平臺,市場也會對農戶行為造成一定的影響,如Komarek等(2017)發現化肥價格與化肥使用、收入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朱哲毅等(2021)通過Oprobit 模型實證驗證了市場監督與組織約束對菜農減肥減藥行為的促進作用。也有學者從社會層面解讀影響農戶綠色生產行為的因素,如唐林等(2019)發現社會監督和群體認同能促進親環境行為。還有一部分學者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出發,提出通過提高農戶對他人、制度和社會的信任程度可以增強農業廢棄物循環利用的觀點(何可 等,2015;Mao et al., 2021),楊志海(2018)也證實了社交網絡會對綠色技術采用產生影響。
綜上,已有研究從各個方面對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主要聚焦在內部影響因素——農戶的個人特征、家庭經營特征和認知特征,以及外部影響因素——政府、市場和社會關系網絡。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大部分研究分析了生產環節中的某項或某幾項綠色生產行為,然而,綠色生產貫穿于農產品的產前、產中和產后各個環節,而不是指單一的某個環節或者某項行為。農戶對綠色生產技術的采納具有連貫性和多元性,僅僅研究某種或某個環節的生產行為并不足以代表農戶的綠色生產行為。2)現有研究大多探討某個因素或某方面的因素對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將各類因素歸納梳理到同一框架的研究較少。農戶綠色生產行為的實施與否受到多方因素的綜合影響,同時,各個因素之間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因此,在同一框架下研究各類影響因素,并探索各個因素之間的關系十分必要。3)現有研究對熱帶經濟作物綠色生產行為涉獵較少。經濟作物能給農戶帶來較多收益的同時,也能倒逼農戶增加化肥、農藥的使用量以獲取更多利潤。因此,對于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戶研究尤為重要。
荔枝作為中國熱帶地區的典型經濟作物,其種植規模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且經濟價值較高,是中國的優勢作物。因此,對荔枝種植戶——荔農進行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不僅能改善當地生態環境,也有助于突破“綠色壁壘”,開拓海外市場。鑒于此,本文從農戶的角度出發,選擇廣州市增城區荔農為研究對象,將產前、產中、產后需采納到的共11 項綠色生產行為納入研究體系,運用有序Logistic 模型實證分析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并利用隨機森林模型對綠色生產行為有顯著影響的因素進行重要性排序,深入挖掘影響綠色生產行為的關鍵因素。以期為相關政策制定的側重點提供參考,精準助推廣州市農業綠色轉型。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中國是荔枝種植第一大國,作為中國對外貿易重要港口的廣州市更是在荔枝種植規模上遙遙領先其他地區,且其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也名列前茅(齊文娥 等,2023),因此選擇廣州市進行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研究。廣州市增城區是著名的“荔枝之鄉”,荔枝種植歷史悠久,長期從事荔枝種植的農戶較為集中,相較于其他地區,增城荔枝單價較高(鄧小瓊 等,2017),能有效地帶動當地經濟效益,并于2012 年被評為國家地理標志產品,更具代表性。因此,選擇廣州市增城區作為調研地點(圖1)。

圖1 廣州市增城區區位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Zengcheng District, Guangzhou
調研小組于2022 年5—8 月先后對研究區開展預調研和正式調研,先采用隨機抽樣的方式從增城區全區抽取4個鎮/街道(仙村鎮、中新鎮、石灘鎮和荔城街道),再對荔農進行抽樣調查。為保證問卷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受訪者均為本地荔枝種植戶,對荔枝種植有一定的了解,且1 戶填寫1 份問卷。共計發放360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后,回收有效問卷323 份,有效率達到89.7%。有效調查樣本中,男性占比63.8%,明顯高于女性;年齡主要集中在41~50和51~60歲2個區間,分別占比30.7%和32.2%;初中學歷占比最高,達到46.7%,高中和小學分別占比22.0%和19.2%。
1.2 變量選擇
荔農的綠色生產行為是指荔枝種植戶在從事生產活動的各個環節中,采取低污染、低消耗、循環利用的方式生產出高品質、綠色無公害的產品,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張云華 等,2004)。基于已有研究,結合荔枝特性,將荔農的生產活動分為產前、產中、產后3個階段,并總結歸納整個生產過程所需涉及到的綠色生產技術,從化肥(張復宏等,2017;Zheng et al., 2020;張紅麗 等,2021)、農藥(張云華 等,2004)、水資源(羅磊 等,2022)、廢棄物處理(黃武 等,2012;蓋豪 等,2020)4個方面選取11項指標作為二元變量納入衡量荔農實施綠色生產行為程度的指標體系,問卷中以“是”和“否”表征荔農該項綠色生產技術的實施情況,并賦值為“1”和“0”,而后將得分加總進行等級劃分,具體指標與等級劃分見表1所示。

表1 增城區荔農綠色生產行為實施程度的指標體系與賦值Table 1 Index system and assignment of implementation degree of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of lychee growers in Zengcheng district
基于文獻梳理,將解釋變量劃分為個人特征、家庭經營特征、認知特征和外部因素4 部分。其中,將認知特征梳理為安全生產認知、環境認知和政策認知3個維度,并通過主成分分析法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具體題項及因子分析結果見表2 所示。認知特征部分提取的3 個公因子及其他變量的具體含義和描述性統計分析見表3所示。

表2 增城區荔農認知特征的變量含義與因子分析結果Table 2 Variable meaning and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of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ychee growers in Zengcheng district

表3 變量含義及描述性統計分析Table 3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1.3 研究方法
荔農在決定是否實施綠色生產行為時,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明晰影響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因素,并確定各個影響因素的重要性,對研究如何有針對性地推動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高效實施,全面提高荔農綠色生產水平有重要意義。因此,選用有序Logistic 回歸模型提煉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潛在影響因素,并利用隨機森林模型對各影響因素的重要性進行排序。
1.3.1 有序Logistic 回歸模型 基于個人特征、家庭經營特征、認知特征和外部環境4個層面,選取影響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20 個指標作為解釋變量(X),以“荔農綠色生產行為實施程度”為被解釋變量(Y)。被解釋變量被分為“差”“較差”“中等”“良好”“優秀”5 個等級,分別賦值為“1”“2”“3”“4”“5”,為有序多分類變量。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 回歸模型分析荔農綠色生產行為實施程度的影響因素。該模型的表達式為(張蓓 等,2014;劉鋼 等,2017):
式中:P(Y≤j|X)為荔農綠色生產行為實施程度等級為j時的概率;Xi表示第i個自變量;j代表綠色生產行為實施程度等級;β是與X對應的回歸系數;α為模型截距。
1.3.2 隨機森林模型 隨機森林是一種監督機器學習算法,在分類和回歸上都有較強的穩定性和準確性,也能對變量的相對重要性進行預測(邢曉語等,2021;Yang et al., 2021)。因此,利用R4.2.1軟件構建隨機森林模型,對有序Logistic 模型的回歸結果進行重要性排序。該模型采用基于基尼系數選擇特征的分類回歸樹進行重要性排序,即每個變量對分類樹每個節點上觀測值異質性的影響越大,該變量越重要。通過調試,將樣本按照7︰3的比例分成訓練集和測試集,設置隨機種子數為100,ntree=400,mtry=4。計算變量重要性的表達式為(Cheng et al., 2020):
2 結果與討論
2.1 模型檢驗
為保證問卷的有效性,利用SPSS26.0軟件對問卷進行信度和效度的分析。問卷整體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58,信度較高;安全生產認知、環境認知和政策認知3個維度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出KMO值為0.791,Bartlett 球形檢驗<0.001,說明問卷結構效度較好,設計合理。
在進行有序Logistic 回歸分析前,對各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容差值均>0.1,方差膨脹因子VIF值均<5,說明各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且模型通過平行線檢驗,符合比例優勢。
2.2 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2.2.1 個人特征對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 由表4可知,性別和學歷對荔農的綠色生產行為無顯著影響。文獻梳理發現,國內外對性別的研究均無統一定論,本研究中性別無顯著影響的原因可能是男性受訪者占總樣本的63.8%,占比過高。學歷無顯著影響可能是因為研究區為發達地區,相較于其他學者的研究地區而言,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國家統計局,2021)。年齡在1%的統計水平上對荔農的綠色生產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可能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荔農勞動供給能力降低,難以掌握復雜的綠色生產技術(楊志海,2018)。

表4 增城區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回歸分析結果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of lychee growers in Zengcheng district
2.2.2 家庭經營特征對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荔農兼業和園地面積分別在5%和1%的統計水平上對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實施具有顯著負向影響,這說明荔農的兼業情況會阻礙其綠色生產行為的實施,這可能是因為本研究樣本中荔農兼業現象達到76.2%,很多村民都是采摘季返家務農,其余時間無暇打理果樹,對土地的依賴性降低(Zheng et al.,2020),為了減少人力資本和時間成本,荔農可能會選擇無規律、無節制地增加化肥、農藥的施用量;園地越大,荔農綠色生產行為實施程度從差到好的概率越低,這說明園地面積越大的荔農,越不容易采納綠色生產行為,這與宋鳳仙等(2021)的研究一致。在實際調研中發現,研究區荔枝產量穩定,單價高,容易吸引資本投入,追逐利潤和存在的管理漏洞可能會成為承包商提高綠色生產水平的阻礙。
2.2.3 認知特征對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 政策認知、環境認知和安全生產認知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正向顯著影響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實施,這與大部分學者的研究一致(余威震 等,2017;張紅麗 等,2021)。政策認知和環境認知能促進荔農綠色生產行為,可能是因為綠色生產的政策和荔農的切身利益相關,并且對各種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后,荔農認為綠色生產能得到保障,其實施意愿也會隨之加強;荔農越了解不規范生產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就越能意識到綠色生產的必要性,轉變生產方式的可能性越大(Lithourgidis et al., 2016)。安全生產認知正向影響荔農綠色生產行為,可能是因為對違禁農藥、農用化學品的危害及其包裝的正確處理有一定了解程度的荔農更有可能采納綠色生產行為(張復宏 等,2017),這可能與當地政府著重宣傳相關知識、設置安全標語以及合理配置相關基礎設施有關。
2.2.4 外部環境對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 政府滿意度、增加農業收益、參加培訓、加大綠色生產補貼力度、制定村規民約和認定地理標志農產品品牌也能對綠色生產行為產生積極影響。就激勵作用而言,荔農對政府的滿意度能反映其對政府的信任(盧海陽 等,2016)。在足夠的信任、有力的政策保障和有效的品牌效應下,荔農對采納綠色生產技術帶來效益形成良好的心理預期,就越有可能實施綠色生產行為。“增加農業收益”能正向顯著影響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實施,這說明實施綠色生產所獲收益越高,荔農采納綠色生產技術的意愿也越強(Aldy et al., 1998),這符合經濟學中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就制約作用而言,法律法規作為一種正式制度,公眾信服力較強,但晦澀難懂,大多數村民難以理解其中要義;而村規民約是一種非正式制度,在發揮價值導向作用的同時,也淺顯易懂,因此,村規民約在農村發揮廣泛的作用(陳寒非 等,2018),其影響村民實施綠色生產行為的可能性較高。
“法律法規”“周邊村民的生產方式”和“增加生產成本”的影響力調查中發現,3 個變量對荔農的綠色生產行為沒有顯著影響。可能的解釋是,在以血緣、親緣、地緣關系為主導的鄉土社會中,人們的社會關系不是靠法律來調節,而是靠“禮”這種社會規范來調節(費孝通,2013),并且農村是一個典型的熟人社會,在執法過程中很難做到鐵面無私,難以把懲罰制度落實到位,這導致村民存在一定的僥幸心理,削弱了法律法規在農村的效力,較難約束村民行為;隨著網絡交通信息的發達,村民能多方位獲取荔枝種植的相關信息,其他渠道獲取的信息更為權威、科學、豐富,傳統的交流方式逐漸被替代,因此,在信息化的現代社會中周邊村民的生產方式對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不大;增加生產成本對荔農的綠色生產行為沒有顯著影響的原因可能是荔農在計算生產成本時并未將“實施綠色生產所需的成本”和“未實施綠色生產所需的成本”區別開。
2.3 荔農綠色生產行為影響因素的重要性分析
個人特征、家庭經營特征、認知特征和外部環境中的每一個解釋變量影響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重要程度都不同。因此,構建隨機森林模型用于分析荔農綠色生產行為影響因素的相對重要性(圖2)。其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政策認知、制定村規民約、安全生產認知、認定地理標志農產品品牌、環境認知、增加農業收益、年齡、園地面積、參加培訓、加大綠色生產補貼、政府滿意度和兼業情況。由此可見,認知特征占據主要地位,外部影響次之。這表明制定綠色生產相關政策時需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尊重荔農的主觀能動性,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村規民約排名第二,占據重要地位,可能是因為在長期執行過程中,村規民約逐漸內化為村民價值觀的一部分(周家明 等,2014),能較好地規范村民行為準則。加大補貼力度和增加收益都沒有占據重要地位,這說明荔農經濟理性不是影響其綠色生產的首要因素,這與石志恒等(2020)的研究一致。荔農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會綜合考慮其他因素,被動或主動地實現由“理性經濟人”到“生態經濟人”的轉變(李沛莉 等,2018)。

圖2 荔農綠色生產行為影響因素的重要性排序Fig.2 The importance ranking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of lychee growers
2.4 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回歸結果的可靠性,對樣本進行穩健性檢驗。由于探討的是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相較于年輕荔農,年長荔農的綠色生產行為參與度較弱,因此,刪除年齡段在50歲以上的樣本對實證結果進行穩健性估計(表5)。其各項回歸結果與表4基本一致,說明結果較穩健。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Table 5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3 結論與對策建議
利用增城區360戶荔農的調查數據,運用有序Logistic 模型對荔農綠色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并構建隨機森林模型揭示各個影響因素的相對重要性,得出以下結論:1)年齡、園地面積與兼業現象顯著負向影響荔農綠色生產行為實施;2)安全生產認知、環境認知和政策認知能有效促進荔農采納綠色生產行為,但環境認知的排名低于安全生產認知與政策認知;3)外部環境中的村規民約、加大綠色生產補貼、認定地理標志農產品品牌、政府滿意度、參加培訓、增加農業收益均顯著正向影響荔農的綠色生產行為,其中村規民約占據重要地位;4)4類影響因素的重要性排序為認知特征、外部環境、家庭經營特征和個人特征。
結合本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對策建議:1)制定綠色生產相關政策時需重點考慮荔農主體性,激發荔農主體意識,加強綠色生產責任感,正確引導不同認知程度的荔農積極進行綠色生產;2)著力塑造良好的綠色生產環境,提高政府公信力,合理制定村規民約、培訓方案、宣傳方案等政策措施,確保其可行性,做到“一村一策”;3)對采用綠色生產技術的荔農給予適當補貼,并將采用綠色生產技術后的成本與收益進行可視化對比,刺激荔農采納綠色生產技術的積極性;4)政府牽頭,適當引入資本,對種植大戶實行有效的市場監督,制定完整的果品檢測方案,并且通過土地流轉的方式適當擴大種植規模,降低兼業荔農比例,實現整個綠色生產過程中的統一管理,打造優質的品牌形象;5)促進科研院所和高校與果園的合作,推廣綠色生產技術,提升果品質量,培養新型職業農民,全面提高荔農綠色生產水平。
此外,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1)調研樣本不夠全面。由于時間資源和人力資源有限,本研究僅抽取增城區的4個鄉鎮進行問卷發放,所獲數據不夠全面,如果在全市范圍內增加調研樣本,結果的準確性將會得到提高;2)綠色生產行為的概念范圍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續需要擴充農業綠色生產行為的內涵,擴展綠色生產行為的研究領域。